强哥?请问阁下是谁?不错的好文
您正在使用一款已经过时的浏览器!部分功能不能正常使用。
请尝试升级或使用 其他浏览器。
请尝试升级或使用 其他浏览器。
精华 蓝色的浮冰
- 主题发起人 让我拥抱你
- 开始时间
- 注册
- 2010-04-24
- 消息
- 33,189
- 荣誉分数
- 17,601
- 声望点数
- 1,373
谢谢,回头想想好像没什么故事情节,拉了好长。不错的好文
Qiang Ge
新手上路
- 注册
- 2014-03-19
- 消息
- 12
- 荣誉分数
- 20
- 声望点数
- 3
这个称呼不错啊,谢谢强哥?请问阁下是谁?
Qiang Ge
新手上路
- 注册
- 2014-03-19
- 消息
- 12
- 荣誉分数
- 20
- 声望点数
- 3
是谁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想是谁就是谁强哥?请问阁下是谁?
OH YEAH~! 我知道你是谁了。是谁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想是谁就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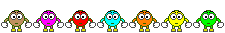
你是哥吗?你真的是哥吗?这个称呼不错啊,谢谢

Qiang Ge
新手上路
- 注册
- 2014-03-19
- 消息
- 12
- 荣誉分数
- 20
- 声望点数
- 3
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果果啊?你是哥吗?你真的是哥吗?

- 注册
- 2010-04-24
- 消息
- 33,189
- 荣誉分数
- 17,601
- 声望点数
- 1,373
看了半天到结尾原来是这样。。。。。简直让我哭笑不得啊。后面的那句话,让我想起我女儿小时候 ,一天和她出去玩在回家的路上,她突然跺着脚说尿急,但找来找去找不到可以尿尿的地方,可我不想找个角落让她尿,虽然那时她才三岁。那时中国可不象在加拿大那么方便,可以有TIM记什么的,没办法,就跟她说:忍一忍,忍一忍。于是急急忙忙的回家,回到家,她冲进洗手间,不久,出来,一边抄着裤子一边舒服的叹了口气后说:好长好长呀我的尿尿。
- 注册
- 2014-04-15
- 消息
- 6,048
- 荣誉分数
- 11,373
- 声望点数
- 1,323
凄美。 弥漫着不敢触摸的忧伤。 青春回眸,走近了;记忆的门透着熙光。门外是她被风吹拂的长发和温婉的身影。 期待故事的继续。。。二
街灯像是秋天下个不停的靡靡的细雨,把昏黄色的灯光像雨点一样耐心的打在站在酒吧门前排队的人的头发上,脸上和肩膀上。雨点流下的地方,洒了一片橙色的光晕。闷热的夜色里,我无精打采地变换着姿势站着,抖落一身灯光的雨水,百无聊赖地看着街上走过的一个一个打扮得很性感的女人。在这趟酒吧和舞厅聚集的街上,所有的女人都打扮得很妖娆,短裙,高跟鞋和低胸露肩露背的衣服是夏天闷热的晚上最常见的装束。她们大部分都是周围学校的学生,在晚上出来喝喝酒疯狂一下,显露一下优美的青春的身段,放松一下被学习绷得很紧的神经,就像我期末考试结束的时候觉得必须要出去醉一场一样。汽车引擎的噪音与嘀声和刹车声不断地在街上响起,像是一只没有新意的曲子,在古老的留声机里重复的让人厌倦地播放着,又像是恒久不停的单调的雨声,让人郁闷和无处发泄。
不远处的街角有一个男人站在一个墨西哥餐馆的栅栏外面靠着栅栏在抽烟,他的脸上带着孤独和疲倦的神色,烟的雾气在他的鼻子上方缭绕,模糊了他的额头。这让我想起了夜深时刻倚在寓所的窗户前抽烟的时候,有时会俯身看到下面空旷的街道上从汽车站方向走过来的神情疲累的女子,她们往往是经过一晚上的酒醉和狂舞之后独自乘坐公车回家的人。曲终人散,在半夜时分踯躅的在街头走过,她们的脸上带着暗淡的神情,像是被狂欢抛弃后坠入黑暗的深渊的孤独的天使。夜色拽住了她们的影子,高跟鞋的声音疲累的敲击着被夜色打湿的路面,失落攫取了她们的灵魂。那些女人偶尔会抬头向窗户里看着我。月光如水,我们四目相视,一刹那间心底似被什么触动,但很快就又恢复了平静。
我在蒙特利尔街头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女子。那天我错过了回W城的十一点的末班车,就在车站后面的一条街上找了一个供学生住的价格低廉的小旅馆要了一个房间。房间里面的空调的噪音大得让我睡不着觉,于是午夜时分我爬起来到外面去散步,把手插在裤兜里在旅馆附近的几条街上到处闲逛。我喜欢夜晚在陌生的城市散步,那些陌生的街巷总让我的心里感受到一种悸动,倘若是下雨,我一定会撑着一把伞。我喜欢在细雨霏霏的夜晚撑着伞在寂静的街上行走,让清凉的雨丝划过脸庞。在一条昏暗的巷子里,我看见一个在苍白的街灯下独自行走的像个学生一样的姑娘。她身材微胖,个子不高,穿着一条素雅的白色裙子,从我的对面走来。我记不清她上衣穿的是什么,反正不是那种妖艳的衣服。她在与我擦肩而过的时候用深蓝色的眼睛瞥了我一眼,停下脚步来用法语问了我一句话。我听不懂她讲的是什么,就站住了脚,对她摇摇头。她迈上路边的一间三层的陈旧的公寓的木板台阶,在公寓的破旧的木门口掏出钥匙把门打开,手扶着门把手改用英文问我说,这么晚了,你不想找个地方睡一晚吗?倘若是一个在街角伫立的打扮妖艳涂着浓妆的女人问我这句话,我一定会以为是遇上了一个妓女,但是她的穿着很朴素,脸上也没有化妆的痕迹,就像是一个忙碌了一天之后跟几个朋友随便喝了点儿酒然后疲惫的走回家的学生。我想她一定以为我是一个无处可住的可怜的等车人,半夜里在街上闲逛,等待着黎明第一班车的到来。我依旧摇摇头,她的脸上显现出一丝失望和不解的神情,蓝蓝的眼睛瞥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就走进公寓里面去了,木门咯吱一声在她的身后关上。我继续向前走去,心里想起那首诗“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那个蓝眼睛的姑娘的眼里并没有结着愁怨,样子也不像丁香,她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胖墩墩的心地善良的姑娘,从我的身边走过,走进她的小公寓里去睡觉,在错肩而过的时候我们没有火花蹭出。诗人喜欢把生活描写得很美,但是生活毕竟不是诗,也许戴望舒笔下的那个雨巷里走过的丁香一样的姑娘其实是一个俄国老大妈,我很邪恶的想,或者是一个在街头驻足顾盼的夜莺也说不准。我拐过街角,继续向着蓝色和红色的霓虹灯闪烁的圣凯瑟琳街走去,在那里找了一家脱衣舞厅要了两杯啤酒,坐在台前看着舞女们随着震耳欲聋的音乐把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脱掉,脱得最后一丝不挂,在台上扭动着赤裸的身体。那些美丽的长腿和晃动的乳房总会在我的心里引起颤抖,引起我身体的反应,何况在喝酒之后就更加无法控制自己。在一位妖艳的舞女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低下头来用她的热气撩人的嘴唇在我的耳边说了一句话后,我端着啤酒站起来,跟她牵着手走进了后面用隔板隔开的私人跳舞间,让她给我跳了两只舞。她在我的身上蹭来蹭去,把我心里的一点本来微弱的火给撩了起来,恨不得让她一直在我身上蹭下去。但是在曲子终结的时候我突然醒悟过来,我兜里的钱还要留着第二天坐长途车,于是我谢了她,把两只曲子的钱交给她,又给了她五块钱的小费。她把钱放入手包里,拿过在椅子边上的带着蕾丝的乳罩,用手绕到背后把带子的挂钩系上,抬起腿来把红色的内裤重新穿上,站起身来,脸上有些失望的跟我说再见。我端着啤酒坐回到桌前,继续看台上的舞女脱掉本来穿的就不多的衣服。她们大多身上只带着乳罩和穿着细小的颜色鲜艳的内裤在桌子间穿行,不时在桌子边停下来,询问有没有人要她们跳舞。我一直看到凌晨三点关门才带着酒意出来,又回到小旅馆去接着睡觉。回旅馆的路上又经过了来时的路,走过那个女子的公寓的时候看到里面的房间的窗户都黑漆漆的,周围一片寂静,只有夜风在街上寂寞地穿梭,和我的脚步声在路上单调地回响着。我不是一个爱自作多情的人,但是有一刹那,我希望她的公寓里的窗户上还亮着灯光,希望她坐在台阶上吸烟,那样我就可以走过去,跟她借个火,坐在台阶上一起吸只烟,看看如水的天街,聊几句天,然后的然后谁知道呢。
你永远不知道你在生活里错过了什么,就像在蒙特利尔的那个晚上我不知道若是跟那个女子进入她的公寓房间会发生什么一样。从窗外车站方向走过来的女人沿着寂静无人的街道向着黑暗的深处走去,高跟鞋踩在沥青铺成的路面上的声音继续单调地敲打着寂寞的夜色,我依旧在寓所的窗前抽我的烟,看着她的影子在地上移动。烟雾成圈状在我的眼前一环环地散开,被月光砍断,像是一个一个向上飘去的跳跃的音符。我曾经设想过,如果我对着窗外喊一声,嘿,上来一起抽根烟吧,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也许两个孤独的人会结伴度过一个狂欢后寂寞的夜晚,也许两个素不相识的人会在不经意的触碰中擦出微弱的火花,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然而,我从没有这样试过,我只是沉默地吸我的烟,看着烟圈和生命中偶然邂逅的女人渐行渐远,消失在吞没一切的黑暗里。不要说偶然邂逅的女人了,就是当初喜欢的,又怎么样呢?就像我曾经喜欢过的隔壁家的女孩小萍,那个曾经盼着每天从我的窗前经过的小萍,我现在都快想不起来她长得什么样子了。当往日熟悉的面孔在记忆的河流里变得遥远和模糊起来,你会觉得有一种失落感像河底的鹅卵石一样压在心底,有一种惆怅像是吃了一个苦涩的青橄榄一样堵在喉头,有一种想流泪想哭但是流不出泪哭不出来的感觉,那些泪水只是波澜不惊无声无息地流进了心底貌似平静的河流,就像舒婷写的那首诗:“也许有一个约会/至今尚未如期/也许有一次热恋/而不能相许/要哭泣你就哭泣吧, 让泪水/流啊, 流啊, 默默地。”
- 注册
- 2014-04-06
- 消息
- 8,609
- 荣誉分数
- 16,518
- 声望点数
- 1,323
《过于蓝》的结构好了很多,关于结局个人认为,“我”并不是一个求生愿望很强的人,更合理的结局是与直子一起死了,没有可能有那么多‘英雄般’的挣扎......
特别喜欢前两章(小萍出场前的部分),油画般的场景描写,灵巧而精致的画面切换,娴熟的意识流拉伸运用,作者不动声色的将亦幻亦真,如梦如魅般的灵魂世界静静呈现......单凭这样的文字风格就足以让你越众而出,成就不朽。
这个风格在《海边咖啡屋的莫扎特》中得到了延续和发挥,无数细微的感受有如海面上起伏跳跃的银亮光斑,碰撞,惊叹,绽放,破灭,最终消逝.....十分难得!
特别喜欢前两章(小萍出场前的部分),油画般的场景描写,灵巧而精致的画面切换,娴熟的意识流拉伸运用,作者不动声色的将亦幻亦真,如梦如魅般的灵魂世界静静呈现......单凭这样的文字风格就足以让你越众而出,成就不朽。
这个风格在《海边咖啡屋的莫扎特》中得到了延续和发挥,无数细微的感受有如海面上起伏跳跃的银亮光斑,碰撞,惊叹,绽放,破灭,最终消逝.....十分难得!
最后编辑:
- 注册
- 2010-04-24
- 消息
- 33,189
- 荣誉分数
- 17,601
- 声望点数
- 1,373
说得对,最后有些太戏剧化了,如果男主就直接跟直子在大巴上掉入水里死了,可能会更好一些。《过于蓝》的结构好了很多,关于结局个人认为,“我”并不是一个求生愿望很强的人,更合理的结局是与直子一起死了,没有可能有那么多‘英雄般’的挣扎......
特别喜欢前两章(小萍出场前的部分),油画般的场景描写,灵巧而精致的画面切换,娴熟的意识流拉伸运用,作者不动声色的将亦幻亦真,如梦如魅般的灵魂世界静静呈现......单凭这样的文字风格就足以让你越众而出,成就不朽。
这个风格在《海边咖啡屋的莫扎特》中得到了延续和发挥,无数细微的感受有如海面上起伏跳跃的银亮光斑,碰撞,惊叹,绽放,破灭,最终消逝.....你可能正在创造中国文学的一个奇迹,十分难得!
谢谢你的过于褒奖之词,这样的小说,是喜欢的人喜欢,不喜欢的人根本就看不下去。我想我这类的小说,不会有几个人真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