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使用一款已经过时的浏览器!部分功能不能正常使用。
请尝试升级或使用 其他浏览器。
请尝试升级或使用 其他浏览器。
暖暖午后茶
- 主题发起人 让我拥抱你
- 开始时间
- 注册
- 2012-04-23
- 消息
- 3,017
- 荣誉分数
- 4,624
- 声望点数
- 323
- 注册
- 2010-04-24
- 消息
- 33,189
- 荣誉分数
- 17,601
- 声望点数
- 1,373
- 注册
- 2014-04-15
- 消息
- 6,048
- 荣誉分数
- 11,373
- 声望点数
- 1,323
他乡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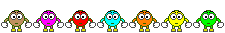 有范儿!
有范儿!- 注册
- 2012-04-23
- 消息
- 3,017
- 荣誉分数
- 4,624
- 声望点数
- 323
这两段写得很感人啊,虽然是30多年以前写的,很多内容跟现在也没什么区别。那时侯的台湾,和现在的大陆十分象,都是拼命要出国。一个学中文的人,出国做什么?(我是指于织云,没有谈别的人,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出国了,只能在家里呆着,难怪有那么多忧愁。
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一谈起祖国,我就感到非常亲切。
曾曼琳的话使织云很高兴,忙写了一封信到台北,向静慧报告一番。静慧回去后只来过一封信,说是忙,亲戚朋友都给他们接风,祖国的人情味“浓得像温暖的阳光”,这使常常面对阴沉沉的冷天的织云,更添了一份乡思。
织云领着小汉思的手,踩着枯黄色的草皮,被踏成黑褐色的落叶,从山坡上走下去。阳光那样好,照在他们的头上,热热的,暖得简直不像秋天,往常在这时节已经很冷了。运气不好的话,说不定会下雪,可是今天居然会这样暖,暖得像明媚的春天。旁边一些红木长椅上,坐了十多个晒太阳的女人,有的看书,有的织手工,有的聊天,有的逗孩子。一堆孩子在坡上追逐嬉戏。整个画面充满了宁静安详,看那些人的神态,彷佛不知道这世界上曾有过战争、死亡和衰老,她们的脸上洋溢着无忧而和平的笑。平常每次走到这里,小汉思总说:“妈妈,我要从坡上跑下去。”织云也总鼓励他说:“快跑、快跑,我倒要看看这个小运动员的腿脚有多快。”小汉思就会像脱缰的小马般,一口气跑到下面。
今天,他小小的心灵也被罩上了一层阴影,竟没有说要跑下去的话。母子两人紧紧的握着手,在众人好奇的眼光中,茫茫的林野间,默无一言的走过。远远的晴空,无垠的大地,让人看出岁月的无尽,人生之路的漫长。织云的心悸然一动,试想她唯一的爱子未来的一生,会不会像她这么茫然孤单的度过?她知道自己从那里来,回忆中有属于自己的国和家,还有乡可怀,有故土可恋,而她的小汉思,她的比生命还宝贵的孩子,竟连这点怀恋和回忆的幸福都没有,他是无乡可怀的。这个想头,使她的神经都痉挛起来。她握紧了小汉思,疼痛从心直流到手掌。孩子小小的心灵,立刻感到了母亲的悲哀,他回握着织云,不断的轻声叫道:“妈妈,妈妈——”
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一谈起祖国,我就感到非常亲切。
曾曼琳的话使织云很高兴,忙写了一封信到台北,向静慧报告一番。静慧回去后只来过一封信,说是忙,亲戚朋友都给他们接风,祖国的人情味“浓得像温暖的阳光”,这使常常面对阴沉沉的冷天的织云,更添了一份乡思。
织云领着小汉思的手,踩着枯黄色的草皮,被踏成黑褐色的落叶,从山坡上走下去。阳光那样好,照在他们的头上,热热的,暖得简直不像秋天,往常在这时节已经很冷了。运气不好的话,说不定会下雪,可是今天居然会这样暖,暖得像明媚的春天。旁边一些红木长椅上,坐了十多个晒太阳的女人,有的看书,有的织手工,有的聊天,有的逗孩子。一堆孩子在坡上追逐嬉戏。整个画面充满了宁静安详,看那些人的神态,彷佛不知道这世界上曾有过战争、死亡和衰老,她们的脸上洋溢着无忧而和平的笑。平常每次走到这里,小汉思总说:“妈妈,我要从坡上跑下去。”织云也总鼓励他说:“快跑、快跑,我倒要看看这个小运动员的腿脚有多快。”小汉思就会像脱缰的小马般,一口气跑到下面。
今天,他小小的心灵也被罩上了一层阴影,竟没有说要跑下去的话。母子两人紧紧的握着手,在众人好奇的眼光中,茫茫的林野间,默无一言的走过。远远的晴空,无垠的大地,让人看出岁月的无尽,人生之路的漫长。织云的心悸然一动,试想她唯一的爱子未来的一生,会不会像她这么茫然孤单的度过?她知道自己从那里来,回忆中有属于自己的国和家,还有乡可怀,有故土可恋,而她的小汉思,她的比生命还宝贵的孩子,竟连这点怀恋和回忆的幸福都没有,他是无乡可怀的。这个想头,使她的神经都痉挛起来。她握紧了小汉思,疼痛从心直流到手掌。孩子小小的心灵,立刻感到了母亲的悲哀,他回握着织云,不断的轻声叫道:“妈妈,妈妈——”
- 注册
- 2012-04-23
- 消息
- 3,017
- 荣誉分数
- 4,624
- 声望点数
- 323
我们的歌 一五四
织云气得半天说不出话,盯着何绍祥看了一阵才道:
“虽然你不在乎做那国人,我还是要告诉小汉思,他是中国人。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看你也是,父母都是中国人,孩子怎能不是呢?何况我认为做中国人是最幸运最光荣的事。再说,我的父母已经把我生成了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我想不做也来不及了。我既然爱做中国人,当然也得叫我的儿子做中国人。”织云故意嘲弄的笑笑,挖苦的道:“我们跟你不同,你太了不起了,早就不是中国人了。”
“妈妈,你说错了。爸比是中国人,莉萨说过:谁长了斜斜的往上吊,一条缝的眼睛,喏,就是爸比那样的,就是中国人。”小汉思把织云的话当了真,连忙更正她。
“够了,够了。一天到晚就甚么中国人不中国人的,连这么小的孩子都会说这样的话了。我就不懂,如果觉得非做中国人不可的话,为甚么要到国外来,要想尽方法留在这里!”何绍祥激动的大声说。由于他向来像池不会起波涛的死水,从不会大发脾气,也不会忘形的欢笑,总是含含蓄蓄、温温吞吞,现在发了这么大的雷霆,就使织云和小汉思都吃了一惊。
小汉思赶快溜回房里去了。织云却被他最后那句话伤得透了骨,她定定神,道:
“我虽然想尽方法留在这里,幸而还没有数典忘祖,比起有些人,还算好的呢!现在我想想,真的有点惭愧,国家把我培植到大学毕业,我甚么义务也没为她尽一点,天天就在这里怨天怨地的闹情绪。可是,绍祥,在你想给全人类尽义务的时候,就一点优先权也不给自己的祖国吗?你完全忘了受过国家多少好处吗?”
何绍祥怔了一下,就理直气壮的道:
“我没受谁的好处,我有今天完全凭自己,如果我留在中国,就不会有今天。”
“可是没有中国就没有你,别忘了你是用中国人的钱公费保送出来的,如果你不是在国内底子打得好,也不会有今天。”
“公费保送我出来,是因为我的成绩够资格。我没靠任何人,我是自己辛辛苦苦闯出来的天下。”何绍祥固执的说。
“好吧!随你怎么说。”织云的激动渐渐转成冷静,放弃的道:“绍祥,我们两个人的想法差得太远,在一起过这些年已经很不容易了。老实告诉你一句话,跟你在一起我觉得耻辱——”
“甚么?你说甚么?”何绍祥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恼怒的打断了织云的话。
“我说,我跟你在一起觉得耻辱。”织云清清楚楚的又说一遍。她面色苍白,声音有些微微的颤抖。“你忘本忘得太离谱了。你以为你比别的中国人高了好几等,你看不起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人,你不是吗?以前在慕尼黑凡是中国人的集会你全不参加,因为怕沾辱了你,是罢?你这个人,冷酷、自私、对谁都没有热情,你除了爱你的工作,你的论文,你的名,你的就要到手的所长地位,别的甚么也不爱。你就是学问打两百分,人性也只好打不及格。绍祥,我不能忍受跟你继续生活下去了。”织云在痛心之余,把数年来的积郁,一古脑儿全吐了出来。
何绍祥惊愕得像一个石头人似的僵站在地上,剎那间彷佛所有的思想和意念全脱了躯壳。织云的话使他太伤心也太意想不到了。跟她生活在一起几年,他一直努力工作,为她争得荣誉和金钱,让她过得富裕称心,自己辛苦得像架永不停歇的机器。他没有任何嗜好和享受,除了偶尔喝半小杯白兰地之外,可说是只有吃饭睡觉和工作。
而她,全看不到这一切,居然把他看成这样一文不值的一个人,在别人的眼睛里,何绍祥是甚么等级的人物?自己的妻子竟然说得他这样不堪。而且她提到慕尼黑,她为甚么要提慕尼黑?一定是因为怀念江啸风,对了,一定是,他早就觉察到她没忘记他。
何绍祥推推眼镜框,镜片后面的眼珠变得特别明亮,似有泫然欲泪之势。
“是了,我这样的人对你是不适合的,只有江啸风那种在国外混不下去的笨中国人,才适合你的胃口,你怎么不去找他呢?”他狠狠的说。
“你不必拖上别人,我是要带小汉思回台湾,我早就想回去了,只是下不了决心。谢谢你到底给了我勇气。”织云的脸色由白转红,黑幽幽的眸子盛着沉痛,真好像下了很大的决心。“没有甚么痛苦,比一个人看到自己卑怯更痛苦。我不但痛苦,我早就看不起自己了。”她强忍住夺眶欲出的泪。
“哼!”何绍祥从鼻孔里哼出一声冷气,回到书房去了。他双手抱着头,坐在书桌前,情绪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想起明早就得到日内瓦的高能物理研究所出公差,而要提出讨论的实验报告还差了一些没写完,他的心里就更焦躁,后来他换上了家常穿的衣服,喝了小半杯白兰地酒,假寐十多分钟,精神才又恢复了。
何绍祥就是何绍祥,一工作起来,就能忘记身外的世界,包括快乐的与不快乐的。跟织云争执的事,已不在他的意念之中。自然也就没有料到,织云这次并不是只说气话,而是真的下了决心,要带小汉思回台湾去了。
织云第二天一早就给瑞士航空公司打电话订了票,六天之后飞曼谷,然后转泰航经过香港直飞台北。
票既订好,她就赶忙给家里写信,叫他们到机场去接。但写了一半,又觉得不妥,这么突然的回去,是不是会使家人怀疑她此行的原因?如果父母知道她与何绍祥之间发生了裂痕,将会如何的失望、伤心、受打击!她想了想,决心扯个谎,就说何绍祥要到美国出差两个月,她带着小汉思在瑞士太寂寞,正好趁这机会回家去看看。
信是用快邮挂号寄的,她想象着家人收到后的兴奋和惊奇。
决定回去后,她的心反而定了,接着就忙着打理行装。出国八九年,总不能空着两只手回去,回国探亲的人没有不带些礼物送亲友的。可是她的心情如此坏,在这种情况之下回去,那里有心情去上街采办?如果甚么都不带的话,又怕家人亲友失望。正在为难之际,她忽然想起家里还有许多没有动用的新东西何不带回去送人?于是便翻箱倒柜的大找特找,到底给她发掘出来一些宝藏,甚么纱质衣料、丝围巾、皮手套、化妆品、男人领带、袖扣、小记事本、瑞士特产的小刀,还有其它零零碎碎的小玩艺,堆得像座小山。
在一只旧衣箱的底层,她发现了一只牛皮纸信封,面上没写字,里面像装着东西,看来似曾相识,却又说不出是甚么?拿着信封往外一倒,竟是一本过时的机票和一只小小的白金戒指。这两样东西使她触目惊心,久久不能移动眼光,而许许多多的往事,在剎那间都涌到眼前来。
她想起和江啸风一同创作“我们的歌”时候的日子,想起他们一同去买戒指,以及后来江啸风决定回国,硬把机票塞在她的皮包里,说:“回去找我,我等你、永远等你”时候的情景。
如今她真要回去了?难道他还在等她吗?难道她真会去投奔他么?江啸风曾说:“不管甚么时候,只要你愿意跟我完成我们共同的理想,我都张开双手来欢迎你。”她曾赌气的说:“大江,那只是你一个人的理想,并不是我的。”这几年来她就为这句话在惭愧,因为现在才深深的觉悟到,那也是她的理想。她曾有那么长的一段时期,活在迷乱与茫然之中,如今,她终算看清了真正的自己。但,过去的一切还会回头吗?她会真的去找他,站在他的面前,说:“大江,我终回来了”么?不,过去的永远过去了,爱情没有回头的路,受伤的爱情更无修补的可能,而她,怎么样也不会厚颜的真去找他。
织云气得半天说不出话,盯着何绍祥看了一阵才道:
“虽然你不在乎做那国人,我还是要告诉小汉思,他是中国人。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看你也是,父母都是中国人,孩子怎能不是呢?何况我认为做中国人是最幸运最光荣的事。再说,我的父母已经把我生成了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我想不做也来不及了。我既然爱做中国人,当然也得叫我的儿子做中国人。”织云故意嘲弄的笑笑,挖苦的道:“我们跟你不同,你太了不起了,早就不是中国人了。”
“妈妈,你说错了。爸比是中国人,莉萨说过:谁长了斜斜的往上吊,一条缝的眼睛,喏,就是爸比那样的,就是中国人。”小汉思把织云的话当了真,连忙更正她。
“够了,够了。一天到晚就甚么中国人不中国人的,连这么小的孩子都会说这样的话了。我就不懂,如果觉得非做中国人不可的话,为甚么要到国外来,要想尽方法留在这里!”何绍祥激动的大声说。由于他向来像池不会起波涛的死水,从不会大发脾气,也不会忘形的欢笑,总是含含蓄蓄、温温吞吞,现在发了这么大的雷霆,就使织云和小汉思都吃了一惊。
小汉思赶快溜回房里去了。织云却被他最后那句话伤得透了骨,她定定神,道:
“我虽然想尽方法留在这里,幸而还没有数典忘祖,比起有些人,还算好的呢!现在我想想,真的有点惭愧,国家把我培植到大学毕业,我甚么义务也没为她尽一点,天天就在这里怨天怨地的闹情绪。可是,绍祥,在你想给全人类尽义务的时候,就一点优先权也不给自己的祖国吗?你完全忘了受过国家多少好处吗?”
何绍祥怔了一下,就理直气壮的道:
“我没受谁的好处,我有今天完全凭自己,如果我留在中国,就不会有今天。”
“可是没有中国就没有你,别忘了你是用中国人的钱公费保送出来的,如果你不是在国内底子打得好,也不会有今天。”
“公费保送我出来,是因为我的成绩够资格。我没靠任何人,我是自己辛辛苦苦闯出来的天下。”何绍祥固执的说。
“好吧!随你怎么说。”织云的激动渐渐转成冷静,放弃的道:“绍祥,我们两个人的想法差得太远,在一起过这些年已经很不容易了。老实告诉你一句话,跟你在一起我觉得耻辱——”
“甚么?你说甚么?”何绍祥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恼怒的打断了织云的话。
“我说,我跟你在一起觉得耻辱。”织云清清楚楚的又说一遍。她面色苍白,声音有些微微的颤抖。“你忘本忘得太离谱了。你以为你比别的中国人高了好几等,你看不起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人,你不是吗?以前在慕尼黑凡是中国人的集会你全不参加,因为怕沾辱了你,是罢?你这个人,冷酷、自私、对谁都没有热情,你除了爱你的工作,你的论文,你的名,你的就要到手的所长地位,别的甚么也不爱。你就是学问打两百分,人性也只好打不及格。绍祥,我不能忍受跟你继续生活下去了。”织云在痛心之余,把数年来的积郁,一古脑儿全吐了出来。
何绍祥惊愕得像一个石头人似的僵站在地上,剎那间彷佛所有的思想和意念全脱了躯壳。织云的话使他太伤心也太意想不到了。跟她生活在一起几年,他一直努力工作,为她争得荣誉和金钱,让她过得富裕称心,自己辛苦得像架永不停歇的机器。他没有任何嗜好和享受,除了偶尔喝半小杯白兰地之外,可说是只有吃饭睡觉和工作。
而她,全看不到这一切,居然把他看成这样一文不值的一个人,在别人的眼睛里,何绍祥是甚么等级的人物?自己的妻子竟然说得他这样不堪。而且她提到慕尼黑,她为甚么要提慕尼黑?一定是因为怀念江啸风,对了,一定是,他早就觉察到她没忘记他。
何绍祥推推眼镜框,镜片后面的眼珠变得特别明亮,似有泫然欲泪之势。
“是了,我这样的人对你是不适合的,只有江啸风那种在国外混不下去的笨中国人,才适合你的胃口,你怎么不去找他呢?”他狠狠的说。
“你不必拖上别人,我是要带小汉思回台湾,我早就想回去了,只是下不了决心。谢谢你到底给了我勇气。”织云的脸色由白转红,黑幽幽的眸子盛着沉痛,真好像下了很大的决心。“没有甚么痛苦,比一个人看到自己卑怯更痛苦。我不但痛苦,我早就看不起自己了。”她强忍住夺眶欲出的泪。
“哼!”何绍祥从鼻孔里哼出一声冷气,回到书房去了。他双手抱着头,坐在书桌前,情绪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想起明早就得到日内瓦的高能物理研究所出公差,而要提出讨论的实验报告还差了一些没写完,他的心里就更焦躁,后来他换上了家常穿的衣服,喝了小半杯白兰地酒,假寐十多分钟,精神才又恢复了。
何绍祥就是何绍祥,一工作起来,就能忘记身外的世界,包括快乐的与不快乐的。跟织云争执的事,已不在他的意念之中。自然也就没有料到,织云这次并不是只说气话,而是真的下了决心,要带小汉思回台湾去了。
织云第二天一早就给瑞士航空公司打电话订了票,六天之后飞曼谷,然后转泰航经过香港直飞台北。
票既订好,她就赶忙给家里写信,叫他们到机场去接。但写了一半,又觉得不妥,这么突然的回去,是不是会使家人怀疑她此行的原因?如果父母知道她与何绍祥之间发生了裂痕,将会如何的失望、伤心、受打击!她想了想,决心扯个谎,就说何绍祥要到美国出差两个月,她带着小汉思在瑞士太寂寞,正好趁这机会回家去看看。
信是用快邮挂号寄的,她想象着家人收到后的兴奋和惊奇。
决定回去后,她的心反而定了,接着就忙着打理行装。出国八九年,总不能空着两只手回去,回国探亲的人没有不带些礼物送亲友的。可是她的心情如此坏,在这种情况之下回去,那里有心情去上街采办?如果甚么都不带的话,又怕家人亲友失望。正在为难之际,她忽然想起家里还有许多没有动用的新东西何不带回去送人?于是便翻箱倒柜的大找特找,到底给她发掘出来一些宝藏,甚么纱质衣料、丝围巾、皮手套、化妆品、男人领带、袖扣、小记事本、瑞士特产的小刀,还有其它零零碎碎的小玩艺,堆得像座小山。
在一只旧衣箱的底层,她发现了一只牛皮纸信封,面上没写字,里面像装着东西,看来似曾相识,却又说不出是甚么?拿着信封往外一倒,竟是一本过时的机票和一只小小的白金戒指。这两样东西使她触目惊心,久久不能移动眼光,而许许多多的往事,在剎那间都涌到眼前来。
她想起和江啸风一同创作“我们的歌”时候的日子,想起他们一同去买戒指,以及后来江啸风决定回国,硬把机票塞在她的皮包里,说:“回去找我,我等你、永远等你”时候的情景。
如今她真要回去了?难道他还在等她吗?难道她真会去投奔他么?江啸风曾说:“不管甚么时候,只要你愿意跟我完成我们共同的理想,我都张开双手来欢迎你。”她曾赌气的说:“大江,那只是你一个人的理想,并不是我的。”这几年来她就为这句话在惭愧,因为现在才深深的觉悟到,那也是她的理想。她曾有那么长的一段时期,活在迷乱与茫然之中,如今,她终算看清了真正的自己。但,过去的一切还会回头吗?她会真的去找他,站在他的面前,说:“大江,我终回来了”么?不,过去的永远过去了,爱情没有回头的路,受伤的爱情更无修补的可能,而她,怎么样也不会厚颜的真去找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