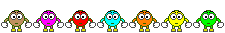orangejellybean
糖罐罐里的桔子豆
- 注册
- 2003-06-03
- 消息
- 211
- 荣誉分数
- 0
- 声望点数
- 0
A story to share
前段时间随手写了一些东西,本来打算回忆一下来加拿大十年的种种感想,但是一忙就丢在那里了。 读的时候请“切记”这是一个只在中国上过六年小学的人的随笔涂鸦, 不要有太多期待。。。haha ^_^
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来到加拿大整整十年了。十年,三千六百多个日子,如果我能活到七十岁的话,那么我已然在这个国家渡过了我生命的七分之一。时间像飞,不知不觉中我已经从那个懵懵懂懂,不太懂事的十三岁的小姑娘变成了现在。。。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实在是不好说,也许要等到下一个十年我才能对今天的自己彻底了解,并作一番贴切的评价。
今天我只好说我现在二十三岁。站在这个即将踏入本命年的门槛,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回忆的闸门一下子打开,许多本来以为淡忘掉了的往事忽然一下子变得无比清晰起来。有温馨的,快乐的,痛苦的, 悲伤的,有些是长久以来小心珍藏在记忆中的, 所以格外清晰,有些是模糊的,尤其是对无忧无虑的童年的印象,但被后来爸妈无数次如数家珍的描述过,也变得仿佛就在昨天。
最早的记忆是三四岁的时候和爸爸去北海玩,我拉着一个比自己稍稍大一点的小姐姐快活的在那片银滩上洒满我们的小脚印,并且不知好歹的在一块我自认为是最漂亮的地方栽上了一枝树枝,浇上海水,自作聪明的以为自己对这片美丽的海滩的最大贡献是十年后这里将长起一棵参天大树,并且和小姐姐约定了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回来摘下“树”上的一片叶子吹吹口哨。离开的时候爸爸告诉我等涨潮的时候我的“小树”就要被卷走了,我对他的观点呲之以鼻。
清楚地记得小的时候是个特别淘气顽皮的孩子,这个印象也多次被长辈和儿时的朋友证实过。那些多年没见过我的人,再次面对时总是惊讶得拉着我的手,说 “凡凡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文静懂事了,小的时候可淘气了。” 有些往事我早已经淡忘, 可是有些因为顽皮而闯祸的“重要事件”却记得好多。
还记得每年放暑假,同龄的孩子们总是急急的在头几天里赶完那本薄薄的暑假作业,反正老师最后也不检查,所以质量和速度成为反比。因为数学题做得快,我几乎总是第一个合上书本,并且以据说是极其让人“讨厌”的口吻对还在埋头的朋友们说,“我要下去玩儿了,大家继续加油努力啊。” 然后开始了我连续两个月的淘气生活。几乎男孩子们玩什么,我玩什么;女孩子们玩什么,我也玩什么。于是我在大院里和男孩子们上树爬墙,捉蜻蜓螳螂;和女孩子们跳皮筋打羽毛球。南方的机关大院里总是有许多漂亮的花花草草, 但是最最吸引我们的是随处可见的果树。 有酸酸的黄皮果,稍稍发涩的柚子,青色的梅子,紫色的桑仁,虽然小巧玲珑, 但是火红的石榴。最喜欢的莫过于大院里葡萄架上结的,一串串绿莹莹的葡萄。 可是因为架子很高,除了个别高年级的,个子比较高的男孩子可以够到一些结在低处的葡萄外,别的孩子只能干瞪眼。于是我从某个角落里拾来了一根长长的竹竿,用小刀把一头劈成两半,然后把这个自制的“夹子”伸到高处的葡萄藤中,夹住,轻扭几下,就把一串甜甜的葡萄完好无缺的提到自己面前。朋友们喜得纷纷效仿,这据说是那年夏天孩子们公认的最好的“发明”。?不过,最最令我得意的是楼下的那株属于我的枇杷树。这是大院里唯一的一株枇杷,据说是我很小的时候吃完了果子, 随手把子儿扔到楼下长成的。既然有这么一个典故,我就霸道的,毫不客气的把这棵树据为己有了。还记得第一次结枇杷的时候,有一个要好的朋友从楼下经过,发现了,就上楼去把我拉了下来,比我还兴奋的嚷嚷:“凡凡,你的枇杷树结果子了!”于是乎,我在众多孩子的注视下勇敢的爬上二楼的平台,危危险险的把果子摘下,与众家兄弟姐妹们分享。
最令人郁闷的事莫过于被上班去的妈妈反锁在防盗门内,一整天呆在家里。因为爸爸远在法国,妈妈白天还要上班,怕我在外面疯跑,于是一道防盗门把我和门外快乐的世界一分为二,我只能眼巴巴看着伙伴们继续他们的探险,一脸无奈的隔着防盗门的铁条对偶尔来“探视”我的朋友们皱眉头。开始的一段日子里,我还能勉勉强强的用妈妈给我留的好吃的零食和电视打发,自己在家弹弹钢琴,种种花草,用彩色的橡皮泥涅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实在无聊了就把家里废弃了的闹钟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拆下,再装回去。要么就是把爸爸给买的,一大盒子塑料小兵和大炮摆成战场,不过战局总是一边倒的,无一例外的以我方大获全胜,敌方全军覆没告终。不过过了几天,我不再安于现状,开始寻找我能力范围之内的“有意思的”事做,并且殃及左右上下的邻居。我把皮筋绑在椅子上跳皮筋,把鱼竿伸到楼下阳台伙伴的金鱼缸里“钓鱼”,用绳子吊上伙伴们刚刚捉到的螳螂蚂蚱之类的东西把玩,并且为了给二楼出远门的朋友留在阳台上的植物浇水而淋湿了三楼邻居奶奶就要晾干的床单。被严重警告之后,我只好对家里的东西发挥自己的想象。遭殃的东西包括无辜的君子兰,即将含苞待放的花苞被我用小刀给“解剖”了,灵感来源于我爱不释手的十万个为什么:植物篇;阳台上养的一盆现在我也想不起名字的开白花的植物被我注射了红墨水,满心期待着能够开出漂亮的红花(想法起源于动脑筋老爷爷), 不想还没到下午花儿就蔫了,估计死于红墨水的“毒杀”;还有一盆仙人球被我用镊子细心的把刺全部拔下,终于露出了“光洁的肌肤”,不过好像用“千疮百孔”来形容更为贴切些。最最令我伤心的是我心爱的小金鱼由于不堪我无聊时经常用手把它捞出来又放回去的蹂躏,终于在我周末外出的时候跳出鱼缸,结束了它短暂痛苦的一生。我把它葬在了楼下草地上,并在它的墓前献上了一个比它的墓要大得多的花圈。
又挨了几日,我实在无法忍受被监禁的痛苦,决定依靠自己的智慧想法子出逃。和我家阳台一墙相隔的伙伴献计让我举着雨伞从阳台上跳下去,并信誓旦旦的推测雨伞的功能与降落伞有异曲同工之效。现在想来不禁庆幸好在自己那时胆子不够大,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经过一番权衡,我小心翼翼的从自家的阳台爬到了隔壁,胆战心惊后开始了我盼望已久的第一个自由的上午。不过我很快就得到了应有的教训。在妈妈快要下班回来的时候,玩了一天的我终于不再有力气和胆量再从伙伴的阳台爬回自己家,只好乖乖坐在自家大门前等妈妈回来,结果当然是挨了妈妈一顿严厉的训话,并且第二天依然回到防盗门内的世界去。好在这种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经过了一系列的搜索,我终于掌握了妈妈留在家里的备用钥匙。于是乎,我在每天早晨妈妈的身影消失后的十分钟就用备用钥匙把自己“释放”出来,快乐逍遥一天之后又在妈妈即将回家的半个小时前把自己“监禁”回去。这个法子屡试不爽,直到来加拿大多年后被我失口泄露给妈妈。
还有一次是因为贪玩, 晚饭后爸爸多次叫我回家我都不予理睬。结果是正在得意洋洋从一个石凳跳到另一个石凳的我莫名其妙地把下巴磕在了石桌上。爸爸急得连忙张罗送我上医院,并找来认识的主任大夫亲自给我缝针。不知道是吓傻了还是害怕挨骂,虽然血流满了毛衣前襟,我还是不停的安慰爸爸说我其实一点也不疼。缝针之后的几天我总算安分守己的呆在家里了,只是每次去医院换药的时候被护士小姐戏称为“下巴戴上了口罩的小姑娘”。
还好我的淘气多数是收敛在家的,但有的时候毕竟本性难移,在学校时偶尔也会原形毕露。小学时上自然课,我是班上胆子比较大的孩子之一。有次作青蛙和小鱼的解剖,和我一个小组的几乎都是女孩子,手中的“屠刀”自然不敢对活蹦乱跳的小鱼小蛙划下去, 全都缩到了桌子的另一边。我对几位“淑女”不客气的嘲弄了一番,满不在乎的“磨刀霍霍向鱼蛙”。这种兴趣和大胆也许就是我对以后职业的选择奠定的第一步吧。
还记得有段时间我迷上了香港卫视中文台播放的日本动画片,为此没少和放学后强行把我们几个女孩子留在学校排练节目的班长抱怨。 现在想想,为了集体的幸福,我当时牺牲了多少宝贵的动画片段啊。更过分的是初中一年级有一次放学召开班干部会议,我心里正如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惦记着五点半播放的“足球小子”的大结局。班主任看我一副坐立不安着急上火的模样,问我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我少根筋的坦白了真实原因,愣把四十多岁的班主任气得目瞪口呆。凡此种种,今天想起来真是有些汗颜。 记得班上有段时间时兴男女生之间互相捉弄,可怜的我自然没能幸免。最最令我不爽的是每次打完预防针总被同桌的男孩(他坐我左边)威胁要捏我刚刚挨了一针的左边胳膊(右手要留着写字), 不过终于在一次因为流感和乙肝疫苗同时注射所以两只胳膊都没能幸免的情况下被我痛快的以牙还牙,这位仁兄立时当着全班的面含泪呲牙咧嘴。该生随后伺机报复,一日课间趁我在专心苦读课外书的时候将一只表面附满茸毛,可以以假乱真的塑料蜘蛛下降到我眼前。我大惊,猛然窜起后闪,将该男连同后边一排探头等待看热闹的家伙撞倒在地,顿时一片哎呀声起伏。待我惊魂未定的从地上爬起,可怜的同桌还倒在地上捧着被我一屁股坐到的小腿狂揉,我对其怒目相视,遂补上一脚。正是因为我出了名的调皮捣蛋,班主任又特别喜欢温柔文静的女孩(比如班长),所以无缘于她老人家的“专宠”名单,但是大概因为我成绩不错,她对我还是比较容忍的。
每年最最开心的事就是寒假或者暑假的时候随妈妈去北京探亲, 因而享受了无数每个孩子都“爱不释口”的美食,如豌豆黄,奶油炸糕,素什锦,山楂糕,果丹皮,小豆羊羹, 驴打滚, 栗子面小窝头…数不胜数,所以我这个馋虫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最难以忘怀的是九一年寒假在西单附近吃了一次“加州牛肉面”,外面干冷的北风和面前香喷喷,热气腾腾的面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是来年再去却怎么也寻不到这个铺子了。来加拿大后我偶然对朋友们赞起,被告知其实加州是没有什么牛肉面的。
在北京度假时,因为嘴巴比较甜而且家里也没有别的和我同龄的孩子,众位长辈对我可谓是宠爱有嘉,我拍马屁的时候大人经常会以好吃的和露雪和瑞士巧克力勉之。我最早的马屁历史要追溯到两岁零八个月。 当然,我自己的记忆力可没有那么灵光,完全是引用了妈妈的口述。据说当时人小鬼大的我在刚刚到家的时候对着迎出来的姨姥姥亲亲热热地冲上去,“姨姥姥,我可想你了!” 姨姥姥乐得嘴都合不拢了,立马奖励了一个妈妈也想不起来的好吃的东西。这倒没什么,不过次日我依样画葫芦的对舅姥爷献媚道:“舅姥爷,我最想你了!”一旁的妈妈惊愕与我无师自通的马屁技术,不过我拒绝相信她的描述,我的印象中,自己因该是一个绝对乖巧的小姑娘,绝对不是一个如此“两面三刀”,“阴险狡诈”的人(即是妈妈的描述属实,那么我现在也早就“改过自新”,并且“重新做人”了。)
最近开学了,好忙好忙,只好仍在这里了。好有好多需要补充的,以后也应该把现在写进去,不过结尾先写好了。。。赫赫
我对自己的要求:面对生活,我坚韧开朗;面对困难,我勇往直前;对于理想,我执著追求;对于生命,我永不放弃。
写于来加十年。献给随我一路走来的父母家人,与我一同度过这些美好时光的朋友们,以及那些因为我的调皮捣蛋而遭殃的儿时伙伴,谢谢你们让我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可以珍藏,并觉得此时此刻如此温馨快乐。
前段时间随手写了一些东西,本来打算回忆一下来加拿大十年的种种感想,但是一忙就丢在那里了。 读的时候请“切记”这是一个只在中国上过六年小学的人的随笔涂鸦, 不要有太多期待。。。haha ^_^
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来到加拿大整整十年了。十年,三千六百多个日子,如果我能活到七十岁的话,那么我已然在这个国家渡过了我生命的七分之一。时间像飞,不知不觉中我已经从那个懵懵懂懂,不太懂事的十三岁的小姑娘变成了现在。。。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实在是不好说,也许要等到下一个十年我才能对今天的自己彻底了解,并作一番贴切的评价。
今天我只好说我现在二十三岁。站在这个即将踏入本命年的门槛,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回忆的闸门一下子打开,许多本来以为淡忘掉了的往事忽然一下子变得无比清晰起来。有温馨的,快乐的,痛苦的, 悲伤的,有些是长久以来小心珍藏在记忆中的, 所以格外清晰,有些是模糊的,尤其是对无忧无虑的童年的印象,但被后来爸妈无数次如数家珍的描述过,也变得仿佛就在昨天。
最早的记忆是三四岁的时候和爸爸去北海玩,我拉着一个比自己稍稍大一点的小姐姐快活的在那片银滩上洒满我们的小脚印,并且不知好歹的在一块我自认为是最漂亮的地方栽上了一枝树枝,浇上海水,自作聪明的以为自己对这片美丽的海滩的最大贡献是十年后这里将长起一棵参天大树,并且和小姐姐约定了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回来摘下“树”上的一片叶子吹吹口哨。离开的时候爸爸告诉我等涨潮的时候我的“小树”就要被卷走了,我对他的观点呲之以鼻。
清楚地记得小的时候是个特别淘气顽皮的孩子,这个印象也多次被长辈和儿时的朋友证实过。那些多年没见过我的人,再次面对时总是惊讶得拉着我的手,说 “凡凡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文静懂事了,小的时候可淘气了。” 有些往事我早已经淡忘, 可是有些因为顽皮而闯祸的“重要事件”却记得好多。
还记得每年放暑假,同龄的孩子们总是急急的在头几天里赶完那本薄薄的暑假作业,反正老师最后也不检查,所以质量和速度成为反比。因为数学题做得快,我几乎总是第一个合上书本,并且以据说是极其让人“讨厌”的口吻对还在埋头的朋友们说,“我要下去玩儿了,大家继续加油努力啊。” 然后开始了我连续两个月的淘气生活。几乎男孩子们玩什么,我玩什么;女孩子们玩什么,我也玩什么。于是我在大院里和男孩子们上树爬墙,捉蜻蜓螳螂;和女孩子们跳皮筋打羽毛球。南方的机关大院里总是有许多漂亮的花花草草, 但是最最吸引我们的是随处可见的果树。 有酸酸的黄皮果,稍稍发涩的柚子,青色的梅子,紫色的桑仁,虽然小巧玲珑, 但是火红的石榴。最喜欢的莫过于大院里葡萄架上结的,一串串绿莹莹的葡萄。 可是因为架子很高,除了个别高年级的,个子比较高的男孩子可以够到一些结在低处的葡萄外,别的孩子只能干瞪眼。于是我从某个角落里拾来了一根长长的竹竿,用小刀把一头劈成两半,然后把这个自制的“夹子”伸到高处的葡萄藤中,夹住,轻扭几下,就把一串甜甜的葡萄完好无缺的提到自己面前。朋友们喜得纷纷效仿,这据说是那年夏天孩子们公认的最好的“发明”。?不过,最最令我得意的是楼下的那株属于我的枇杷树。这是大院里唯一的一株枇杷,据说是我很小的时候吃完了果子, 随手把子儿扔到楼下长成的。既然有这么一个典故,我就霸道的,毫不客气的把这棵树据为己有了。还记得第一次结枇杷的时候,有一个要好的朋友从楼下经过,发现了,就上楼去把我拉了下来,比我还兴奋的嚷嚷:“凡凡,你的枇杷树结果子了!”于是乎,我在众多孩子的注视下勇敢的爬上二楼的平台,危危险险的把果子摘下,与众家兄弟姐妹们分享。
最令人郁闷的事莫过于被上班去的妈妈反锁在防盗门内,一整天呆在家里。因为爸爸远在法国,妈妈白天还要上班,怕我在外面疯跑,于是一道防盗门把我和门外快乐的世界一分为二,我只能眼巴巴看着伙伴们继续他们的探险,一脸无奈的隔着防盗门的铁条对偶尔来“探视”我的朋友们皱眉头。开始的一段日子里,我还能勉勉强强的用妈妈给我留的好吃的零食和电视打发,自己在家弹弹钢琴,种种花草,用彩色的橡皮泥涅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实在无聊了就把家里废弃了的闹钟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拆下,再装回去。要么就是把爸爸给买的,一大盒子塑料小兵和大炮摆成战场,不过战局总是一边倒的,无一例外的以我方大获全胜,敌方全军覆没告终。不过过了几天,我不再安于现状,开始寻找我能力范围之内的“有意思的”事做,并且殃及左右上下的邻居。我把皮筋绑在椅子上跳皮筋,把鱼竿伸到楼下阳台伙伴的金鱼缸里“钓鱼”,用绳子吊上伙伴们刚刚捉到的螳螂蚂蚱之类的东西把玩,并且为了给二楼出远门的朋友留在阳台上的植物浇水而淋湿了三楼邻居奶奶就要晾干的床单。被严重警告之后,我只好对家里的东西发挥自己的想象。遭殃的东西包括无辜的君子兰,即将含苞待放的花苞被我用小刀给“解剖”了,灵感来源于我爱不释手的十万个为什么:植物篇;阳台上养的一盆现在我也想不起名字的开白花的植物被我注射了红墨水,满心期待着能够开出漂亮的红花(想法起源于动脑筋老爷爷), 不想还没到下午花儿就蔫了,估计死于红墨水的“毒杀”;还有一盆仙人球被我用镊子细心的把刺全部拔下,终于露出了“光洁的肌肤”,不过好像用“千疮百孔”来形容更为贴切些。最最令我伤心的是我心爱的小金鱼由于不堪我无聊时经常用手把它捞出来又放回去的蹂躏,终于在我周末外出的时候跳出鱼缸,结束了它短暂痛苦的一生。我把它葬在了楼下草地上,并在它的墓前献上了一个比它的墓要大得多的花圈。
又挨了几日,我实在无法忍受被监禁的痛苦,决定依靠自己的智慧想法子出逃。和我家阳台一墙相隔的伙伴献计让我举着雨伞从阳台上跳下去,并信誓旦旦的推测雨伞的功能与降落伞有异曲同工之效。现在想来不禁庆幸好在自己那时胆子不够大,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经过一番权衡,我小心翼翼的从自家的阳台爬到了隔壁,胆战心惊后开始了我盼望已久的第一个自由的上午。不过我很快就得到了应有的教训。在妈妈快要下班回来的时候,玩了一天的我终于不再有力气和胆量再从伙伴的阳台爬回自己家,只好乖乖坐在自家大门前等妈妈回来,结果当然是挨了妈妈一顿严厉的训话,并且第二天依然回到防盗门内的世界去。好在这种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经过了一系列的搜索,我终于掌握了妈妈留在家里的备用钥匙。于是乎,我在每天早晨妈妈的身影消失后的十分钟就用备用钥匙把自己“释放”出来,快乐逍遥一天之后又在妈妈即将回家的半个小时前把自己“监禁”回去。这个法子屡试不爽,直到来加拿大多年后被我失口泄露给妈妈。
还有一次是因为贪玩, 晚饭后爸爸多次叫我回家我都不予理睬。结果是正在得意洋洋从一个石凳跳到另一个石凳的我莫名其妙地把下巴磕在了石桌上。爸爸急得连忙张罗送我上医院,并找来认识的主任大夫亲自给我缝针。不知道是吓傻了还是害怕挨骂,虽然血流满了毛衣前襟,我还是不停的安慰爸爸说我其实一点也不疼。缝针之后的几天我总算安分守己的呆在家里了,只是每次去医院换药的时候被护士小姐戏称为“下巴戴上了口罩的小姑娘”。
还好我的淘气多数是收敛在家的,但有的时候毕竟本性难移,在学校时偶尔也会原形毕露。小学时上自然课,我是班上胆子比较大的孩子之一。有次作青蛙和小鱼的解剖,和我一个小组的几乎都是女孩子,手中的“屠刀”自然不敢对活蹦乱跳的小鱼小蛙划下去, 全都缩到了桌子的另一边。我对几位“淑女”不客气的嘲弄了一番,满不在乎的“磨刀霍霍向鱼蛙”。这种兴趣和大胆也许就是我对以后职业的选择奠定的第一步吧。
还记得有段时间我迷上了香港卫视中文台播放的日本动画片,为此没少和放学后强行把我们几个女孩子留在学校排练节目的班长抱怨。 现在想想,为了集体的幸福,我当时牺牲了多少宝贵的动画片段啊。更过分的是初中一年级有一次放学召开班干部会议,我心里正如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惦记着五点半播放的“足球小子”的大结局。班主任看我一副坐立不安着急上火的模样,问我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我少根筋的坦白了真实原因,愣把四十多岁的班主任气得目瞪口呆。凡此种种,今天想起来真是有些汗颜。 记得班上有段时间时兴男女生之间互相捉弄,可怜的我自然没能幸免。最最令我不爽的是每次打完预防针总被同桌的男孩(他坐我左边)威胁要捏我刚刚挨了一针的左边胳膊(右手要留着写字), 不过终于在一次因为流感和乙肝疫苗同时注射所以两只胳膊都没能幸免的情况下被我痛快的以牙还牙,这位仁兄立时当着全班的面含泪呲牙咧嘴。该生随后伺机报复,一日课间趁我在专心苦读课外书的时候将一只表面附满茸毛,可以以假乱真的塑料蜘蛛下降到我眼前。我大惊,猛然窜起后闪,将该男连同后边一排探头等待看热闹的家伙撞倒在地,顿时一片哎呀声起伏。待我惊魂未定的从地上爬起,可怜的同桌还倒在地上捧着被我一屁股坐到的小腿狂揉,我对其怒目相视,遂补上一脚。正是因为我出了名的调皮捣蛋,班主任又特别喜欢温柔文静的女孩(比如班长),所以无缘于她老人家的“专宠”名单,但是大概因为我成绩不错,她对我还是比较容忍的。
每年最最开心的事就是寒假或者暑假的时候随妈妈去北京探亲, 因而享受了无数每个孩子都“爱不释口”的美食,如豌豆黄,奶油炸糕,素什锦,山楂糕,果丹皮,小豆羊羹, 驴打滚, 栗子面小窝头…数不胜数,所以我这个馋虫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最难以忘怀的是九一年寒假在西单附近吃了一次“加州牛肉面”,外面干冷的北风和面前香喷喷,热气腾腾的面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是来年再去却怎么也寻不到这个铺子了。来加拿大后我偶然对朋友们赞起,被告知其实加州是没有什么牛肉面的。
在北京度假时,因为嘴巴比较甜而且家里也没有别的和我同龄的孩子,众位长辈对我可谓是宠爱有嘉,我拍马屁的时候大人经常会以好吃的和露雪和瑞士巧克力勉之。我最早的马屁历史要追溯到两岁零八个月。 当然,我自己的记忆力可没有那么灵光,完全是引用了妈妈的口述。据说当时人小鬼大的我在刚刚到家的时候对着迎出来的姨姥姥亲亲热热地冲上去,“姨姥姥,我可想你了!” 姨姥姥乐得嘴都合不拢了,立马奖励了一个妈妈也想不起来的好吃的东西。这倒没什么,不过次日我依样画葫芦的对舅姥爷献媚道:“舅姥爷,我最想你了!”一旁的妈妈惊愕与我无师自通的马屁技术,不过我拒绝相信她的描述,我的印象中,自己因该是一个绝对乖巧的小姑娘,绝对不是一个如此“两面三刀”,“阴险狡诈”的人(即是妈妈的描述属实,那么我现在也早就“改过自新”,并且“重新做人”了。)
最近开学了,好忙好忙,只好仍在这里了。好有好多需要补充的,以后也应该把现在写进去,不过结尾先写好了。。。赫赫
我对自己的要求:面对生活,我坚韧开朗;面对困难,我勇往直前;对于理想,我执著追求;对于生命,我永不放弃。
写于来加十年。献给随我一路走来的父母家人,与我一同度过这些美好时光的朋友们,以及那些因为我的调皮捣蛋而遭殃的儿时伙伴,谢谢你们让我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可以珍藏,并觉得此时此刻如此温馨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