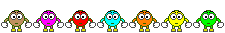高山上的营养补给的确是个大问题。全包团当然很好,不过体验是不一样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说实在的,你那小身子骨,太瘦了。登山太壮太廋都不行。如果你想下次还要低成本登山,肯定要进行大量训练,补充营养。
您正在使用一款已经过时的浏览器!部分功能不能正常使用。
请尝试升级或使用 其他浏览器。
请尝试升级或使用 其他浏览器。
阿凡“慕士塔格日记" (更新)
- 主题发起人 阿凡
- 开始时间
我们团有个肺部有疾病的人,医生让他坚持长跑。这家伙过去一年每星期跑40k, 最后花了9个小时登顶。长跑看来是都市生活没有其他条件训练的人增加心肺功能的道。确实,那样体验是不一样的。用直升机把人降落在8840米处,然后带着氧气上个几米也能登到珠峰顶。这样就没意思了。
不过,你平时应该健健身,吃的科学一些,涨涨肌肉。如果有条件,到低氧低压的地方训练一下心肺功能。
慕士塔格的回忆 – 后记
2017年7月5号 从新疆喀什出发,在慕士塔格历经19天的登山行程,之后几经辗转回到半个地球之外宁静祥和的渥太华,又经过十天休整之后我从一个喜马拉雅人褪了颜色变回都市常人。我感觉这二十多天好像穿越了一个漫长的世纪 – 从原本陌生却渐渐熟悉的近乎原始的生活,然后回到原本熟悉却渐渐陌生的现代日子;感觉似乎将自己大部分的灵魂都留在了七千米的海拔上;感觉有很多话想说却不知从何说起,感觉那一切似乎已经过去,却好像尚未终结。
2017的慕峰是我今生(准确地说是“我的前半生”)最为艰难的攀登,没有之一。慕峰也是我第一次攀登6000米以上白雪皑皑的山峰,没有之一;这是我第一次采取大本营以上全自助攀登的登山活动,没有之一;我也是整个慕峰大本营两百多位登山者中唯一一位登山滑雪的中国人,没有之一。
然而,这也是我第一次没有登顶的高海拔攀登。在第15天准备冲顶的时候,我顶着30公里的风,踩着滑雪板绕着巨大的“之”字路线,用完几乎最后一丝力气登到7002米高度时决定停止冲顶。等我滑降回C3营地的时候,全程一直领先全团的俄罗斯领队早就将雪板插在帐篷外边,他因为滑雪鞋老化加上大风造成脚部过快失温,一早就放弃了冲顶。而我竟然在脱下雪靴的时候才发觉四根手指的末梢已然失去触觉,很难想象如果继续冲顶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后经分析总结,登山滑雪虽然滑降时间短,但是由于慕峰各雪坡平均坡度都在30度以上,用滑雪板上升的时候需要比用雪鞋走更长的路线,而且雪板加上雪靴的重量又数倍于雪鞋,因此登山滑雪的体力消耗实际上要大于走直线的雪鞋攀登方式。
2017年7月5号 从新疆喀什出发,在慕士塔格历经19天的登山行程,之后几经辗转回到半个地球之外宁静祥和的渥太华,又经过十天休整之后我从一个喜马拉雅人褪了颜色变回都市常人。我感觉这二十多天好像穿越了一个漫长的世纪 – 从原本陌生却渐渐熟悉的近乎原始的生活,然后回到原本熟悉却渐渐陌生的现代日子;感觉似乎将自己大部分的灵魂都留在了七千米的海拔上;感觉有很多话想说却不知从何说起,感觉那一切似乎已经过去,却好像尚未终结。
2017的慕峰是我今生(准确地说是“我的前半生”)最为艰难的攀登,没有之一。慕峰也是我第一次攀登6000米以上白雪皑皑的山峰,没有之一;这是我第一次采取大本营以上全自助攀登的登山活动,没有之一;我也是整个慕峰大本营两百多位登山者中唯一一位登山滑雪的中国人,没有之一。
然而,这也是我第一次没有登顶的高海拔攀登。在第15天准备冲顶的时候,我顶着30公里的风,踩着滑雪板绕着巨大的“之”字路线,用完几乎最后一丝力气登到7002米高度时决定停止冲顶。等我滑降回C3营地的时候,全程一直领先全团的俄罗斯领队早就将雪板插在帐篷外边,他因为滑雪鞋老化加上大风造成脚部过快失温,一早就放弃了冲顶。而我竟然在脱下雪靴的时候才发觉四根手指的末梢已然失去触觉,很难想象如果继续冲顶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后经分析总结,登山滑雪虽然滑降时间短,但是由于慕峰各雪坡平均坡度都在30度以上,用滑雪板上升的时候需要比用雪鞋走更长的路线,而且雪板加上雪靴的重量又数倍于雪鞋,因此登山滑雪的体力消耗实际上要大于走直线的雪鞋攀登方式。
让我该如何描述你呢,我所亲历的慕士塔格? 那每一个清晨掀开帐篷迎面而来夹杂着冰雪却无比清新的风,那每一个傍晚在高山营帐外的气炉里渐渐融化的白雪,那每一晚不管外面如何风雪肆虐拉上睡袋拉链后只露出鼻口呼吸的温暖,那每一步攀登前行所伴随的沉重的呼吸和无数次默默的计数,还有大本营区晒得黝黑却挂满温暖笑容的一张张脸庞,那遮得严严实实却藏不住的眼神里流露出遇到山友的热诚,那些在伙房大帐里互不问姓甚名谁只问缘何热爱攀登哪一座会是下一座的对话,还有那在最后500 米之上时而慈祥时而威严的让我看得见却未缘一面的慕峰之巅。
记得准备冲顶前的一个晚上,我去乔戈里登山队的大帐里找山友闲聊,在和十几个登山爱好者寒喧一圈之后,和一个来自台湾的职业登山向导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你平时都在哪里组织登山?”我问道,心里想回答大约不是喜马拉雅,就是天山昆仑之类的高山吧。能来慕峰做高山协作的可都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的履历里大多有8000米的经验。
“主要就在台湾啊,偶尔有组织去韩国日本那边登山。”
“台湾的山海拔都不高吧?”,我很难想象一个以登山向导为职业的人居然主要的活动地区是在台湾那样的小岛。
“台湾的山海拔虽然不算很高,但是3、4千米的山也不少。而且台湾70%的地方都是山区,很适合组织登山活动。”,她表情淡定地喝了一口茶,然后突然回问一句:“为什么你们只是对海拔这么有兴趣呢?我觉得不管登多高海拔的山都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啊。”
记得准备冲顶前的一个晚上,我去乔戈里登山队的大帐里找山友闲聊,在和十几个登山爱好者寒喧一圈之后,和一个来自台湾的职业登山向导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你平时都在哪里组织登山?”我问道,心里想回答大约不是喜马拉雅,就是天山昆仑之类的高山吧。能来慕峰做高山协作的可都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的履历里大多有8000米的经验。
“主要就在台湾啊,偶尔有组织去韩国日本那边登山。”
“台湾的山海拔都不高吧?”,我很难想象一个以登山向导为职业的人居然主要的活动地区是在台湾那样的小岛。
“台湾的山海拔虽然不算很高,但是3、4千米的山也不少。而且台湾70%的地方都是山区,很适合组织登山活动。”,她表情淡定地喝了一口茶,然后突然回问一句:“为什么你们只是对海拔这么有兴趣呢?我觉得不管登多高海拔的山都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啊。”
后来才知道,这位向导两年前曾经在吉尔吉斯斯坦登山的时候坠入冰裂缝,造成腿部神经受损,经历一年的康复之后,带着10%的神经尚未复元的双脚重新带队登山。她的经历让帐篷里所有的山友们都感到肃然起敬。而她那句反问也让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坦白说尝试体验一个新的海拔高度的确是我的主要登山目的。我也不得不承认对于每一座曾经,现在,和未来想攀登的高山之巅都抱有强烈的欲望。可是我也能隐约感觉到这种对海拔高度的过度关注也许在不经意间削弱了登山本身带给我的那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感受:事后回想这次登顶未果的结局,是否让我一时淡忘了在这二十天时间里,渺小的自己置身于浩瀚的慕峰之上那些包含着痛苦和喜悦、纠结和超脱、期望与实现的体验和经历?是否让我不去感念在白茫茫一片雪雾中陌生人递过来一杯热腾腾的姜茶?是否仍然记得绝望坡上一小时上行100米的坚持和御风而行的纵情?是否,让这二十天不再成为今生最特别的一段日子?
登山,是一种无法用任何单一的词汇来概括的事情:那是碌碌凡尘间漫长岁月里抽离出来的一段让我感到特别的日子,那是自己的外在和自己的内心真正独处的片刻,那是很久很久之后岁月爬满眉头时让我依然觉得青春跃动的回忆,那是一个自己去开始自己去圆满的一个故事。登顶会是故事的一个完美结局,然而就算有没有这样的完美结局,曾经的一切情节都不应该被忘记。
因为,能够登山,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登山,是一种无法用任何单一的词汇来概括的事情:那是碌碌凡尘间漫长岁月里抽离出来的一段让我感到特别的日子,那是自己的外在和自己的内心真正独处的片刻,那是很久很久之后岁月爬满眉头时让我依然觉得青春跃动的回忆,那是一个自己去开始自己去圆满的一个故事。登顶会是故事的一个完美结局,然而就算有没有这样的完美结局,曾经的一切情节都不应该被忘记。
因为,能够登山,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慕士塔格的回忆 – 开始冲顶
7月16日
从7月12号拉练结束那天之后,慕峰天气急转直下,连续数日的大风将大本营区所有团队的人都牢牢地圈定在营区。艾尚峰登山团队ABC三组50多人都在焦急的等待天气的好转。大队长李渊每天都呆在指挥中心收集各种预报信息,他的营帐也成了我最经常去拜访打探消息的地方。
“所有的网站上的预报都说18号之后天气会好转。”,李队头上蒙着登山巾,手里一直都拿着手机或者对讲机,眼前摊着一大桌子的电子器材和通讯设备,整个一前线指战员的范儿,哭笑着说道:“但是我有一个气象专家朋友却告诉我19号天气会变得更坏,倒是这两三天是相对好一些的天气。如此矛盾的预报让我也很矛盾,我只好把各个队都先召集到这里,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准备开始冲顶。”
相比中国登山队的条件,我们国际登山团要落后很多,除了通过慕峰大本营区一带和天气一样变幻莫测、时有时无的手机信号查询网络预报,还需要靠领队的经验对天气趋势作出判断。海拔6000米以上的高海拔雪山天气瞬息万变,风速往往暗示着各种可能的天气变化,也是决定是否冲顶最主要的因素。经验丰富的登山者通过观测顶峰上方飘动的云层(也称为“旗云”)移动方向和速度,可以大致知道顶峰一带的风速条件是否适合在最近几天内冲顶。
“We wait, and we will see. ”,连续几天山顶的云都在自西向东飞速疾行( 连我都看出来不是时机),俄国领队始终用这样简短的回答告诉焦急等待冲顶的团员们。我们也用完了三天的天气机动时间,时刻准备冲顶的我们谁都不会去想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大本营吃吃喝喝看书睡午觉的好日子会成为让每个人怀念的美好时光。
终于在16号中午,久违的阳光普照营区,风速也大大降低,领队终于下达了进发C1的指令。用完午饭之后各小分队陆续向第一营地进发。按理说拉练阶段我们已经将必需品分别带到了C1和C2,大本营到C1轻装即可。可是经过几天休息后我感觉状态很好,于是把几乎能带上山的装备和器材都装进了背包,这额外多出来的几公斤重量却成为我最后下山时最痛苦的负担,此处按下不表。
经过数次拉练路线已经非常熟悉的C1在良好的天气情况下走起来十分轻松,我只用了2个半小时就到达营地。一边烧水做饭一边等待着夕阳西下。我们小组5人中年纪最大的米老头由于拉练阶段就没有完成C2,他决定明天只是尝试冲击C2营地即行下撤,于是我们打算拆掉两个比较结实的帐篷带到C2,留下最轻便的一顶帐篷存放保留物资。冲顶第一阶段感觉十分轻松的我又一次错过了放弃不必要装备尽量减轻负重的机会,把沉重的相机和备用的一套Goretex 衣裤塞入背包。以一种过于乐观的心情也把自己塞进了在C1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
7月16日
从7月12号拉练结束那天之后,慕峰天气急转直下,连续数日的大风将大本营区所有团队的人都牢牢地圈定在营区。艾尚峰登山团队ABC三组50多人都在焦急的等待天气的好转。大队长李渊每天都呆在指挥中心收集各种预报信息,他的营帐也成了我最经常去拜访打探消息的地方。
“所有的网站上的预报都说18号之后天气会好转。”,李队头上蒙着登山巾,手里一直都拿着手机或者对讲机,眼前摊着一大桌子的电子器材和通讯设备,整个一前线指战员的范儿,哭笑着说道:“但是我有一个气象专家朋友却告诉我19号天气会变得更坏,倒是这两三天是相对好一些的天气。如此矛盾的预报让我也很矛盾,我只好把各个队都先召集到这里,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准备开始冲顶。”
相比中国登山队的条件,我们国际登山团要落后很多,除了通过慕峰大本营区一带和天气一样变幻莫测、时有时无的手机信号查询网络预报,还需要靠领队的经验对天气趋势作出判断。海拔6000米以上的高海拔雪山天气瞬息万变,风速往往暗示着各种可能的天气变化,也是决定是否冲顶最主要的因素。经验丰富的登山者通过观测顶峰上方飘动的云层(也称为“旗云”)移动方向和速度,可以大致知道顶峰一带的风速条件是否适合在最近几天内冲顶。
“We wait, and we will see. ”,连续几天山顶的云都在自西向东飞速疾行( 连我都看出来不是时机),俄国领队始终用这样简短的回答告诉焦急等待冲顶的团员们。我们也用完了三天的天气机动时间,时刻准备冲顶的我们谁都不会去想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大本营吃吃喝喝看书睡午觉的好日子会成为让每个人怀念的美好时光。
终于在16号中午,久违的阳光普照营区,风速也大大降低,领队终于下达了进发C1的指令。用完午饭之后各小分队陆续向第一营地进发。按理说拉练阶段我们已经将必需品分别带到了C1和C2,大本营到C1轻装即可。可是经过几天休息后我感觉状态很好,于是把几乎能带上山的装备和器材都装进了背包,这额外多出来的几公斤重量却成为我最后下山时最痛苦的负担,此处按下不表。
经过数次拉练路线已经非常熟悉的C1在良好的天气情况下走起来十分轻松,我只用了2个半小时就到达营地。一边烧水做饭一边等待着夕阳西下。我们小组5人中年纪最大的米老头由于拉练阶段就没有完成C2,他决定明天只是尝试冲击C2营地即行下撤,于是我们打算拆掉两个比较结实的帐篷带到C2,留下最轻便的一顶帐篷存放保留物资。冲顶第一阶段感觉十分轻松的我又一次错过了放弃不必要装备尽量减轻负重的机会,把沉重的相机和备用的一套Goretex 衣裤塞入背包。以一种过于乐观的心情也把自己塞进了在C1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
慕士塔格日记 – 冲顶 (C1- C2)
7月17日
高山上的日子永远睡不够。感觉就眯合了一会而眼,从太阳下山的晚10点到太阳升起的早10点,整整12小时忽悠一下就过去了。掀开帐篷帘子,昨儿才停歇了大半天的风又一次呼啸而来,温度明显下降。由于今天需要将两个营地全部拆掉准备带到第三营地,而且要负重爬升和穿越整个慕峰攀登中技术难度最大的冰裂缝地区,风速又比较高,因此需要比拉练时期C1 上C2预留更多的时间。没有太多时间重新烧融冰雪冲配早餐,直接将昨晚放在帐篷外速冻的半袋Chicken Teriyaki 热一下就当作今天的早餐加午饭,顶着凌乱的风拆好帐篷打包好装备,已经是中午12点的样子。
高山营地的位置选择是登顶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我们的C1 建立的高度较低,只有5200米,虽然给初次建营带来了便利条件,却要求在之后上升C2时海拔提升接近1000米。相比之下,中国登山团在海拔5600 米建立的高C1永久营区位置更加合理 – 尽管从大本营到高C1费时更长一些,但是由于这一阶段海拔不高,队员体力也更加充沛。而且从高C1上升C2也容易一些。我团不少队员都认为要是我们一开始也将营地建在高C1附近的位置,则会对后半程冲顶的体力分配更加有利。
出发没多久,我就面临一个问题。连日的大风已经将我的营地和高C1这一段大雪坡表层的积雪吹刮得所剩无几,加上这个海拔地带的积雪白天日晒融化之后,夜晚气温骤降冻成十分不利于登山滑雪板止滑带上行的冻雪表层。给没有配制雪板齿状冰爪(ski crampon)的我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止滑带在坚硬冻雪表面上容易发生侧滑和倒滑,迫使我不得不多次绕道避开冰冻面,四处寻找尚存少量积雪的坡面上行。这一段消耗了不少体力,心想要是昨天趁天气好气温高的时候多花点时间将营帐扎到5600的话应该是个明智的决定。
7月17日
高山上的日子永远睡不够。感觉就眯合了一会而眼,从太阳下山的晚10点到太阳升起的早10点,整整12小时忽悠一下就过去了。掀开帐篷帘子,昨儿才停歇了大半天的风又一次呼啸而来,温度明显下降。由于今天需要将两个营地全部拆掉准备带到第三营地,而且要负重爬升和穿越整个慕峰攀登中技术难度最大的冰裂缝地区,风速又比较高,因此需要比拉练时期C1 上C2预留更多的时间。没有太多时间重新烧融冰雪冲配早餐,直接将昨晚放在帐篷外速冻的半袋Chicken Teriyaki 热一下就当作今天的早餐加午饭,顶着凌乱的风拆好帐篷打包好装备,已经是中午12点的样子。
高山营地的位置选择是登顶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我们的C1 建立的高度较低,只有5200米,虽然给初次建营带来了便利条件,却要求在之后上升C2时海拔提升接近1000米。相比之下,中国登山团在海拔5600 米建立的高C1永久营区位置更加合理 – 尽管从大本营到高C1费时更长一些,但是由于这一阶段海拔不高,队员体力也更加充沛。而且从高C1上升C2也容易一些。我团不少队员都认为要是我们一开始也将营地建在高C1附近的位置,则会对后半程冲顶的体力分配更加有利。
出发没多久,我就面临一个问题。连日的大风已经将我的营地和高C1这一段大雪坡表层的积雪吹刮得所剩无几,加上这个海拔地带的积雪白天日晒融化之后,夜晚气温骤降冻成十分不利于登山滑雪板止滑带上行的冻雪表层。给没有配制雪板齿状冰爪(ski crampon)的我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止滑带在坚硬冻雪表面上容易发生侧滑和倒滑,迫使我不得不多次绕道避开冰冻面,四处寻找尚存少量积雪的坡面上行。这一段消耗了不少体力,心想要是昨天趁天气好气温高的时候多花点时间将营帐扎到5600的话应该是个明智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