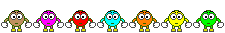您正在使用一款已经过时的浏览器!部分功能不能正常使用。
请尝试升级或使用 其他浏览器。
请尝试升级或使用 其他浏览器。
给我一条波斯米亚红裙
- 主题发起人 让我拥抱你
- 开始时间
- 注册
- 2014-04-15
- 消息
- 6,048
- 荣誉分数
- 11,373
- 声望点数
- 1,323
拥抱, 恕我直言: 觉得没有一句有真正的人情味。这些是今天这个年代只看利益的那种人。 这可不是那个年代的人。那个年代的人朴素,善良,正直。当然也有最大的投机者 。。。。。这么自私自利的人, 可能不会冒着危险为靳凡传递信息。 靳凡是重犯, 接触他和为他传信都是一般人绝不会做的。 既然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人品高尚, 刚毅,正直,善良的人。 靳凡身陷囹圄,蓬头垢面, 没有舞台让他展示, 他有什么魅力呢? 他的魅力是他内心的刚毅和热情执着。仅供拥抱参考。 好的小说要写到骨头里,谓之入木三分。看到拥抱已经开始展开写众多人物,几个时代的故事了。 是一个挺大的跨越。 希望拥抱写好。我觉得她有三种可能,一种是说,靳凡在监狱里挺好的,将来出狱来看你和孩子。一种是说,靳凡在监狱里死了,死前让我来看看你。一种是说,你也嫁人了,我跟靳凡在监狱里好了,你以后别惦记他了。
期望看到拥抱把舞蹈的魂,艺术的灵魂,舞蹈者人生的灵魂能展现出来。往往艺高者德馨; 在艺术人生里,有很多那个年代的人, 他们感人的故事可以佐证。。。。。。
- 注册
- 2010-04-24
- 消息
- 33,189
- 荣誉分数
- 17,601
- 声望点数
- 1,373
谢谢一尘。说得都很中肯很对。拥抱, 恕我直言: 觉得没有一句有真正的人情味。这些是今天这个年代只看利益的那种人。 这可不是那个年代的人。那个年代的人朴素,善良,正直。当然也有最大的投机者 。。。。。这么自私自利的人, 可能不会冒着危险为靳凡传递信息。 靳凡是重犯, 接触他和为他传信都是一般人绝不会做的。 既然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人品高尚, 刚毅,正直,善良的人。 靳凡身陷囹圄,蓬头垢面, 没有舞台让他展示, 他有什么魅力呢? 他的魅力是他内心的刚毅和热情执着。仅供拥抱参考。 好的小说要写到骨头里,谓之入木三分。看到拥抱已经开始展开写众多人物,几个时代的故事了。 是一个挺大的跨越。 希望拥抱写好。
期望看到拥抱把舞蹈的魂,艺术的灵魂,舞蹈者人生的灵魂能展现出来。往往艺高者德馨; 在艺术人生里,有很多那个年代的人, 他们感人的故事可以佐证。。。。。。
那个年代的人,的确是比较重情义和感情,也没受那么多金钱和物质的污染,比现在的人纯洁和简单一些。
“把舞蹈的魂,艺术的灵魂,舞蹈者人生的灵魂能展现出来”,这个说得很对。这篇小说,爱情是一条线,但是应该是一条副线,主线应该是对艺术的不懈追求。
- 注册
- 2010-04-24
- 消息
- 33,189
- 荣誉分数
- 17,601
- 声望点数
- 1,373
十九
一片灰蒙蒙的光透过楼门上的玻璃照进来,给昏暗的楼道增添了一种迷蒙而不真实的色彩。推开芭蕾舞团办公大楼的厚重的楼门,外面的强光一下照射过来,让她的眼睛有些不适应。门边的墙上贴着一张芭蕾舞团面试的通知,上面有一个黑色的箭头指向楼内。院外传来钻机钻地的突突声,一阵阵粉尘从院外飘过来,伴随着公共汽车行驶的声音,摩托车的尾气喷管发出的嘟嘟声和三轮车的发锈的铁链子的产生的嘎吱声。楼外的喧嚣和楼内的安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迎面扑来的闷热的空气和噪音让她感觉好象是走进了另外的一个世界。明宵背着她的书包走在前面,迈下了门口的宽宽的灰色水泥台阶。她一手提着红裙,一手拿着自己的绿裙子,低头看着脚底下的台阶,跟着明宵向下走。
一辆停在门口的银灰色的中型轿车的门打开了,上面下来几个人,其中一个看着有六十多岁的白了头发的男人在几个人的簇拥下拾阶而上,正好跟向下走的她和明宵打了个照面。男人身穿一件笔挺的深蓝色中山装,裤线笔直,脚上是一双蒙了灰尘的黑色的皮鞋。与她擦肩而过时,男人锐利的眼睛看见了她身上穿的波希米亚红裙,突然停住了脚步。
姑娘,你是谁?是来参加面试的吗?男人回头问她说。
她没有答话,只是低头跟着明宵快步向着院门的方向走去。她不想在这里多耽搁。她还穿着这件红裙,刚才没敢在大楼里的洗手间里换衣服,因为怕芭蕾舞团的人发现靳凡被打,会追上来拦住他们,把他们抓起来。嗨,我们团长问你话呢,男人身后一个助理模样的年轻人对她说。我不是来面试的。她回身对着男人说了一声后,继续快步向着院门走去。
靳老,现在这些孩子真没礼貌,助理对男人说。您认识这孩子?
不认识,男人看着渐去渐远的红裙若有所思地说。只是这件裙子看着眼熟。
经过传达室的门口的时候,她看见看门大爷看着她身上的吊带红裙,对她微笑了一下。院门口有几个进门的人也都回过头来用赞叹地眼光看了一眼她身上的的红裙。她知道穿着这件裙子走在街上太扎眼,想赶紧把红裙换下来,但是大院门外是马路和院墙,看不见厕所和能换衣服的地方。一些建筑工人正在不远处施工,用钻机钻着路面,把街上弄得尘土飞扬。一辆公共汽车绕着路障从尘土中钻了出来,车上的人都捂着口鼻。他们快步走到自行车棚,找到了明宵的自行车。明宵把她的绿裙子塞进书包里,把书包斜背在身上。你就这么穿着吧,你穿着这件红裙特别好看,明宵一边俯身打开车锁一边对她说。别拿我开涮了,还不够丢人现眼的呢,她脸红了说。
这怎么了?好看又不丢人,明宵骑上车说。要我是你,就穿着这件裙子去王府井溜达一圈儿,专拣人多的地方走。
发觉你这人有时真讨厌哎,她紧跑两步蹿上了明宵的自行车说。没眼力见,不分时间场合开玩笑。看不出人家心里很难受吗?劳驾,赶紧帮我找个地儿换衣服。
真的好看,没拿你逗闷子,看着跟西班牙人似的,明宵说。前面不远就是陶然亭,我们去那里吧,公园里肯定有换衣服的地方。
在公园里林木茂密的僻静处,明宵把一直替她背着的书包交给她,站在路边给她站着岗。她提着书包躲进小树林里,藏在一颗粗大的老槐树后,先把书包里塞着的绿裙子拿了出来,放在树下的绿草上。她把红裙的吊带从肩膀上顺着胳膊捋了下来,弯腰抬腿,把红裙从身上褪了下来。她把红裙对折了几下,放在书包上,随后拿起草地上的绿裙子,从头上套了下去。她把绿裙子拽平,把裙子侧面的拉链拉上,把折好的红裙塞回书包里,把书包扣带系上。她用手指拢了一下乱了的头发,抬头看见明宵正背对着她,站在树林边看着安静的湖水。波光粼粼的湖水把几束微光映照在明宵的刚毅的脸庞上。高高的个子,白净的皮肤,干净整洁的白衬衣,合身的蓝裤子,洗得干净的白球鞋,浓密而有些自来卷的头发,宽宽的脊背,倒三角的体型,长长的运动员一样的腿,站在湖边的明宵显得很帅气。
她站在树后看着明宵,有些看呆了。阳光帅气,家庭出身好,又要去美国上高中,将来要去学导演专业,去实现他的电影梦。她不知道怎么会遇见明宵,遇见这个白马王子一样的男孩。这几天,她的生活就好像天翻地覆了一样,完全改变了。明宵给她带来了一种变化,让她渴望自己变得更美更温柔。
明宵听见从背后传来的脚步声,转过身来,黑黑的眼睛看着她。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嫣然一笑,头微微低着,两手交叉着站在了明宵身旁。
换好了?明宵打量着她身上穿的绿裙子问。
嗯,她点头说。我们去哪里?
你想呢?
我想去复习数学,她抬头想了一下说。好几天了都没上补习班,怕下次去跟不上了。
那到我家里来吧,我帮你复习,明宵说。我数学最好了,教你没问题。你数学书带了吧?
她看了明宵一眼。她喜欢明宵请她去家里。她也喜欢去明宵家里。她喜欢坐在明宵家的客厅里,跟明宵单独在一起,听他的立体声录音机里传出来的乐曲,听他用带着磁性的声音讲话。她喜欢他的英俊,喜欢他的勇敢,也喜欢他帮着她做事情。虽然刚才他对靳凡下手狠了一些,但是他是为了给她出气才这样做的,她不但不想埋怨他,而且想感激他。但是她又有些莫名的担心和害怕。不是因为她不信任明宵,他对她说什么她都会相信,而是因为明宵说要她去他家,她的心里就有些发热和嗵嗵跳。过去她觉得男生女生单独去公园或者单独在一起就是小流氓,现在她就和明宵就单独在公园里,还要去他家。
嗯,带了,在书包里,她有些犹豫地说。你家里有人吗?别人看见了怎么办?
我爸妈都上班去了,家里没人,明宵毫不在乎地说。别人看见了又怎么了?我们是邻居,就不能串门吗?再说,我是帮你复习功课啊。
我是怕人说闲话,她依然有些担心地说。让居委会那些老太太们要是看见了,该有的没的乱嚼舌头了。
呵呵,你管她们呢,她们爱怎么着怎么着,明宵说。走,上我家去,看她们谁能把我们怎样。八杆子打不着的人,她们爱说什么就让她们说去。
他们沿着湖边走着。湖水微澜,映着阴阴的天空。空气有些闷热和潮湿,像是要下雨的感觉。她觉得浑身在发热,不知是因为天气还是因为跟明宵这样并肩在湖边走。她偷看了明宵几眼。聪颖的宽宽的额头,浓厚的眉毛,黑黑的带着睿智却又不失纯真的眼睛,高挺的鼻梁,骄傲的有些看不起人的嘴角,挺拔的身材和比自己高出一头的个儿,利索的打扮。明宵的精神和帅气都让她眼晕。
我跟你说啊,你穿上红裙跳舞的时候真的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一点儿也不像平时的你,明宵边走边说。别看我们打小在一幢楼里长大,过去还真对你不太了解,老觉得你是那个扎着小辫,手上脏兮兮的女孩,可没想到在舞台上,你穿着这条裙子,倍儿漂亮,简直认不出来了。
我没觉得啊。她假装谦虚地说,心里美滋滋的。
她心里盼望着明宵再夸她几句,从小到大没有人夸过她好看,明宵是第一个夸她的人。她一直觉得自己不好看,特别是自己的跳芭蕾的脚,平时她都是穿着袜子,不敢让人看到她的有些变形的脚趾。自从她发育之后,男孩子们看她的次数多了,但是从来没有人当面夸她好看。她渴望着别人告诉她,她是一个美丽的少女,渴望着从别人的嘴里证实自己是美丽的。
对自己特没自信吧?明宵说。真的我不骗你,向毛主席保证,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你要是去我们学校,肯定是校花了。
听到明宵这么说,她觉得自己的整个心都融化了,觉得自己在身不由己地掉入一个陷阱里去。一个甜蜜而温柔的陷阱。她跟着明宵走着,心里充满了快乐和兴奋,早上在芭蕾舞团发生的不快都已经全部云消雾散,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沿着湖边走着,好像是游荡在无人的城市的边缘,一切都变得很遥远,只有她和明宵很近。她对陶然亭不熟,除了小时跟父亲来这里滑过几次雪山之外,再也没有来过。她不知道明宵带着她走到哪里。对她来说,一切都是陌生的,包括明宵也是陌生的,她从昨天起才真正开始认识他。现在,他们在一个陌生的公园的湖边小径上走着,身影落在寂静的湖水里。即使明宵现在带着她走向天边,她也会闭着眼跟着去的。

站在四楼的玻璃窗口,看着女儿和男孩走出院门,靳凡用手绢堵住鼻子,觉得身体和心情都很难受。即使从穿着红裙的背影上看,走出院门的小曦也像是她母亲。没有阳光的天空显得很压抑,他看着女儿坐上了男孩的自行车,向着南面骑去,红裙像是一朵红色的火焰,在街上跳跃着,消失在视野之外。
他没有想到今天在这里会见到自己的女儿,更没有想到女儿会这样痛恨自己。比起肋骨上的伤痛,女儿对他的斥责更让他难受。但是他不想怪女儿。很多事,女儿不知道,也不懂。在女儿当面指责他的时候,他震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一直不知道自己最爱的那个人是为何自杀的。他只知道她死了。这么些年来,他一直觉得非常内疚和后悔,后悔把她带到了中国来,带入了绝境。他不想争辩,因为无论如何,爱人的死是跟他有关。无论怎样争辩,即使能澄清,也挽回不了一个已经逝去的生命。
他转过身来,走到四楼的洗手间,站在白色陶瓷洗手池边上,弯腰把脸上的血和鼻子里的血清洗干净。弯腰的时候,他觉得肋骨被踢的地方依然隐隐的疼,但是已经好多了,他用手按了按肋骨,发现没有被踢断。除了在监狱里,他还没有被别人这样打过。他掸了掸身上蹭上的尘土,把破了的西服脱下来,搭在臂弯上。他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除了脸颊上有一块青肿之外,别的伤都看不出来。
他走出洗手间,在走廊里找到了掉在地上的碎了的眼镜,和在墙角躺着的小黑乌龟。他把黑色的眼镜框和小黑乌龟捡了起来,一起扔到了剧场门口放着的一个垃圾箱里。他想起了女儿在小剧场舞台上跳的芭蕾。他没有想到女儿的芭蕾跳得这样好,这样有天分。一定要让小曦到芭蕾舞团来,他下定决心说。他忍着疼向楼下走去,在三楼的拐弯处遇见了匆匆向上爬的妻子。
你去哪里了,妻子喘着气抱怨说。说好休息二十分钟,都半个小时了,到处都找不到你。你是面试委员会主任,别人要是都像你一样迟到,你怎么管别人呢?
我去四楼休息了一下,他忍住肋骨的疼痛说。没注意时间过了。
脸上怎么了?妻子仔细盯着他的脸上的青肿问。让我看看。哎呦,都破了,疼不疼?怎么弄得?要不要马上去医务室去一趟?
刚才上楼时没注意摔了一下,他轻描淡写地说。没事儿,我先去主持面试,面试完了再去医务室。
那你赶紧先去排练厅吧,妻子说。我去把张大夫叫来给你看看。
快到明宵家的路上,突然下了一阵小雨。他们都没有带伞,只好在雨中狼狈地骑车。明宵的宽厚的肩膀成了一堵墙,替她挡住了前面的冷风和被风吹来的小雨点。也许是因为下雨的缘故,明宵家的楼门口没有人,这让她稍微宽心了一些。她在楼门口跳下车,跟着明宵进了楼门。明宵在前面一手提着车把,一手提着车的立梁,把二八锰钢自行车抬上了三楼,锁在楼道里。她跟在明宵后面,没有出声,在楼道拐弯时有时帮明宵举一下后车座。
第二次来到明宵的家里,她不像第一次那样害怕了,直接跟明宵进了门,在门口换了拖鞋。明宵看见她的头发和裙子都湿了,就进屋给她找了一条干净的齐头短裤和一件白衬衣让她换上,又给她拿了一条毛巾来擦头发。她去了洗手间,把有些湿漉漉的绿裙子脱了,搭在旁边的一个架子上,换上了明宵的衣服。她在脸盆里放了一些水,洗了把脸,把头发和脸都擦干净了,对着镜子照了照,咬了咬嘴唇,感觉清爽和舒服多了。
她走出洗手间来到客厅,看见沙发前的茶几上已经放着两杯酸梅汁和一盘西瓜,听见厨房里传来一阵声响。她走到厨房边上,探头向里面望去,看见明宵已经换好了一件白背心和一条蓝色运动短裤,正在煤气炉上烧一锅水。你忙活什么呢?她站在门口问明宵说。煮方便面,明宵扭头笑笑说。这种方便面的汤很好喝,不信一会儿你尝尝。你先客厅坐着去吧,方便面一会儿就好。
她回到客厅,就着盘子吃了一块西瓜,用桌上的一张纸巾擦了擦手,端着酸梅汁走到书架前。她看见明宵的书架上放着《安娜卡列尼娜》,《欧亨利短篇小说集》,《简爱》,《约翰克里斯多夫》,《悲惨世界》,《巴尔扎克全集》,《战争与和平》,《牛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与黑》,《复活》,《静静的顿河》,《三个火枪手》,几乎她能知道名字的外国小说都应有尽有。她觉得很惊讶,这个街道上的孩子王,怎么家里也这么多书。她把酸梅汁放在茶几上,从书架上抽出《安娜卡列尼娜》,站着翻了翻,没翻几页就入迷地读了起来。
方便面好了。明宵端着一碗打了鸡蛋和放入切碎了的西红柿的方便面走进客厅来,把碗放在茶几上说。
虽然听见了明宵的招呼,她依然恋恋不舍地读着《安娜卡列尼娜》,舍不得放下。自从去年中央台播放了英国拍摄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十集连续剧后,她一直想看看这本原著,但是一直没来得及看。
看什么呢,这么入迷?明宵走到她身边问。噢,《安娜》啊,很好的书,我很喜欢。
你怎么这么多书啊,她羡慕地问。你都看过吗?
差不多吧,明宵说。文革抄家的时候,别人的书都往外扔书,我妈特别喜欢外国文艺,就往回捡书。这书架上的大部分书都是我妈那时捡的,我在初中以前就读完了。
你妈胆子够大的啊,她说。
我们家出身好,根正苗红,不怕,明宵说。这些书,你要想看就随便拿,不过每次只能拿两本,看完再来换。
太好了,她欣喜地说。暑假正想好好读几本书呢。
赶紧吃面去吧,明宵催促她说。不然该坨了,你一会儿不是还想补习数学呢吗?
她把书放回书架,走回沙发边坐下。明宵回厨房给自己也端了一碗方便面和拿了两双筷子来,把一双筷子递给了她。路上淋了雨,喝着热乎的方便面,她觉得很舒服。她吃得很慢,明宵吃得快。明宵吃出了一身汗,站到客厅的电扇前,让摇头电扇吹着自己的身体。吃完方便面后,明宵把碗筷收拾回厨房,她从书包里把有些潮了的数学书摊开在茶几上,随后把一个铅笔盒掏出来也放在茶几上,用一把铅笔刀削铅笔。她一边削铅笔,眼睛一边心不在焉地看着厨房,不小心把左手的拇指削了一下。唉呦,她小声叫了一声,放下铅笔刀,用右手捏住了手指。怎么了?明宵在厨房听见了,跑出来看。怎么把手给削着了?明宵看着她的冒血的拇指心疼地说,转身去厨房的壁橱里翻着,找出了一卷纱布和云南白药来。明宵用云南白药给她的拇指伤处点上,用纱布小心地缠好。还疼吗?明宵问她说。不疼了,她说。我们学数学吧。
明宵坐在她身边,翻了翻她的数学书,开始给她讲数学。他讲完原理之后,很耐心地给她讲着书上的例题,然后帮她做习题。她觉得自己在数学上有些愚笨和不开窍,上课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也不好意思问老师。但是在明宵的讲解下,她突然觉得自己开窍了许多。一些看上去很难的问题,在明宵的耐心讲解下,也变得容易了。挨着明宵坐着,她也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她能闻见明宵身上和头发上散发出来的雨水的气味。她觉得明宵这么优秀,帅气,聪明,有理想有才华,任何一个女孩都会喜欢上他的,但是他却坐在她身边,耐心地帮着她做数学,还挺身而出,带着她去中央芭蕾舞团,帮她给母亲出气,对她还好。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她现在感觉到了那种万有引力一样的强烈的吸引力,开始明白母亲为什么会不怕危险,跟着自己的爱人到中国来。她在做习题的时候,明宵的腿有时会碰到她的腿,胳膊也有时会碰到她的裸露的手臂,每一次不经意的触碰都给她带来一种触电似的刺激和兴奋。她喜欢明宵的长跑运动员一样匀称的大腿和小腿。看见明宵英俊的脸庞,听见他的带有磁性的自信的声音,她的脸有时会突然一下变红,身体会颤抖一下,手心里会出一些汗。她尽量遮掩着自己,不想让明宵知道她对他的喜欢。
埋头做了三个小时的数学题之后,她觉得累了,不想继续做数学了。
放点儿音乐吧,她揉着手腕对明宵说。不想做了,手都做残了。
明宵走到客厅一角的音响前,把一盘《天鹅湖》放在里面,随后走回了她身边,继续坐在沙发上。双簧管吹出的柔和曲调,自客厅的角落向着四周弥漫,把他们引到了充满着荆棘与迷雾的天鹅湖畔。竖琴的琶音像是透彻的清泉自山间流下,弦乐器发出的震音和弦给屋子带来了一阵让人不安的忧郁。她沉浸在哀婉动人的旋律里,心里感到一阵悸动。你会跳《天鹅湖》吗?明宵突然问她说。会,她点头说。跳一段吧,你平时不是也自己练习吗?明宵说。可是我没有舞鞋,也没有合适的裙子,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推脱说。早上在小剧场不也没舞鞋,也跳的很好看吗?你就这样跳就挺好的,我很喜欢看,明宵说。好吧,她站起身来说。跳不好不许笑话我啊。
她带着一丝羞怯走到客厅中央,看了一眼明宵,两手下垂,左脚在前,右脚在后,踮起脚尖,摆了一个预备姿势。明宵目不斜视地看着她,脸上带着微笑,给她鼓着掌。她微笑了一下,挺起胸膛,两只手臂举起,越过头顶,弯成一个弧形,让两只手并拢的指尖在头顶上遥遥相对。随着缠绵悱恻的音乐,她像是变成了森林里的一只美丽的带着忧伤和彷徨的天鹅,在浓雾弥漫的湖边游荡着。她时而旋转,时而跃起,时而俯下身,像是一只纯洁美丽的白天鹅,带着无尽的哀伤和惆怅,在湖边游荡。一曲完毕,她停下脚步,看着坐在沙发上的明宵,两只手拽着想象中的裙角,做了一个优雅的谢幕的姿势。
跳得太好了,明宵使劲儿鼓掌说。真的跳得太好了,没想到你跳得这么好,比我在天桥剧场看到的芭蕾舞都好多了。你应该去芭蕾舞团,绝对应该去芭蕾舞团。
我不会去的,她摇头说。只要他在那里,我就不回去的。
真可惜,多少人打破脑袋都想进的中央芭蕾舞团,你居然机会到了手了都不去,明宵说。不过别担心,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电影导演的,到时你到我的电影里来跳芭蕾好了。
那你的第一部片子一定要让我来拍啊,她开玩笑说。
肯定的,明宵很认真地说。一言为定。
你真的要去美国上学吗?她问明宵说。
签证申请七月初都已经交上去了,明宵说。八月份应该就能拿到签证,订好机票,九月份开学就能去旧金山念书了。
这么快啊,她有些吃惊地说。还以为要有好长时间呢。
她突然觉得心情有些沮丧。她以为明宵至少要明年才能去美国,没想到他过完暑假就会走。难道她的命就是这样,刚喜欢一个人,不久就会分开?如果她能跟他一起去美国就好了,但是她知道,她去不了。她不敢想象明宵去了美国会怎样。她去不了美国,跟明宵隔着这么远,他恐怕渐渐就会把自己给忘记了。
她有些黯然地从客厅中间走回到沙发边坐下,端起酸梅汤来喝了一大口。她咽得急了一些,被呛了一口,咳嗽了起来。明宵递给了她一张纸巾,她擦了擦嘴,把纸巾放下,看了一眼窗外依旧阴郁的天空和墙上不断走着的表,觉得好像就要跟明宵分开了一样,心里很难受。
怎么了?明宵问她说。看你有些不开心。
没怎么,她勉强笑了一下说。没怎么。都快五点了,你爸妈也快回家了吧,我得走了,让他们看见怪不好的。我能把那本《安娜卡列尼娜》借走看看吗?
没问题,明宵爽快地答应说。明天我们还能见面吗?要不明天上午你到我家来,我继续给你补数学?
真不好意思,到你这里又是吃又是喝又是拿的,她一边把数学书和作业本收拾进书包一边说。
咱俩谁跟谁啊,你跟我还客气?明宵说。那就说好了,明天继续来我家好吧?我爸妈七点半就出门上班去了,之后什么时候来都行,我在家里等着你。手还疼吗?
不疼了。她从沙发上站起来,提起书包说。跟你学习,都忘了疼了,比上补习班强多了。
让我看看,明宵说。
她把左手伸出来给明宵看。明宵抓住她的手,把她的手指拉近眼前仔细看着。她觉得自己的手在明宵的手里,显得很柔软和软绵绵的。明宵用手指触摸着她的缠着纱布的大拇指。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把手抽出来。其实还有一点疼,她说。
她走到书架边,取下了《安娜卡列尼娜》那本书。书有上下两册,她把书塞进书包里。她走进洗手间,看了一眼晾在架子上的裙子。裙子还有些潮湿,但是可以穿了。她关上门,把明宵给她的白衬衣和短裤脱了下来,换上了自己的裙子。她打开洗手间的门,把衬衣和短裤还给明宵。她有些不好意思,觉得应该洗洗再还给明宵,但是她不能把明宵的衣服带回家。她有些恋恋不舍地跟明宵在门口道别,答应着第二天早上再来,然后背着鼓鼓囊囊的书包,转身飞快地跑下楼梯,回家去了。
靳凡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准备回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夕阳在天际留下了十几米宽的橙色的痕迹,消失在一片树梢之后。他把人事处的办公室门锁上,沿着一楼静悄悄的走廊来到了父亲的团长办公室。他习惯每天走之前来看看父亲走没走,有什么嘱咐没有。楼道有些昏暗,走到门口时,他看见办公室的灯已经亮了。靳凡轻轻推开门,走进了团长办公室。他看见花白了头发的父亲正坐在宽大的硬木办公桌后,在看着桌上的一份请示报告。办公桌摆着一部白色的电话,案头整齐地叠放着几落文件。爸,这么晚了您还在忙?靳凡走进办公桌问父亲说。今天的面试怎么样?父亲从办公桌后抬起头问他。
不太好。靳凡自己给自己拉了一把椅子在父亲对面坐下说。这两天都没有看见特别出色的,明天还有一天面试,再看看吧,不行只能矬子里拔将军了。
你期望太高了,父亲说。这都是全国的尖子,你还不满意啊?
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还是缺乏一些灵性和悟性,靳凡说。
我今天从外面开会回来,在门口遇见了一个穿着红裙的女孩,父亲放下手里的报告说。看到那条裙子的时候,我就想这孩子怎么也有一条这样的裙子,看着特别眼熟。
是小曦,她今天来了,靳凡说。
噢,是来面试吗?她的木匠爸爸不是不想让她见到你吗?
不是来面试,靳凡说。我也奇怪,可能是她自己听说了什么,知道了我在这里,就到了芭蕾舞团来。我在四楼小剧场看见一个女孩穿着一条红裙在跳舞,一下就认出了她。她跳得非常好,比我今天看见的所有的考生都跳得好。她太有芭蕾天分了,简直跟她母亲跳得一模一样。爸,我想让她直接来参加复试,您看行吗?
这孩子一看就灵气,长得也像她妈。你就让她直接来复试好了,我支持你,父亲微笑了一下说。
爸,有您的支持我就有底气了,靳凡说。不过小曦好像不太想来,可能因为她妈的去世,对我有一些怨气或者什么。
我们是对不起她妈,没能把她照顾好。父亲叹息说。她从苏联跟着你来到这里,我们都没想到后来会有文革,会发生那些事情。可是当时有什么办法呢?那时我在牛棚劳动改造,你在监狱,我们都见不到听不到消息。好在她后面嫁了一个好人,生下了小曦。但是谁也没想到几年之后她自己走了。她要是能坚持几年,也就能熬过去了。小曦是咱们家的孩子,母亲也去世了,咱们多照顾她,也是应该的。你想办法让她来吧,有这么好的条件,不来这里太可惜了。再说,她来了这里,你不就能总能见到她啦,也不用偷偷去看她了。我也会很高兴的。
我也是这么想,靳凡说。监狱的这十年把我的身体都毁了,年龄大了也生不了孩子了。咱家就只有小曦这么一个孩子,她喜欢芭蕾,咱们有这么好的条件,不把她好好培养多亏啊。我会想办法劝她来的。
文学城链接:
给我一条波希米亚红裙(十九)
一片灰蒙蒙的光透过楼门上的玻璃照进来,给昏暗的楼道增添了一种迷蒙而不真实的色彩。推开芭蕾舞团办公大楼的厚重的楼门,外面的强光一下照射过来,让她的眼睛有些不适应。门边的墙上贴着一张芭蕾舞团面试的通知,上面有一个黑色的箭头指向楼内。院外传来钻机钻地的突突声,一阵阵粉尘从院外飘过来,伴随着公共汽车行驶的声音,摩托车的尾气喷管发出的嘟嘟声和三轮车的发锈的铁链子的产生的嘎吱声。楼外的喧嚣和楼内的安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迎面扑来的闷热的空气和噪音让她感觉好象是走进了另外的一个世界。明宵背着她的书包走在前面,迈下了门口的宽宽的灰色水泥台阶。她一手提着红裙,一手拿着自己的绿裙子,低头看着脚底下的台阶,跟着明宵向下走。
一辆停在门口的银灰色的中型轿车的门打开了,上面下来几个人,其中一个看着有六十多岁的白了头发的男人在几个人的簇拥下拾阶而上,正好跟向下走的她和明宵打了个照面。男人身穿一件笔挺的深蓝色中山装,裤线笔直,脚上是一双蒙了灰尘的黑色的皮鞋。与她擦肩而过时,男人锐利的眼睛看见了她身上穿的波希米亚红裙,突然停住了脚步。
姑娘,你是谁?是来参加面试的吗?男人回头问她说。
她没有答话,只是低头跟着明宵快步向着院门的方向走去。她不想在这里多耽搁。她还穿着这件红裙,刚才没敢在大楼里的洗手间里换衣服,因为怕芭蕾舞团的人发现靳凡被打,会追上来拦住他们,把他们抓起来。嗨,我们团长问你话呢,男人身后一个助理模样的年轻人对她说。我不是来面试的。她回身对着男人说了一声后,继续快步向着院门走去。
靳老,现在这些孩子真没礼貌,助理对男人说。您认识这孩子?
不认识,男人看着渐去渐远的红裙若有所思地说。只是这件裙子看着眼熟。
经过传达室的门口的时候,她看见看门大爷看着她身上的吊带红裙,对她微笑了一下。院门口有几个进门的人也都回过头来用赞叹地眼光看了一眼她身上的的红裙。她知道穿着这件裙子走在街上太扎眼,想赶紧把红裙换下来,但是大院门外是马路和院墙,看不见厕所和能换衣服的地方。一些建筑工人正在不远处施工,用钻机钻着路面,把街上弄得尘土飞扬。一辆公共汽车绕着路障从尘土中钻了出来,车上的人都捂着口鼻。他们快步走到自行车棚,找到了明宵的自行车。明宵把她的绿裙子塞进书包里,把书包斜背在身上。你就这么穿着吧,你穿着这件红裙特别好看,明宵一边俯身打开车锁一边对她说。别拿我开涮了,还不够丢人现眼的呢,她脸红了说。
这怎么了?好看又不丢人,明宵骑上车说。要我是你,就穿着这件裙子去王府井溜达一圈儿,专拣人多的地方走。
发觉你这人有时真讨厌哎,她紧跑两步蹿上了明宵的自行车说。没眼力见,不分时间场合开玩笑。看不出人家心里很难受吗?劳驾,赶紧帮我找个地儿换衣服。
真的好看,没拿你逗闷子,看着跟西班牙人似的,明宵说。前面不远就是陶然亭,我们去那里吧,公园里肯定有换衣服的地方。
在公园里林木茂密的僻静处,明宵把一直替她背着的书包交给她,站在路边给她站着岗。她提着书包躲进小树林里,藏在一颗粗大的老槐树后,先把书包里塞着的绿裙子拿了出来,放在树下的绿草上。她把红裙的吊带从肩膀上顺着胳膊捋了下来,弯腰抬腿,把红裙从身上褪了下来。她把红裙对折了几下,放在书包上,随后拿起草地上的绿裙子,从头上套了下去。她把绿裙子拽平,把裙子侧面的拉链拉上,把折好的红裙塞回书包里,把书包扣带系上。她用手指拢了一下乱了的头发,抬头看见明宵正背对着她,站在树林边看着安静的湖水。波光粼粼的湖水把几束微光映照在明宵的刚毅的脸庞上。高高的个子,白净的皮肤,干净整洁的白衬衣,合身的蓝裤子,洗得干净的白球鞋,浓密而有些自来卷的头发,宽宽的脊背,倒三角的体型,长长的运动员一样的腿,站在湖边的明宵显得很帅气。
她站在树后看着明宵,有些看呆了。阳光帅气,家庭出身好,又要去美国上高中,将来要去学导演专业,去实现他的电影梦。她不知道怎么会遇见明宵,遇见这个白马王子一样的男孩。这几天,她的生活就好像天翻地覆了一样,完全改变了。明宵给她带来了一种变化,让她渴望自己变得更美更温柔。
明宵听见从背后传来的脚步声,转过身来,黑黑的眼睛看着她。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嫣然一笑,头微微低着,两手交叉着站在了明宵身旁。
换好了?明宵打量着她身上穿的绿裙子问。
嗯,她点头说。我们去哪里?
你想呢?
我想去复习数学,她抬头想了一下说。好几天了都没上补习班,怕下次去跟不上了。
那到我家里来吧,我帮你复习,明宵说。我数学最好了,教你没问题。你数学书带了吧?
她看了明宵一眼。她喜欢明宵请她去家里。她也喜欢去明宵家里。她喜欢坐在明宵家的客厅里,跟明宵单独在一起,听他的立体声录音机里传出来的乐曲,听他用带着磁性的声音讲话。她喜欢他的英俊,喜欢他的勇敢,也喜欢他帮着她做事情。虽然刚才他对靳凡下手狠了一些,但是他是为了给她出气才这样做的,她不但不想埋怨他,而且想感激他。但是她又有些莫名的担心和害怕。不是因为她不信任明宵,他对她说什么她都会相信,而是因为明宵说要她去他家,她的心里就有些发热和嗵嗵跳。过去她觉得男生女生单独去公园或者单独在一起就是小流氓,现在她就和明宵就单独在公园里,还要去他家。
嗯,带了,在书包里,她有些犹豫地说。你家里有人吗?别人看见了怎么办?
我爸妈都上班去了,家里没人,明宵毫不在乎地说。别人看见了又怎么了?我们是邻居,就不能串门吗?再说,我是帮你复习功课啊。
我是怕人说闲话,她依然有些担心地说。让居委会那些老太太们要是看见了,该有的没的乱嚼舌头了。
呵呵,你管她们呢,她们爱怎么着怎么着,明宵说。走,上我家去,看她们谁能把我们怎样。八杆子打不着的人,她们爱说什么就让她们说去。
他们沿着湖边走着。湖水微澜,映着阴阴的天空。空气有些闷热和潮湿,像是要下雨的感觉。她觉得浑身在发热,不知是因为天气还是因为跟明宵这样并肩在湖边走。她偷看了明宵几眼。聪颖的宽宽的额头,浓厚的眉毛,黑黑的带着睿智却又不失纯真的眼睛,高挺的鼻梁,骄傲的有些看不起人的嘴角,挺拔的身材和比自己高出一头的个儿,利索的打扮。明宵的精神和帅气都让她眼晕。
我跟你说啊,你穿上红裙跳舞的时候真的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一点儿也不像平时的你,明宵边走边说。别看我们打小在一幢楼里长大,过去还真对你不太了解,老觉得你是那个扎着小辫,手上脏兮兮的女孩,可没想到在舞台上,你穿着这条裙子,倍儿漂亮,简直认不出来了。
我没觉得啊。她假装谦虚地说,心里美滋滋的。
她心里盼望着明宵再夸她几句,从小到大没有人夸过她好看,明宵是第一个夸她的人。她一直觉得自己不好看,特别是自己的跳芭蕾的脚,平时她都是穿着袜子,不敢让人看到她的有些变形的脚趾。自从她发育之后,男孩子们看她的次数多了,但是从来没有人当面夸她好看。她渴望着别人告诉她,她是一个美丽的少女,渴望着从别人的嘴里证实自己是美丽的。
对自己特没自信吧?明宵说。真的我不骗你,向毛主席保证,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你要是去我们学校,肯定是校花了。
听到明宵这么说,她觉得自己的整个心都融化了,觉得自己在身不由己地掉入一个陷阱里去。一个甜蜜而温柔的陷阱。她跟着明宵走着,心里充满了快乐和兴奋,早上在芭蕾舞团发生的不快都已经全部云消雾散,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沿着湖边走着,好像是游荡在无人的城市的边缘,一切都变得很遥远,只有她和明宵很近。她对陶然亭不熟,除了小时跟父亲来这里滑过几次雪山之外,再也没有来过。她不知道明宵带着她走到哪里。对她来说,一切都是陌生的,包括明宵也是陌生的,她从昨天起才真正开始认识他。现在,他们在一个陌生的公园的湖边小径上走着,身影落在寂静的湖水里。即使明宵现在带着她走向天边,她也会闭着眼跟着去的。
站在四楼的玻璃窗口,看着女儿和男孩走出院门,靳凡用手绢堵住鼻子,觉得身体和心情都很难受。即使从穿着红裙的背影上看,走出院门的小曦也像是她母亲。没有阳光的天空显得很压抑,他看着女儿坐上了男孩的自行车,向着南面骑去,红裙像是一朵红色的火焰,在街上跳跃着,消失在视野之外。
他没有想到今天在这里会见到自己的女儿,更没有想到女儿会这样痛恨自己。比起肋骨上的伤痛,女儿对他的斥责更让他难受。但是他不想怪女儿。很多事,女儿不知道,也不懂。在女儿当面指责他的时候,他震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一直不知道自己最爱的那个人是为何自杀的。他只知道她死了。这么些年来,他一直觉得非常内疚和后悔,后悔把她带到了中国来,带入了绝境。他不想争辩,因为无论如何,爱人的死是跟他有关。无论怎样争辩,即使能澄清,也挽回不了一个已经逝去的生命。
他转过身来,走到四楼的洗手间,站在白色陶瓷洗手池边上,弯腰把脸上的血和鼻子里的血清洗干净。弯腰的时候,他觉得肋骨被踢的地方依然隐隐的疼,但是已经好多了,他用手按了按肋骨,发现没有被踢断。除了在监狱里,他还没有被别人这样打过。他掸了掸身上蹭上的尘土,把破了的西服脱下来,搭在臂弯上。他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除了脸颊上有一块青肿之外,别的伤都看不出来。
他走出洗手间,在走廊里找到了掉在地上的碎了的眼镜,和在墙角躺着的小黑乌龟。他把黑色的眼镜框和小黑乌龟捡了起来,一起扔到了剧场门口放着的一个垃圾箱里。他想起了女儿在小剧场舞台上跳的芭蕾。他没有想到女儿的芭蕾跳得这样好,这样有天分。一定要让小曦到芭蕾舞团来,他下定决心说。他忍着疼向楼下走去,在三楼的拐弯处遇见了匆匆向上爬的妻子。
你去哪里了,妻子喘着气抱怨说。说好休息二十分钟,都半个小时了,到处都找不到你。你是面试委员会主任,别人要是都像你一样迟到,你怎么管别人呢?
我去四楼休息了一下,他忍住肋骨的疼痛说。没注意时间过了。
脸上怎么了?妻子仔细盯着他的脸上的青肿问。让我看看。哎呦,都破了,疼不疼?怎么弄得?要不要马上去医务室去一趟?
刚才上楼时没注意摔了一下,他轻描淡写地说。没事儿,我先去主持面试,面试完了再去医务室。
那你赶紧先去排练厅吧,妻子说。我去把张大夫叫来给你看看。
快到明宵家的路上,突然下了一阵小雨。他们都没有带伞,只好在雨中狼狈地骑车。明宵的宽厚的肩膀成了一堵墙,替她挡住了前面的冷风和被风吹来的小雨点。也许是因为下雨的缘故,明宵家的楼门口没有人,这让她稍微宽心了一些。她在楼门口跳下车,跟着明宵进了楼门。明宵在前面一手提着车把,一手提着车的立梁,把二八锰钢自行车抬上了三楼,锁在楼道里。她跟在明宵后面,没有出声,在楼道拐弯时有时帮明宵举一下后车座。
第二次来到明宵的家里,她不像第一次那样害怕了,直接跟明宵进了门,在门口换了拖鞋。明宵看见她的头发和裙子都湿了,就进屋给她找了一条干净的齐头短裤和一件白衬衣让她换上,又给她拿了一条毛巾来擦头发。她去了洗手间,把有些湿漉漉的绿裙子脱了,搭在旁边的一个架子上,换上了明宵的衣服。她在脸盆里放了一些水,洗了把脸,把头发和脸都擦干净了,对着镜子照了照,咬了咬嘴唇,感觉清爽和舒服多了。
她走出洗手间来到客厅,看见沙发前的茶几上已经放着两杯酸梅汁和一盘西瓜,听见厨房里传来一阵声响。她走到厨房边上,探头向里面望去,看见明宵已经换好了一件白背心和一条蓝色运动短裤,正在煤气炉上烧一锅水。你忙活什么呢?她站在门口问明宵说。煮方便面,明宵扭头笑笑说。这种方便面的汤很好喝,不信一会儿你尝尝。你先客厅坐着去吧,方便面一会儿就好。
她回到客厅,就着盘子吃了一块西瓜,用桌上的一张纸巾擦了擦手,端着酸梅汁走到书架前。她看见明宵的书架上放着《安娜卡列尼娜》,《欧亨利短篇小说集》,《简爱》,《约翰克里斯多夫》,《悲惨世界》,《巴尔扎克全集》,《战争与和平》,《牛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与黑》,《复活》,《静静的顿河》,《三个火枪手》,几乎她能知道名字的外国小说都应有尽有。她觉得很惊讶,这个街道上的孩子王,怎么家里也这么多书。她把酸梅汁放在茶几上,从书架上抽出《安娜卡列尼娜》,站着翻了翻,没翻几页就入迷地读了起来。
方便面好了。明宵端着一碗打了鸡蛋和放入切碎了的西红柿的方便面走进客厅来,把碗放在茶几上说。
虽然听见了明宵的招呼,她依然恋恋不舍地读着《安娜卡列尼娜》,舍不得放下。自从去年中央台播放了英国拍摄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十集连续剧后,她一直想看看这本原著,但是一直没来得及看。
看什么呢,这么入迷?明宵走到她身边问。噢,《安娜》啊,很好的书,我很喜欢。
你怎么这么多书啊,她羡慕地问。你都看过吗?
差不多吧,明宵说。文革抄家的时候,别人的书都往外扔书,我妈特别喜欢外国文艺,就往回捡书。这书架上的大部分书都是我妈那时捡的,我在初中以前就读完了。
你妈胆子够大的啊,她说。
我们家出身好,根正苗红,不怕,明宵说。这些书,你要想看就随便拿,不过每次只能拿两本,看完再来换。
太好了,她欣喜地说。暑假正想好好读几本书呢。
赶紧吃面去吧,明宵催促她说。不然该坨了,你一会儿不是还想补习数学呢吗?
她把书放回书架,走回沙发边坐下。明宵回厨房给自己也端了一碗方便面和拿了两双筷子来,把一双筷子递给了她。路上淋了雨,喝着热乎的方便面,她觉得很舒服。她吃得很慢,明宵吃得快。明宵吃出了一身汗,站到客厅的电扇前,让摇头电扇吹着自己的身体。吃完方便面后,明宵把碗筷收拾回厨房,她从书包里把有些潮了的数学书摊开在茶几上,随后把一个铅笔盒掏出来也放在茶几上,用一把铅笔刀削铅笔。她一边削铅笔,眼睛一边心不在焉地看着厨房,不小心把左手的拇指削了一下。唉呦,她小声叫了一声,放下铅笔刀,用右手捏住了手指。怎么了?明宵在厨房听见了,跑出来看。怎么把手给削着了?明宵看着她的冒血的拇指心疼地说,转身去厨房的壁橱里翻着,找出了一卷纱布和云南白药来。明宵用云南白药给她的拇指伤处点上,用纱布小心地缠好。还疼吗?明宵问她说。不疼了,她说。我们学数学吧。
明宵坐在她身边,翻了翻她的数学书,开始给她讲数学。他讲完原理之后,很耐心地给她讲着书上的例题,然后帮她做习题。她觉得自己在数学上有些愚笨和不开窍,上课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也不好意思问老师。但是在明宵的讲解下,她突然觉得自己开窍了许多。一些看上去很难的问题,在明宵的耐心讲解下,也变得容易了。挨着明宵坐着,她也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她能闻见明宵身上和头发上散发出来的雨水的气味。她觉得明宵这么优秀,帅气,聪明,有理想有才华,任何一个女孩都会喜欢上他的,但是他却坐在她身边,耐心地帮着她做数学,还挺身而出,带着她去中央芭蕾舞团,帮她给母亲出气,对她还好。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她现在感觉到了那种万有引力一样的强烈的吸引力,开始明白母亲为什么会不怕危险,跟着自己的爱人到中国来。她在做习题的时候,明宵的腿有时会碰到她的腿,胳膊也有时会碰到她的裸露的手臂,每一次不经意的触碰都给她带来一种触电似的刺激和兴奋。她喜欢明宵的长跑运动员一样匀称的大腿和小腿。看见明宵英俊的脸庞,听见他的带有磁性的自信的声音,她的脸有时会突然一下变红,身体会颤抖一下,手心里会出一些汗。她尽量遮掩着自己,不想让明宵知道她对他的喜欢。
埋头做了三个小时的数学题之后,她觉得累了,不想继续做数学了。
放点儿音乐吧,她揉着手腕对明宵说。不想做了,手都做残了。
明宵走到客厅一角的音响前,把一盘《天鹅湖》放在里面,随后走回了她身边,继续坐在沙发上。双簧管吹出的柔和曲调,自客厅的角落向着四周弥漫,把他们引到了充满着荆棘与迷雾的天鹅湖畔。竖琴的琶音像是透彻的清泉自山间流下,弦乐器发出的震音和弦给屋子带来了一阵让人不安的忧郁。她沉浸在哀婉动人的旋律里,心里感到一阵悸动。你会跳《天鹅湖》吗?明宵突然问她说。会,她点头说。跳一段吧,你平时不是也自己练习吗?明宵说。可是我没有舞鞋,也没有合适的裙子,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推脱说。早上在小剧场不也没舞鞋,也跳的很好看吗?你就这样跳就挺好的,我很喜欢看,明宵说。好吧,她站起身来说。跳不好不许笑话我啊。
她带着一丝羞怯走到客厅中央,看了一眼明宵,两手下垂,左脚在前,右脚在后,踮起脚尖,摆了一个预备姿势。明宵目不斜视地看着她,脸上带着微笑,给她鼓着掌。她微笑了一下,挺起胸膛,两只手臂举起,越过头顶,弯成一个弧形,让两只手并拢的指尖在头顶上遥遥相对。随着缠绵悱恻的音乐,她像是变成了森林里的一只美丽的带着忧伤和彷徨的天鹅,在浓雾弥漫的湖边游荡着。她时而旋转,时而跃起,时而俯下身,像是一只纯洁美丽的白天鹅,带着无尽的哀伤和惆怅,在湖边游荡。一曲完毕,她停下脚步,看着坐在沙发上的明宵,两只手拽着想象中的裙角,做了一个优雅的谢幕的姿势。
跳得太好了,明宵使劲儿鼓掌说。真的跳得太好了,没想到你跳得这么好,比我在天桥剧场看到的芭蕾舞都好多了。你应该去芭蕾舞团,绝对应该去芭蕾舞团。
我不会去的,她摇头说。只要他在那里,我就不回去的。
真可惜,多少人打破脑袋都想进的中央芭蕾舞团,你居然机会到了手了都不去,明宵说。不过别担心,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电影导演的,到时你到我的电影里来跳芭蕾好了。
那你的第一部片子一定要让我来拍啊,她开玩笑说。
肯定的,明宵很认真地说。一言为定。
你真的要去美国上学吗?她问明宵说。
签证申请七月初都已经交上去了,明宵说。八月份应该就能拿到签证,订好机票,九月份开学就能去旧金山念书了。
这么快啊,她有些吃惊地说。还以为要有好长时间呢。
她突然觉得心情有些沮丧。她以为明宵至少要明年才能去美国,没想到他过完暑假就会走。难道她的命就是这样,刚喜欢一个人,不久就会分开?如果她能跟他一起去美国就好了,但是她知道,她去不了。她不敢想象明宵去了美国会怎样。她去不了美国,跟明宵隔着这么远,他恐怕渐渐就会把自己给忘记了。
她有些黯然地从客厅中间走回到沙发边坐下,端起酸梅汤来喝了一大口。她咽得急了一些,被呛了一口,咳嗽了起来。明宵递给了她一张纸巾,她擦了擦嘴,把纸巾放下,看了一眼窗外依旧阴郁的天空和墙上不断走着的表,觉得好像就要跟明宵分开了一样,心里很难受。
怎么了?明宵问她说。看你有些不开心。
没怎么,她勉强笑了一下说。没怎么。都快五点了,你爸妈也快回家了吧,我得走了,让他们看见怪不好的。我能把那本《安娜卡列尼娜》借走看看吗?
没问题,明宵爽快地答应说。明天我们还能见面吗?要不明天上午你到我家来,我继续给你补数学?
真不好意思,到你这里又是吃又是喝又是拿的,她一边把数学书和作业本收拾进书包一边说。
咱俩谁跟谁啊,你跟我还客气?明宵说。那就说好了,明天继续来我家好吧?我爸妈七点半就出门上班去了,之后什么时候来都行,我在家里等着你。手还疼吗?
不疼了。她从沙发上站起来,提起书包说。跟你学习,都忘了疼了,比上补习班强多了。
让我看看,明宵说。
她把左手伸出来给明宵看。明宵抓住她的手,把她的手指拉近眼前仔细看着。她觉得自己的手在明宵的手里,显得很柔软和软绵绵的。明宵用手指触摸着她的缠着纱布的大拇指。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把手抽出来。其实还有一点疼,她说。
她走到书架边,取下了《安娜卡列尼娜》那本书。书有上下两册,她把书塞进书包里。她走进洗手间,看了一眼晾在架子上的裙子。裙子还有些潮湿,但是可以穿了。她关上门,把明宵给她的白衬衣和短裤脱了下来,换上了自己的裙子。她打开洗手间的门,把衬衣和短裤还给明宵。她有些不好意思,觉得应该洗洗再还给明宵,但是她不能把明宵的衣服带回家。她有些恋恋不舍地跟明宵在门口道别,答应着第二天早上再来,然后背着鼓鼓囊囊的书包,转身飞快地跑下楼梯,回家去了。
靳凡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准备回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夕阳在天际留下了十几米宽的橙色的痕迹,消失在一片树梢之后。他把人事处的办公室门锁上,沿着一楼静悄悄的走廊来到了父亲的团长办公室。他习惯每天走之前来看看父亲走没走,有什么嘱咐没有。楼道有些昏暗,走到门口时,他看见办公室的灯已经亮了。靳凡轻轻推开门,走进了团长办公室。他看见花白了头发的父亲正坐在宽大的硬木办公桌后,在看着桌上的一份请示报告。办公桌摆着一部白色的电话,案头整齐地叠放着几落文件。爸,这么晚了您还在忙?靳凡走进办公桌问父亲说。今天的面试怎么样?父亲从办公桌后抬起头问他。
不太好。靳凡自己给自己拉了一把椅子在父亲对面坐下说。这两天都没有看见特别出色的,明天还有一天面试,再看看吧,不行只能矬子里拔将军了。
你期望太高了,父亲说。这都是全国的尖子,你还不满意啊?
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还是缺乏一些灵性和悟性,靳凡说。
我今天从外面开会回来,在门口遇见了一个穿着红裙的女孩,父亲放下手里的报告说。看到那条裙子的时候,我就想这孩子怎么也有一条这样的裙子,看着特别眼熟。
是小曦,她今天来了,靳凡说。
噢,是来面试吗?她的木匠爸爸不是不想让她见到你吗?
不是来面试,靳凡说。我也奇怪,可能是她自己听说了什么,知道了我在这里,就到了芭蕾舞团来。我在四楼小剧场看见一个女孩穿着一条红裙在跳舞,一下就认出了她。她跳得非常好,比我今天看见的所有的考生都跳得好。她太有芭蕾天分了,简直跟她母亲跳得一模一样。爸,我想让她直接来参加复试,您看行吗?
这孩子一看就灵气,长得也像她妈。你就让她直接来复试好了,我支持你,父亲微笑了一下说。
爸,有您的支持我就有底气了,靳凡说。不过小曦好像不太想来,可能因为她妈的去世,对我有一些怨气或者什么。
我们是对不起她妈,没能把她照顾好。父亲叹息说。她从苏联跟着你来到这里,我们都没想到后来会有文革,会发生那些事情。可是当时有什么办法呢?那时我在牛棚劳动改造,你在监狱,我们都见不到听不到消息。好在她后面嫁了一个好人,生下了小曦。但是谁也没想到几年之后她自己走了。她要是能坚持几年,也就能熬过去了。小曦是咱们家的孩子,母亲也去世了,咱们多照顾她,也是应该的。你想办法让她来吧,有这么好的条件,不来这里太可惜了。再说,她来了这里,你不就能总能见到她啦,也不用偷偷去看她了。我也会很高兴的。
我也是这么想,靳凡说。监狱的这十年把我的身体都毁了,年龄大了也生不了孩子了。咱家就只有小曦这么一个孩子,她喜欢芭蕾,咱们有这么好的条件,不把她好好培养多亏啊。我会想办法劝她来的。
文学城链接:
给我一条波希米亚红裙(十九)
最后编辑:
- 注册
- 2014-04-06
- 消息
- 8,609
- 荣誉分数
- 16,518
- 声望点数
- 1,323
用回忆的方式开篇这种结构不错,打破了正常时间顺序的单调感。读者好像看到了两列火车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站台出发,一列运行在少年懵懂的喜欢,一列运行在青春的错失,在有条不紊的叙述中将今昔和明宵之间的故事慢慢展开。十九
在百老汇与明宵重逢的那天晚上,他们坐在一间爱尔兰酒吧的吧台边的高脚凳上,坐得很近,几乎膝盖可以抵住膝盖。对面的乐池后面挂着一幅画,上面画着一个妖艳的女人,穿着一件银灰色的短大衣,里面是一条红色的衬衣配着火红的裙子,黑色的丝袜和紫色的长靴。这样的颜色搭配让她觉得有些别扭,虽然她也说不出别扭在哪里。调酒师扔过来一盒木质火柴。明宵伸手接过火柴盒,熟练地擦亮一只火柴。一股鲜艳的蓝红色火苗嚓地一声腾起。在红色的火焰闪烁下,明宵俯身点上一支烟,扭头看着她,英俊而成熟的脸上,依旧带着一股纯真和打小养成的自信的微笑。
你来纽约来得正好。明宵甩了两下火柴,把冒着残烟的烧焦了的黑褐色火柴棍按到混杂着一些烟蒂的烟灰缸里说。我正在筹划拍第一部片子,一部十五分钟的毕业短片,正缺一个女主角。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会在我的第一部片子里做女主角,现在是你的机会,你还愿意吗?
我愿意,她看着明宵的黑黑的眼瞳柔声说。我一直在等着这一天呢。
三个月之后,参加完明宵的毕业典礼的第二天,她不辞而别,自己去了肯尼迪机场。在乘坐出租车去机场前,她让出租车司机绕道带她去了一趟哥伦比亚大学,在明宵经常看书的一座咖啡馆前驶过。咖啡馆就坐落在哥大附近一幢浓荫遮盖爬满青藤的幽静的老楼边。她坐在出租车里透过车窗瞪大眼睛看着,远远的就已经看见了坐在咖啡馆外面座位上的明宵。他坐在石砌台阶旁的一张黑色小咖啡圆桌边,面前摊开着两本不断被风掀动的书,手里握着一杯咖啡,正懒散地跟旁边的两个同学聊天。八月的阳光流泻过他的全身,他带着开心的微笑,丝毫没有发觉一辆黄色出租车从面前缓缓驶过,里面有一个人隔着褐色的窗玻璃在看着他。她坐在车后座的暗影里,让出租车慢慢地走,好让她有时间仔细地看他一眼。虽然他头上戴的一顶蓝色垒球帽遮住了大部分头发,但是她依然可以从前额,耳边和脖颈上看见那一头浓黑的略微有些卷的头发。他的头发看上去很光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是早上刚刚洗过的样子。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带着竖条的衬衫,衬衫上系着一条蓝白道的领带,袖口上有一粒银色的扣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的长腿上是一条深蓝色的牛仔裤,裤腿在脚面上卷起一截,袜子是深灰色和白色的混合体,显得很厚。他的脚上是一双深棕色的船型鞋,鞋底是白色的,鞋面上也匝着一圈白色的边。
出租车缓缓地从咖啡馆前开过,驶过黑色的铁栅栏和浓密的绿树,驶过哥大校园的正门的两尊希腊式雕像,向着机场的方向驶去。她扭身回头从后车窗里看着远去的哥大校园的铁栅栏门,看着逐渐模糊的咖啡馆和明宵的身影,恍然觉得出租车行驶在时间的长河里,岁月像是逝去的飘着落红的湖水,在身边不断地流淌。
一片灰蒙蒙的光透过楼门上的玻璃照进来,给昏暗的楼道增添了一种迷蒙而不真实的色彩。推开芭蕾舞团办公大楼的厚重的楼门,外面的强光一下照射过来,让她的眼睛有些不适应。门边的墙上贴着一张芭蕾舞团面试的通知,上面有一个黑色的箭头指向楼内。院外传来钻机钻地的突突声,一阵阵粉尘从院外飘过来,伴随着公共汽车行驶的声音,摩托车的尾气喷管发出的嘟嘟声和三轮车的发锈的铁链子的产生的嘎吱声。楼外的喧嚣和楼内的安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迎面扑来的闷热的空气和噪音让她感觉好象是走进了另外的一个世界。明宵背着她的书包走在前面,迈下了门口的宽宽的灰色水泥台阶。她一手提着红裙,一手拿着自己的绿裙子,低头看着脚底下的台阶,跟着明宵向下走。
一辆停在门口的银灰色的中型轿车的门打开了,上面下来几个人,其中一个看着有六十多岁的白了头发的男人在几个人的簇拥下拾阶而上,正好跟向下走的她和明宵打了个照面。男人身穿一件笔挺的深蓝色中山装,裤线笔直,脚上是一双蒙了灰尘的黑色的皮鞋。与她擦肩而过时,男人锐利的眼睛看见了她身上穿的波希米亚红裙,突然停住了脚步。
姑娘,你是谁?是来参加面试的吗?男人回头问她说。
她没有答话,只是低头跟着明宵快步向着院门的方向走去。她不想在这里多耽搁。她还穿着这件红裙,刚才没敢在大楼里的洗手间里换衣服,因为怕芭蕾舞团的人发现靳凡被打,会追上来拦住他们,把他们抓起来。嗨,我们团长问你话呢,男人身后一个助理模样的年轻人对她说。我不是来面试的。她回身对着男人说了一声后,继续快步向着院门走去。
靳老,现在这些孩子真没礼貌,助理对男人说。您认识这孩子?
不认识,男人看着渐去渐远的红裙若有所思地说。只是这件裙子看着眼熟。
经过传达室的门口的时候,她看见看门大爷看着她身上的吊带红裙,对她微笑了一下。院门口有几个进门的人也都回过头来用赞叹地眼光看了一眼她身上的的红裙。她知道穿着这件裙子走在街上太扎眼,想赶紧把红裙换下来,但是大院门外是马路和院墙,看不见厕所和能换衣服的地方。一些建筑工人正在不远处施工,用钻机钻着路面,把街上弄得尘土飞扬。一辆公共汽车绕着路障从尘土中钻了出来,车上的人都捂着口鼻。他们快步走到自行车棚,找到了明宵的自行车。明宵把她的绿裙子塞进书包里,把书包斜背在身上。你就这么穿着吧,你穿着这件红裙特别好看,明宵一边俯身打开车锁一边对她说。别拿我开涮了,还不够丢人现眼的呢,她脸红了说。
这怎么了?好看又不丢人,明宵骑上车说。要我是你,就穿着这件裙子去王府井溜达一圈儿,专拣人多的地方走。
发觉你这人有时真讨厌哎,她紧跑两步蹿上了明宵的自行车说。没眼力见,不分时间场合开玩笑。看不出人家心里很难受吗?劳驾,赶紧帮我找个地儿换衣服。
真的好看,没拿你逗闷子,看着跟西班牙人似的,明宵说。前面不远就是陶然亭,我们去那里吧,公园里肯定有换衣服的地方。
在公园里林木茂密的僻静处,明宵把一直替她背着的书包交给她,站在路边给她站着岗。她提着书包躲进小树林里,藏在一颗粗大的老槐树后,先把书包里塞着的绿裙子拿了出来,放在树下的绿草上。她把红裙的吊带从肩膀上顺着胳膊捋了下来,弯腰抬腿,把红裙从身上褪了下来。她把红裙对折了几下,放在书包上,随后拿起草地上的绿裙子,从头上套了下去。她把绿裙子拽平,把裙子侧面的拉链拉上,把折好的红裙塞回书包里,把书包扣带系上。她用手指拢了一下乱了的头发,抬头看见明宵正背对着她,站在树林边看着安静的湖水。波光粼粼的湖水把几束微光映照在明宵的刚毅的脸庞上。高高的个子,白净的皮肤,干净整洁的白衬衣,合身的蓝裤子,洗得干净的白球鞋,浓密而有些自来卷的头发,宽宽的脊背,倒三角的体型,长长的运动员一样的腿,站在湖边的明宵显得很帅气。
她站在树后看着明宵,有些看呆了。阳光帅气,家庭出身好,又要去美国上高中,将来要去学导演专业,去实现他的电影梦。她不知道怎么会遇见明宵,遇见这个白马王子一样的男孩。这几天,她的生活就好像天翻地覆了一样,完全改变了。明宵给她带来了一种变化,让她渴望自己变得更美更温柔。
明宵听见从背后传来的脚步声,转过身来,黑黑的眼睛看着她。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嫣然一笑,头微微低着,两手交叉着站在了明宵身旁。
换好了?明宵打量着她身上穿的绿裙子问。
嗯,她点头说。我们去哪里?
你想呢?
我想去复习数学,她抬头想了一下说。好几天了都没上补习班,怕下次去跟不上了。
那到我家里来吧,我帮你复习,明宵说。我数学最好了,教你没问题。你数学书带了吧?
她看了明宵一眼。她喜欢明宵请她去家里。她也喜欢去明宵家里。她喜欢坐在明宵家的客厅里,跟明宵单独在一起,听他的立体声录音机里传出来的乐曲,听他用带着磁性的声音讲话。她喜欢他的英俊,喜欢他的勇敢,也喜欢他帮着她做事情。虽然刚才他对靳凡下手狠了一些,但是他是为了给她出气才这样做的,她不但不想埋怨他,而且想感激他。但是她又有些莫名的担心和害怕。不是因为她不信任明宵,他对她说什么她都会相信,而是因为明宵说要她去他家,她的心里就有些发热和嗵嗵跳。过去她觉得男生女生单独去公园或者单独在一起就是小流氓,现在她就和明宵就单独在公园里,还要去他家。
嗯,带了,在书包里,她有些犹豫地说。你家里有人吗?别人看见了怎么办?
我爸妈都上班去了,家里没人,明宵毫不在乎地说。别人看见了又怎么了?我们是邻居,就不能串门吗?再说,我是帮你复习功课啊。
我是怕人说闲话,她依然有些担心地说。让居委会那些老太太们要是看见了,该有的没的乱嚼舌头了。
呵呵,你管她们呢,她们爱怎么着怎么着,明宵说。走,上我家去,看她们谁能把我们怎样。八杆子打不着的人,她们爱说什么就让她们说去。
他们沿着湖边走着。湖水微澜,映着阴阴的天空。空气有些闷热和潮湿,像是要下雨的感觉。她觉得浑身在发热,不知是因为天气还是因为跟明宵这样并肩在湖边走。她偷看了明宵几眼。聪颖的宽宽的额头,浓厚的眉毛,黑黑的带着睿智却又不失纯真的眼睛,高挺的鼻梁,骄傲的有些看不起人的嘴角,挺拔的身材和比自己高出一头的个儿,利索的打扮。明宵的精神和帅气都让她眼晕。
我跟你说啊,你穿上红裙跳舞的时候真的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一点儿也不像平时的你,明宵边走边说。别看我们打小在一幢楼里长大,过去还真对你不太了解,老觉得你是那个扎着小辫,手上脏兮兮的女孩,可没想到在舞台上,你穿着这条裙子,倍儿漂亮,简直认不出来了。
我没觉得啊。她假装谦虚地说,心里美滋滋的。
她心里盼望着明宵再夸她几句,从小到大没有人夸过她好看,明宵是第一个夸她的人。她一直觉得自己不好看,特别是自己的跳芭蕾的脚,平时她都是穿着袜子,不敢让人看到她的有些变形的脚趾。自从她发育之后,男孩子们看她的次数多了,但是从来没有人当面夸她好看。她渴望着别人告诉她,她是一个美丽的少女,渴望着从别人的嘴里证实自己是美丽的。
对自己特没自信吧?明宵说。真的我不骗你,向毛主席保证,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你要是去我们学校,肯定是校花了。
听到明宵这么说,她觉得自己的整个心都融化了,觉得自己在身不由己地掉入一个陷阱里去。一个甜蜜而温柔的陷阱。她跟着明宵走着,心里充满了快乐和兴奋,早上在芭蕾舞团发生的不快都已经全部云消雾散,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沿着湖边走着,好像是游荡在无人的城市的边缘,一切都变得很遥远,只有她和明宵很近。她对陶然亭不熟,除了小时跟父亲来这里滑过几次雪山之外,再也没有来过。她不知道明宵带着她走到哪里。对她来说,一切都是陌生的,包括明宵也是陌生的,她从昨天起才真正开始认识他。现在,他们在一个陌生的公园的湖边小径上走着,身影落在寂静的湖水里。即使明宵现在带着她走向天边,她也会闭着眼跟着去的。
浏览附件514860
站在四楼的玻璃窗口,看着女儿和男孩走出院门,靳凡用手绢堵住鼻子,觉得身体和心情都很难受。即使从穿着红裙的背影上看,走出院门的小曦也像是她母亲。没有阳光的天空显得很压抑,他看着女儿坐上了男孩的自行车,向着南面骑去,红裙像是一朵红色的火焰,在街上跳跃着,消失在视野之外。
他没有想到今天在这里会见到自己的女儿,更没有想到女儿会这样痛恨自己。比起肋骨上的伤痛,女儿对他的斥责更让他难受。但是他不想怪女儿。很多事,女儿不知道,也不懂。在女儿当面指责他的时候,他震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一直不知道自己最爱的那个人是为何自杀的。他只知道她死了。这么些年来,他一直觉得非常内疚和后悔,后悔把她带到了中国来,带入了绝境。他不想争辩,因为无论如何,爱人的死是跟他有关。无论怎样争辩,即使能澄清,也挽回不了一个已经逝去的生命。
他转过身来,走到四楼的洗手间,站在白色陶瓷洗手池边上,弯腰把脸上的血和鼻子里的血清洗干净。弯腰的时候,他觉得肋骨被踢的地方依然隐隐的疼,但是已经好多了,他用手按了按肋骨,发现没有被踢断。除了在监狱里,他还没有被别人这样打过。他掸了掸身上蹭上的尘土,把破了的西服脱下来,搭在臂弯上。他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除了脸颊上有一块青肿之外,别的伤都看不出来。
他走出洗手间,在走廊里找到了掉在地上的碎了的眼镜,和在墙角躺着的小黑乌龟。他把黑色的眼镜框和小黑乌龟捡了起来,一起扔到了剧场门口放着的一个垃圾箱里。他想起了女儿在小剧场舞台上跳的芭蕾。他没有想到女儿的芭蕾跳得这样好,这样有天分。一定要让小曦到芭蕾舞团来,他下定决心说。他忍着疼向楼下走去,在三楼的拐弯处遇见了匆匆向上爬的妻子。
你去哪里了,妻子喘着气抱怨说。说好休息二十分钟,都半个小时了,到处都找不到你。你是面试委员会主任,别人要是都像你一样迟到,你怎么管别人呢?
我去四楼休息了一下,他忍住肋骨的疼痛说。没注意时间过了。
脸上怎么了?妻子仔细盯着他的脸上的青肿问。让我看看。哎呦,都破了,疼不疼?怎么弄得?要不要马上去医务室去一趟?
刚才上楼时没注意摔了一下,他轻描淡写地说。没事儿,我先去主持面试,面试完了再去医务室。
那你赶紧先去排练厅吧,妻子说。我去把张大夫叫来给你看看。
快到明宵家的路上,突然下了一阵小雨。他们都没有带伞,只好在雨中狼狈地骑车。明宵的宽厚的肩膀成了一堵墙,替她挡住了前面的冷风和被风吹来的小雨点。也许是因为下雨的缘故,明宵家的楼门口没有人,这让她稍微宽心了一些。她在楼门口跳下车,跟着明宵进了楼门。明宵在前面一手提着车把,一手提着车的立梁,把二八锰钢自行车抬上了三楼,锁在楼道里。她跟在明宵后面,没有出声,在楼道拐弯时有时帮明宵举一下后车座。
第二次来到明宵的家里,她不像第一次那样害怕了,直接跟明宵进了门,在门口换了拖鞋。明宵看见她的头发和裙子都湿了,就进屋给她找了一条干净的齐头短裤和一件白衬衣让她换上,又给她拿了一条毛巾来擦头发。她去了洗手间,把有些湿漉漉的绿裙子脱了,搭在旁边的一个架子上,换上了明宵的衣服。她在脸盆里放了一些水,洗了把脸,把头发和脸都擦干净了,对着镜子照了照,咬了咬嘴唇,感觉清爽和舒服多了。
她走出洗手间来到客厅,看见沙发前的茶几上已经放着两杯酸梅汁和一盘西瓜,听见厨房里传来一阵声响。她走到厨房边上,探头向里面望去,看见明宵已经换好了一件白背心和一条蓝色运动短裤,正在煤气炉上烧一锅水。你忙活什么呢?她站在门口问明宵说。煮方便面,明宵扭头笑笑说。这种方便面的汤很好喝,不信一会儿你尝尝。你先客厅坐着去吧,方便面一会儿就好。
她回到客厅,就着盘子吃了一块西瓜,用桌上的一张纸巾擦了擦手,端着酸梅汁走到书架前。她看见明宵的书架上放着《安娜卡列尼娜》,《欧亨利短篇小说集》,《简爱》,《约翰克里斯多夫》,《悲惨世界》,《巴尔扎克全集》,《战争与和平》,《牛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与黑》,《复活》,《静静的顿河》,《三个火枪手》,几乎她能知道名字的外国小说都应有尽有。她觉得很惊讶,这个街道上的孩子王,怎么家里也这么多书。她把酸梅汁放在茶几上,从书架上抽出《安娜卡列尼娜》,站着翻了翻,没翻几页就入迷地读了起来。
方便面好了。明宵端着一碗打了鸡蛋和放入切碎了的西红柿的方便面走进客厅来,把碗放在茶几上说。
虽然听见了明宵的招呼,她依然恋恋不舍地读着《安娜卡列尼娜》,舍不得放下。自从去年中央台播放了英国拍摄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十集连续剧后,她一直想看看这本原著,但是一直没来得及看。
看什么呢,这么入迷?明宵走到她身边问。噢,《安娜》啊,很好的书,我很喜欢。
你怎么这么多书啊,她羡慕地问。你都看过吗?
差不多吧,明宵说。文革抄家的时候,别人的书都往外扔书,我妈特别喜欢外国文艺,就往回捡书。这书架上的大部分书都是我妈那时捡的,我在初中以前就读完了。
你妈胆子够大的啊,她说。
我们家出身好,根正苗红,不怕,明宵说。这些书,你要想看就随便拿,不过每次只能拿两本,看完再来换。
太好了,她欣喜地说。暑假正想好好读几本书呢。
赶紧吃面去吧,明宵催促她说。不然该坨了,你一会儿不是还想补习数学呢吗?
她把书放回书架,走回沙发边坐下。明宵回厨房给自己也端了一碗方便面和拿了两双筷子来,把一双筷子递给了她。路上淋了雨,喝着热乎的方便面,她觉得很舒服。她吃得很慢,明宵吃得快。明宵吃出了一身汗,站到客厅的电扇前,让摇头电扇吹着自己的身体。吃完方便面后,明宵把碗筷收拾回厨房,她从书包里把有些潮了的数学书摊开在茶几上,随后把一个铅笔盒掏出来也放在茶几上,用一把铅笔刀削铅笔。她一边削铅笔,眼睛一边心不在焉地看着厨房,不小心把左手的拇指削了一下。唉呦,她小声叫了一声,放下铅笔刀,用右手捏住了手指。怎么了?明宵在厨房听见了,跑出来看。怎么把手给削着了?明宵看着她的冒血的拇指心疼地说,转身去厨房的壁橱里翻着,找出了一卷纱布和云南白药来。明宵用云南白药给她的拇指伤处点上,用纱布小心地缠好。还疼吗?明宵问她说。不疼了,她说。我们学数学吧。
明宵坐在她身边,翻了翻她的数学书,开始给她讲数学。他讲完原理之后,很耐心地给她讲着书上的例题,然后帮她做习题。她觉得自己在数学上有些愚笨和不开窍,上课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也不好意思问老师。但是在明宵的讲解下,她突然觉得自己开窍了许多。一些看上去很难的问题,在明宵的耐心讲解下,也变得容易了。挨着明宵坐着,她也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她能闻见明宵身上和头发上散发出来的雨水的气味。她觉得明宵这么优秀,帅气,聪明,有理想有才华,任何一个女孩都会喜欢上他的,但是他却坐在她身边,耐心地帮着她做数学,还挺身而出,带着她去中央芭蕾舞团,帮她给母亲出气,对她还好。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她现在感觉到了那种万有引力一样的强烈的吸引力,开始明白母亲为什么会不怕危险,跟着自己的爱人到中国来。她在做习题的时候,明宵的腿有时会碰到她的腿,胳膊也有时会碰到她的裸露的手臂,每一次不经意的触碰都给她带来一种触电似的刺激和兴奋。她喜欢明宵的长跑运动员一样匀称的大腿和小腿。看见明宵英俊的脸庞,听见他的带有磁性的自信的声音,她的脸有时会突然一下变红,身体会颤抖一下,手心里会出一些汗。她尽量遮掩着自己,不想让明宵知道她对他的喜欢。
埋头做了三个小时的数学题之后,她觉得累了,不想继续做数学了。
放点儿音乐吧,她揉着手腕对明宵说。不想做了,手都做残了。
明宵走到客厅一角的音响前,把一盘《天鹅湖》放在里面,随后走回了她身边,继续坐在沙发上。双簧管吹出的柔和曲调,自客厅的角落向着四周弥漫,把他们引到了充满着荆棘与迷雾的天鹅湖畔。竖琴的琶音像是透彻的清泉自山间流下,弦乐器发出的震音和弦给屋子带来了一阵让人不安的忧郁。她沉浸在哀婉动人的旋律里,心里感到一阵悸动。你会跳《天鹅湖》吗?明宵突然问她说。会,她点头说。跳一段吧,你平时不是也自己练习吗?明宵说。可是我没有舞鞋,也没有合适的裙子,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推脱说。早上在小剧场不也没舞鞋,也跳的很好看吗?你就这样跳就挺好的,我很喜欢看,明宵说。好吧,她站起身来说。跳不好不许笑话我啊。
她带着一丝羞怯走到客厅中央,看了一眼明宵,两手下垂,左脚在前,右脚在后,踮起脚尖,摆了一个预备姿势。明宵目不斜视地看着她,脸上带着微笑,给她鼓着掌。她微笑了一下,挺起胸膛,两只手臂举起,越过头顶,弯成一个弧形,让两只手并拢的指尖在头顶上遥遥相对。随着缠绵悱恻的音乐,她像是变成了森林里的一只美丽的带着忧伤和彷徨的天鹅,在浓雾弥漫的湖边游荡着。她时而旋转,时而跃起,时而俯下身,像是一只纯洁美丽的白天鹅,带着无尽的哀伤和惆怅,在湖边游荡。一曲完毕,她停下脚步,看着坐在沙发上的明宵,两只手拽着想象中的裙角,做了一个优雅的谢幕的姿势。
跳得太好了,明宵使劲儿鼓掌说。真的跳得太好了,没想到你跳得这么好,比我在天桥剧场看到的芭蕾舞都好多了。你应该去芭蕾舞团,绝对应该去芭蕾舞团。
我不会去的,她摇头说。只要他在那里,我就不回去的。
真可惜,多少人打破脑袋都想进的中央芭蕾舞团,你居然机会到了手了都不去,明宵说。不过别担心,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电影导演的,到时你到我的电影里来跳芭蕾好了。
那你的第一部片子一定要让我来拍啊,她开玩笑说。
肯定的,明宵很认真地说。一言为定。
你真的要去美国上学吗?她问明宵说。
签证申请七月初都已经交上去了,明宵说。八月份应该就能拿到签证,订好机票,九月份开学就能去旧金山念书了。
这么快啊,她有些吃惊地说。还以为要有好长时间呢。
她突然觉得心情有些沮丧。她以为明宵至少要明年才能去美国,没想到他过完暑假就会走。难道她的命就是这样,刚喜欢一个人,不久就会分开?如果她能跟他一起去美国就好了,但是她知道,她去不了。她不敢想象明宵去了美国会怎样。她去不了美国,跟明宵隔着这么远,他恐怕渐渐就会把自己给忘记了。
她有些黯然地从客厅中间走回到沙发边坐下,端起酸梅汤来喝了一大口。她咽得急了一些,被呛了一口,咳嗽了起来。明宵递给了她一张纸巾,她擦了擦嘴,把纸巾放下,看了一眼窗外依旧阴郁的天空和墙上不断走着的表,觉得好像就要跟明宵分开了一样,心里很难受。
怎么了?明宵问她说。看你有些不开心。
没怎么,她勉强笑了一下说。没怎么。都快五点了,你爸妈也快回家了吧,我得走了,让他们看见怪不好的。我能把那本《安娜卡列尼娜》借走看看吗?
没问题,明宵爽快地答应说。明天我们还能见面吗?要不明天上午你到我家来,我继续给你补数学?
真不好意思,到你这里又是吃又是喝又是拿的,她一边把数学书和作业本收拾进书包一边说。
咱俩谁跟谁啊,你跟我还客气?明宵说。那就说好了,明天继续来我家好吧?我爸妈七点半就出门上班去了,之后什么时候来都行,我在家里等着你。手还疼吗?
不疼了。她从沙发上站起来,提起书包说。跟你学习,都忘了疼了,比上补习班强多了。
让我看看,明宵说。
她把左手伸出来给明宵看。明宵抓住她的手,把她的手指拉近眼前仔细看着。她觉得自己的手在明宵的手里,显得很柔软和软绵绵的。明宵用手指触摸着她的缠着纱布的大拇指。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把手抽出来。其实还有一点疼,她说。
她走到书架边,取下了《安娜卡列尼娜》那本书。书有上下两册,她把书塞进书包里。她走进洗手间,看了一眼晾在架子上的裙子。裙子还有些潮湿,但是可以穿了。她关上门,把明宵给她的白衬衣和短裤脱了下来,换上了自己的裙子。她打开洗手间的门,把衬衣和短裤还给明宵。她有些不好意思,觉得应该洗洗再还给明宵,但是她不能把明宵的衣服带回家。她有些恋恋不舍地跟明宵在门口道别,答应着第二天早上再来,然后背着鼓鼓囊囊的书包,转身飞快地跑下楼梯,回家去了。
靳凡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准备回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夕阳在天际留下了十几米宽的橙色的痕迹,消失在一片树梢之后。他把人事处的办公室门锁上,沿着一楼静悄悄的走廊来到了父亲的团长办公室。他习惯每天走之前来看看父亲走没走,有什么嘱咐没有。楼道有些昏暗,走到门口时,他看见办公室的灯已经亮了。靳凡轻轻推开门,走进了团长办公室。他看见花白了头发的父亲正坐在宽大的硬木办公桌后,在看着桌上的一份请示报告。办公桌摆着一部白色的电话,案头整齐地叠放着几落文件。爸,这么晚了您还在忙?靳凡走进办公桌问父亲说。今天的面试怎么样?父亲从办公桌后抬起头问他。
不太好。靳凡自己给自己拉了一把椅子在父亲对面坐下说。这两天都没有看见特别出色的,明天还有一天面试,再看看吧,不行只能矬子里拔将军了。
你期望太高了,父亲说。这都是全国的尖子,你还不满意啊?
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还是缺乏一些灵性和悟性,靳凡说。
我今天从外面开会回来,在门口遇见了一个穿着红裙的女孩,父亲放下手里的报告说。看到那条裙子的时候,我就想这孩子怎么也有一条这样的裙子,看着特别眼熟。
是小曦,她今天来了,靳凡说。
噢,是来面试吗?她的木匠爸爸不是不想让她见到你吗?
不是来面试,靳凡说。我也奇怪,可能是她自己听说了什么,知道了我在这里,就到了芭蕾舞团来。我在四楼小剧场看见一个女孩穿着一条红裙在跳舞,一下就认出了她。她跳得非常好,比我今天看见的所有的考生都跳得好。她太有芭蕾天分了,简直跟她母亲跳得一模一样。爸,我想让她直接来参加复试,您看行吗?
这孩子一看就灵气,长得也像她妈。你就让她直接来复试好了,我支持你,父亲微笑了一下说。
爸,有您的支持我就有底气了,靳凡说。不过小曦好像不太想来,可能因为她妈的去世,对我有一些怨气或者什么。
我们是对不起她妈,没能把她照顾好。父亲叹息说。她从苏联跟着你来到这里,我们都没想到后来会有文革,会发生那些事情。可是当时有什么办法呢?那时我在牛棚劳动改造,你在监狱,我们都见不到听不到消息。好在她后面嫁了一个好人,生下了小曦。但是谁也没想到几年之后她自己走了。她要是能坚持几年,也就能熬过去了。小曦是咱们家的孩子,母亲也去世了,咱们多照顾她,也是应该的。你想办法让她来吧,有这么好的条件,不来这里太可惜了。再说,她来了这里,你不就能总能见到她啦,也不用偷偷去看她了。我也会很高兴的。
我也是这么想,靳凡说。监狱的这十年把我的身体都毁了,年龄大了也生不了孩子了。咱家就只有小曦这么一个孩子,她喜欢芭蕾,咱们有这么好的条件,不把她好好培养多亏啊。我会想办法劝她来的。
文学城链接:
给我一条波希米亚红裙(十九)
文革不是都过去了吗,为什么明宵还总是“向毛主席保证”呢?明宵比今昔大多少?
遇到小曦,发生了冲突,脸上也受伤了,可是靳凡面对妻子的询问却只字未提,轻描淡写的掩盖了过去,可以由此推断,靳凡对妻子是顾忌的,这大概也是他不能直接将小曦接回家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