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册
- 2009-01-16
- 消息
- 4,643
- 荣誉分数
- 1,481
- 声望点数
- 323
三见钟情,这话说得太经典了!徐很正直能干,素质也不错。小溪美丽善良,虽然小溪爱徐不及徐爱小溪,但是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人挺搭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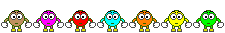
乡里乡亲的借口来看徐泽宁,其实是来看小溪的。。拥抱还是很有生活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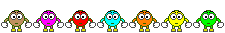
乡里乡亲的借口来看徐泽宁,其实是来看小溪的。。拥抱还是很有生活的吗!


六十二
越野吉普车在蜿蜒起伏的公路上飞快地行驶,车后卷起一阵阵的黄沙。繁华的大城市的建筑,人群,车辆在后视镜里逐渐远去,贫瘠的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逐渐呈现在眼前。她坐在吉普车上,眼睛看着窗外的苍凉的田野和高低起伏的山丘,身子随着车轮的滚动颠簸着,心里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
她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种忧伤的感觉,千里迢迢的来看徐泽宁,她本应该高兴才是。难道一个未婚妻来看望自己的未婚夫,不应该高兴吗?她扭头看了一眼徐泽宁,看见他的头靠在后座背上,脸色有些苍白,厚厚的嘴唇闭着,显然手术后的伤口在颠簸之下有些疼。他对她微笑了一下,伸手抓过了她的手,把她的手放在他的大腿上。吉普车在路上剧烈地颠簸了一下,她看见他皱了一下眉,咬了一下嘴唇。
伤口疼吗?她看着他问。是不是让司机开慢点儿?
没事儿,徐泽宁攥紧她的手说。这边都是这样的路,不过有你在我身边,我觉得好多了。
她把头靠在徐泽宁的肩上。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男人有一副既宽阔又坚强的肩膀,她喜欢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带来的那种安全感。虽然他追了她几年,但是除了他的家世和他的工作以外,她对他还不太了解。他从来没有跟她聊起过他的生活。每次打电话来,他谈起自己来都是工作里的一些事儿,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问她过得怎么样,演出怎么样,心情好不好。她很少问过他什么问题,从不知道生活里的他是个什么样子。她觉得自己到西安来看徐泽宁的决定是很对的,她不仅是在尽一个未婚妻的职责,更是要增加对徐泽宁了解,知道自己要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路上徐泽宁给她介绍着途径的城镇和景点,聊着陕北的民风习俗和历史。她点头听着,窗外的一切对她都是新鲜而陌生的,黄土高原在她的眼里就像是撒哈拉大沙漠,而她就像是三毛,走进了荒寂而又神秘的黄色的王国。有一刻她觉得自己像是舞剧里的睡美人,被一个沙漠王子吻了一下醒来,跟王子一起骑在骆驼背上,走进了天边赤红的落日。
延川,清涧,绥德,米脂,一个个陌生的地名和路标在吉普车外出现又消失。吉普车在狭窄的山路上按着喇叭,不断超过装满货物的绿色的解放牌大卡车,载满了人的灰色的长途客车,带着挎斗的手扶拖拉机车和慢腾腾走路的马车。赶车人挥着鞭子催促着马快走,一只老牛从路边的茅屋里露出两只睁得滚圆的眼睛来,空气中带着牛粪和马粪的味道,贫瘠的山野上覆盖着薄薄的雪。远处出现了一座廖无人烟的荒城,残缺的城墙耸立在杂草横生的沙土地上,高大的夯土台基看着很悲壮。
这是匈奴留下来的城堡,徐泽宁对她介绍说。有一千六百年的历史了,据说当初修建城堡时,墙缝之间灌得是米汁,非常坚固。匈奴监工验工的时候,会把刀片往墙缝里插,要是能插进去,就会把干活的人杀掉。
天上飘来了一阵乌云,乌云携带着狂风,狂风卷起了路上的沙子,豆大的雨点突然毫无预兆地从天而降,噼噼啪啪地打在吉普车的窗玻璃上。对面疾驰而过的一辆大卡车碾过一处水洼,把带着泥沙的污水溅起在吉普车的前车玻璃上,一刹那吉普车的前车窗被笼罩在泥浆中,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了。雨刷咯吱咯吱地响着,把泥浆推到窗户的两边。司机无可奈何地咒骂了一声,继续在雨中飞快地开着车。她有些担心吉普车翻了,心里害怕,身子靠得徐泽宁紧了些,手紧张地抓着徐泽宁的手。
这边都是这样开车,很野,徐泽宁笑笑说。我一开始看见这样也是心惊胆战的,不过后来就慢慢习惯了。记得插队时有一次坐着手扶拖拉机在山路上开,被对面来的一辆大卡车一挤,翻到了公路下面的沟里面,腰部和背部受了伤。幸亏下面的沟不深,不然可能就把命搭在里面了。我当时特别害怕,因为老四跟我一起坐在手扶拖拉机上。老四的父母在文革时都跟傅雷夫妻一样上吊自杀了,我把老四带到陕北来,就是要照看着老四,不让老四出什么意外。我从地上爬起来,大声喊着老四。老四从翻倒的拖拉机挎斗里钻出来,跑到我身边,身上居然一点都没受伤。这小子命大,一车的人都受了伤,只有他毫发无损。
你以后别坐吉普车了,要坐就坐大卡车吧,她有些心疼地说。卡车好歹还安全一些,你每次去西安都是坐吉普车从这条路上走啊?看着真让人害怕和担心。
风尘仆仆七个小时之后,吉普车驶进了榆林城,开进了地委大院。地委大院门口是一个大铁门,门前有两个士兵站岗。看见徐泽宁的吉普车过来,两个士兵赶紧把大门推开,然后站得笔直,向着吉普车敬了一个礼。徐泽宁向站岗士兵摆摆手,吉普车从士兵身边穿过,驶向了最后面的一座灰色的长方形桶子楼房。
司机把吉普车在楼房门口停下。徐泽宁打开车门,有些吃力地扶着门边的把手把腿迈了下来。她从吉普车另一侧跳了下来,绕过吉普车来到徐泽宁身边,伸手搀住徐泽宁的胳膊。徐泽宁感激地看了她一眼。楼房前面有几个人走过来,跟徐泽宁热情地打招呼说:
徐书记回来啦?听说您去西安做手术去了,手术做得怎么样?
很好,徐泽宁面露笑容说。非常成功。医生说可以出院了,我就回来了。
把您的未婚妻带回来了?其中一个人打量着她说。哎呦,这姑娘张得可真俊啊,啧啧,你看这皮肤,水灵灵的,大城市里的姑娘才会保养得这么好。听说还是芭蕾舞大明星呐,徐书记,您真有福气。
她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站在徐泽宁身边,红着脸不知道说什么好。
司机把她和徐泽宁的行李从车上提了下来,几个人跟徐泽宁说笑着,一起帮着把行李提上了楼。徐泽宁的住处在三楼靠最西端的房间。一走上三楼的楼道,几个房间的门都打开了,不断有人走出来跟徐泽宁打招呼和好奇地看着她。司机和几个人帮着把行李提进了徐泽宁的房间,站在门口跟徐泽宁说话。
她好奇地看着徐泽宁的房间,看见门口有两个衣裳架,里面有两个带门的独立房间,一个客厅,一个洗手间,还有一个小厨房。客厅很大,分成两个区域,一个区域摆放着一对简朴的灰色沙发,一个大玻璃茶几,几排书架,一台电视,几个文件柜一样的柜子。另一个区域摆放着一个长方形的木头餐桌,四周放着几个木椅子。四周的墙上挂着几轴字画,一幅世界地图和一幅中国地图,一个挂历和一个大钟。客厅里有两部电话机,一部放在茶几上,一部放在墙角的一个立式小圆架子上。客厅的窗户很大,上面的素色窗帘卷起,露出外面的一个阳台。客厅的地面是水泥地,抹得很平,擦得很干净,亮得像是个镜子。
门口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徐泽宁站在门口不断地跟人寒暄着。她不认识那些人,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站在徐泽宁身边,扶着徐泽宁的胳膊,听着他们说话。站了有半个小时之后,她拽了一下徐泽宁的袖子,跟徐泽宁说:
到沙发上坐一会儿吧,你手术刚完,身体不好,又在车上颠了这么长时间,别累着。
门口的人看了她一眼,赶紧说:
徐书记,不打搅你们了,赶紧好好休息吧,明天办公室我们再谈。
门口的人都走了。她把门关了,扶着徐泽宁坐到沙发上,从旁边的桌子上拿过暖水瓶来,给徐泽宁倒了一杯水,从行李箱里翻出医院给的药来,让徐泽宁吃了药。
怎么这么多人来看你啊,走了一拨又来一拨的?她问徐泽宁说。
他们哪里是来看我,都是来看你,徐泽宁笑着说。经常有人想给我介绍个当地的女朋友,我老跟他们说,我订婚了,未婚妻在北京,既漂亮,人又好。他们是好奇,来看看你这个大芭蕾舞明星是个什么样子。
我也没有打扮,一路上风尘仆仆的,肯定让他们失望了,她脸红着说。人家一定会觉得你在吹牛。
你就这样的朴素的样子最好,徐泽宁说。这地方民风淳朴,你要是打扮了,他们倒会觉得不好看了。
她跟徐泽宁刚在沙发上坐了没几分钟,就听见又有人在敲门。
看,又来人看你了,我敢打赌,现在全大院的人都知道你来了,徐泽宁说着要站起身去开门。
你坐着别动,我去开门,她按住徐泽宁的胳膊说。医生说了让你到家好好休息。
她走到门口,打开门,看见齐静和志宏站在门外,志宏手里端着一个盖着盖子的热气腾腾的铝锅。
齐静!志宏!她惊喜地叫道。是你们啊,真高兴看见你们,快请进。
好妹妹,我们就住在楼下,刚听说你跟着泽宁回来了,齐静走进屋门来兴奋地抱了她一下说。你来了真好,这些日子没见,想死你了。我想你们一路上肯定没来得及吃饭,赶紧煮了一锅饺子,叫着志宏送上来。赶紧趁热吃吧。
还是你们想得周到,徐泽宁站起来说。中午在半路上随便吃了一口饭,肚子还真饿了。
志宏把铝锅放在长方形的餐桌上,齐静走到厨房里拿来几个碗和一瓶醋,倒了两个醋碗,把筷子摆放在醋碗上。
我下午刚包的,自己擀的皮,猪肉大葱白菜馅儿,齐静说。我们都吃过了,你们赶紧尝尝吧,比食堂的机器饺子好吃。
徐泽宁一边吃饺子一边跟志宏聊起了工作。齐静激动地跟她聊着天儿,好像好久都没见了一样。她见了齐静觉得特别高兴,跟见了自己的亲人一样。她忘了齐静请了假来榆林看志宏,本来以为自己到了榆林人生地不熟,除了徐泽宁谁也不认识。现在有了齐静和志宏,她感觉好多了。
老四去西安看了我,徐泽宁跟志宏说。老四联系好了一家美国的农场,过一段时间我们组团去美国,看看美国的农场是怎么经营的。我跟老四说好了,由他们公司拿出一部分钱来,在榆林开办成衣加工厂和玩具工厂,把产品销到国外去。
老四愿意吗?志宏问徐泽宁说。
老四没问题,但是他们公司的一些董事有些不愿意,徐泽宁说。老四说了,我在哪里,老四就把钱投到哪里。他们这几年利用国家的双轨制,赚了不少钱,吐出一部分来帮助陕北这样的落后地区,也是应该。我看邓老爷子的这条摸着石头过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线,最终会造成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悬殊,看看老四他们轻轻松松地赚了多少钱就知道了。他们赚钱可以,但是也要拿出一部分钱来回馈社会,帮助穷人。
有钱的人都抠门儿,这是资本的本性,志宏说,就怕他们赚了钱,就不想吐出来了。
不吐也得吐,不管他们是内资还是外资,不管他们是包玉刚还是李嘉诚,只要是在中国赚到钱,就得拿出一部分来,不然以后别想在中国做买卖,徐泽宁说。我们还是要搞社会主义,不能把中国搞成资本主义,不能让富人们为所欲为,更不能让钱来指挥政府。
你不是想搞均贫富吧,志宏说,那样的路行不通。
不是均贫富,是让资本家赚他们应得的利润,而不是暴利,徐泽宁说。任何他们赚的超出他们应得的利润,都应该还给社会,还给老百姓。
好,我赞同,志宏说。一个过于贫富不均,两级分化,贪污腐败的社会,都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颠覆社会主义体制。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共同富裕,贫富差距不要太大,为政清廉的社会。历史给了中国一个崛起的机会,也给了我们这样的经历过文革,上过山下过乡,知道老百姓疾苦的人一个重任,建设一个强大的,公平的,合理的,共同富裕的社会----
志宏,以后你跟泽宁再高谈阔论好不好?齐静用胳膊肘杵了一下志宏的胳膊说。今天小曦刚来,你别在这里得得个没完,你的那些乌托邦的理想社会以后跟泽宁单独说去,现在先让人家好好休息一下。
对不起,志宏对她抱歉地笑了一下说。小曦,我们就住在楼下205房间,今天晚了,你好好休息,明天让齐静带你去转转榆林城,尝尝榆林的好吃的。
见到你们特别高兴,她兴奋地说。没想到在这里还能跟你们做邻居。
齐静和志宏走了之后,徐泽宁说还有些紧急事情需要处理一下,让她自己先洗洗,休息一下。徐泽宁去了书房之后,她从自己的旅行箱里翻出了毛巾,牙刷牙膏,一卷卫生巾和卫生纸,放在一个朔料袋子里,提着去了洗手间。徐泽宁的洗手间很简陋,只有一个马桶,一个带镜子的洗手池,一个挂着几条毛巾的架子,一个贴在墙上的壁橱和一个垃圾桶。她把牙膏挤在牙刷上,对着镜子刷了牙,洗了把脸,用自己的毛巾把脸擦干净,随手把毛巾放在架子上,跟徐泽宁的毛巾放在一起。
头一次跟一个男人住在一间屋子里,晚上可能还要睡在一张床上,她心里觉得有些忐忑不安和害怕。她有一种迷乱的心情,不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她一直觉得爱是崇高的精神的,做爱是肉体的耻辱的,所以即使跟明宵在一起,她也不愿意在结婚之前放弃自己的最后防线。好在这几天来了老朋友,可以光明正大的拒绝徐泽宁对她的欲望,她想。
她走出洗手间,来到徐泽宁的书房,看见他坐在一张办公桌前,正低头用一杆笔在一卷公文上批着什么。她没有打搅他,而是走到墙边的书架边,想看看徐泽宁平时看什么书。她看见书架上摆着一排灰皮书和蓝皮书,就好奇地拿下一本来翻看。
那是内部书店买的书,徐泽宁抬头对她说。都是外面买不到的,只有省军级的高干才能去的书店,是用我爸的图书证买的。
她看着手里的书,封面上写着《在路上》,署名是杰克·凯鲁亚克。她翻开一页,看见上面写着:
“我多年来从没有这么疲倦过。我去纽约还有三百六十五英里的路需要沿途搭车,口袋里只有一枚一毛硬币。我步行了五英里才走出匹兹堡,搭了两次车,一次是装苹果的卡车,另一次是铰接式卡车,在十月小阳春的雨夜到了哈里斯堡。我不作停留,继续往前。我要回家。。。我们在漆黑的夜里穿过了新墨西哥州;灰蒙蒙的黎明中到了得克萨斯州的达尔哈特;阴冷的星期日下午,我们经过一个又一个的俄克拉何马平原小镇;晚上到了堪萨斯。公共汽车隆隆地行驶。我十月份回家。人人都在十月份回家。”
我们中午到达圣路易斯。我在密西西比河畔散步,看北面蒙大拿的原木顺着河水漂流下来——我们美洲梦里的奥德赛大原木。陷在淤泥里的、耗子出没的旧轮船久经风吹雨打,船上的涡卷装饰已经破败不堪。下午的密云笼罩着密西西比河谷。那晚,公共汽车隆隆驶过印第安纳的玉米地;月光下堆在一起的玉米苞叶显得形状怪异;几乎有万圣节的意思。
。。。
我醒来时太阳发红;那是我一生中难得有的最奇特的时刻: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我远离家乡,旅途劳顿,疲惫不堪,机身在一个从未见过的旅馆房间,听到外面蒸汽的嘶嘶声,旅馆就木器的噶之声,楼上的脚步声以及各种各样凄凉的声音,看到的是开裂的天花板,在最初奇特的十五秒钟里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是谁。我并不惊恐;只觉得自己自己仿佛是另一个人,一个陌生的人,我一生困顿,过着幽灵般的生活。我正处于横穿美国的中间地点,在我青年时期的东部和我未来时期的西部的分界线,也许就是那个奇特的火红下午为什么发生的原因。”
这不是小说吗?她好奇地举着手里的书问徐泽宁说。这种书怎么会只能在内部书店卖?
这是文革时出版的一本书,徐泽宁站起来走到她身边说。写得是美国垮掉的一代的,那时这种书属于毒草级别的,但是我们知青都很爱看。如果我不从政的话,我愿意像里面的那个人,没有多少钱,但是一直在路上旅行,自由自在的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跟不同的人交往 --- 过一种那样的生活也是挺好的 --- 我带你去看看阳台吧?
好,她把书塞回到书架上说。
月亮又大又圆地悬挂在蓝色的天幕上,旁边的一片云彩像是马尾巴一样翘起。她披着自己的棉袄,跟徐泽宁站在阳台上,看着密集的星星散布在天空。脚下的大院里静悄悄的,四周的房屋也黑了灯,像是人们都已经入睡了,没有脚步声也没有风声。阳台上很黑,冬夜的清凉的空气顺着棉袄的脖子处透了进来,让她不禁打了个寒颤。徐泽宁从后面抱住她的腰,让她感觉暖和了一些。
在北京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星星,她小声说。
榆林城太小,灯光少,夜空看得也清晰,徐泽宁的嘴贴在她耳边说道。我喜欢晚上站在阳台上,想一想工作里繁琐的事情,想一想你。
真的吗?她依偎在徐泽宁的怀里说。不是骗我吧?我一直没明白,你怎么会喜欢上我呢?
你相信这世界上有一见钟情吗?徐泽宁问她说。
相信,她说。可是我觉得你不是那样的人,一见钟情的人往往是比较幼稚的人,你很成熟。
成熟的人就不能一见钟情了吗?徐泽宁反问说。比如我对你就是这样。不过你是对的,严格来说不是对你一见钟情,是三见钟情。
怎么个三见?她扭过头问徐泽宁说。
第一次是看你演《天鹅之死》,第二次是见你在舞蹈学院带着学生们跳舞,第三次是看见你穿着那件波希米亚红裙表演《卡门》,徐泽宁说。反正那次看完你表演的卡门之后,我就认定了你就是我喜欢的人。
可是我对你不是特别了解,她说。除了知道你的家世之外,对你几乎什么也不知道。舞蹈学院的女孩子们说,出生在你那样的家庭里的人,一出生就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不用担心,对吗?
人们总羡慕我,觉得我一出生就什么都有了,其实,我受的苦和累比别人一点也不少,徐泽宁说。文革时,我爸爸靠边站了一阵子才出来,后来又跟着邓老爷子,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被打倒。那时跟我一样的出身的人,经常头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醒来就变成了狗崽子,成了黑五类的孩子。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参加了老红卫兵组织联动,干过不少坏事,徐泽宁停了一下说。那时跟着一批高干子弟组成的西城区纠察队,抄家,打砸抢,用皮带抽人打人。但是后来厄运降临到我们头上,一夜之间,联动成了反革命组织,我们也被关进了监狱,后来多亏了总理出面把我们救了出来。
你不知道,那时我为了表现自己,在抄家的时候总是冲在前面,直到抄到萍萍家,徐泽宁接着说。他们知道我跟萍萍好,故意让我去剪萍萍的头发,我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和大义灭亲,就按照他们说的做了,结果萍萍自杀了。
我听你说过,她说。你一定很自责,自那之后就醒悟了 ---
没有,徐泽宁摇头说。萍萍自杀之后,我还没有醒悟,直到联动被打成反革命,进了监狱,我才真正醒悟过来。在监狱里我们都在反思,那时我才明白,我们就是打着革命的名义在互相斗自己。从监狱出来之后,我们一些人就再也不参加红卫兵活动了。那时我们之中的很多之人颓废了,成了顽主,老四也变成了顽主之一,打架斗殴,有一次碴架时被一个混混扎了一刀,几乎把胃扎穿,把命丢掉 ---
老四这么厉害啊,她惊讶地说。看着文质彬彬很儒雅的样子,真难想象。
那是现在,以前不一样,徐泽宁说。我把老四拉了回来,把老四关在家里,不许老四出门,后来把老四带来陕北,一直看着他,不让他惹是生非。在陕北我一直在读书,读了能够找到的所有的书,跟志宏也成了朋友。
那时我真的相信毛主席说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同时也是为了表现自己,插队时每天起得最早,干活最拼命,回来得最晚,徐泽宁继续说。我后来成了大队书记,不是因为我爸,而是因为我自己的表现,没有一个人像我一样不要命地干活。七七年高考,那时没有后门,我是靠自己的本事考进清华读书的。
我觉得你很聪明的,她说。不过你出生在那样的家庭,以为你从小会娇生惯养,吃不了苦呢。
我是小时娇生惯养,但是这并不是我的优势,而是我的劣势,徐泽宁说。因为陕北农村那样的贫穷,对我这样娇生惯养的人来说,那个环境就更艰苦,更恶劣。但是我比别人都做得好。我爸说,我继承了他的基因,什么苦都不怕。我们这拨高干子弟里,将来注定会有祸国殃民的人,注定会有大奸大贪,但是也一定会有不放弃理想,为了国家和人民承担起富国强民的使命的人。我不会成为第一种人,我只能成为后一种人。人们说,政治斗争是最残酷无情的,看看建国后历届的政治运动就知道了,从政这条路不是一条铺满鲜花的路,它其实是一条荆棘丛生,布满陷阱和危险的路。
我为什么要洁身自好,保持清廉?徐泽宁自问自答说。因为像我这样的人,将来注定会挡住一些人的升官发财之路,成为一些人的眼中钉,成为一些人的威胁。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想打倒我,如果他们不能光明正大地打倒我,就会想法儿找出我的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从这两个方面搞臭我,打击我。坦率的说,小曦,你跟着我,将来不仅不会荣华富贵,而且还要担惊受怕,因为不定哪一天,我的对手们会把我抓起来,用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关进监狱。那时你会失去一切,还会跟我一样蒙受耻辱,因为他们也会把你搞臭,甚至会给你身上栽赃陷害。所以你跟我在一起,一定要特别小心,不可以接受任何人的钱财,也不可以接受任何形式的好处。你廉身自洁,既是保护你自己,也是保护我,更是保护我们将来可能有的孩子。
听着徐泽宁的一番肺腑之言,她突然觉得很感动,几乎要哭了。她转过身,在月光下仔细地端详着徐泽宁。月光倾斜地照在徐泽宁的脸的侧面上,他的浓厚眉毛下的眼瞳闪闪发光,嘴角紧闭着,脸庞被一半阴影笼罩着,显得刚毅而威严。她凝视着徐泽宁的面孔,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不屈不挠的斗志,一种忧国忧民的理想,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她仰着头看着徐泽宁,觉得徐泽宁是一个她心目里的真正的英雄,一个让她仰慕的大英雄。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你,她小声说。你跟别的高干子弟不一样,一点儿都不一样。你身上有一股劲儿,一股让人钦佩的理想和执着的劲儿。对于我来说,我不需要什么,有份儿工资,有个房子,有点儿家具,有个简单的生活,将来有个可爱的孩子,我就很满足了。既然跟了你,我就会跟你同舟共济,甘苦与共,也不会给你惹祸的。
我爱你,徐泽宁说。爱你好久了,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你是否也爱我。你会爱上我吗?
我会的,她把头埋到他的胸膛里说。过去我已经喜欢上你了,现在觉得更喜欢你了。
文学城链接:
给我一条波希米亚红裙(六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