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使用一款已经过时的浏览器!部分功能不能正常使用。
请尝试升级或使用 其他浏览器。
请尝试升级或使用 其他浏览器。
叔丁江湖之天马行空 -- 诗,远方,私奔以及月亮
- 主题发起人 叔丁
- 开始时间
- 注册
- 2014-04-15
- 消息
- 6,048
- 荣誉分数
- 11,373
- 声望点数
- 1,323
雨中雪, 文理科, 写得很有趣!赞!雨中雪山,我见雪山多朦胧, 料雪山见我应如是
--雨中滑雪记趣
文/叔丁
没有雪的圣诞一样是圣诞,没有雪的滑雪可就不知该如何命名。好不容易整理好心境时间计划周末滑雪,谁知预报下雨。于是每天刷屏看预报,寄希望于天气预报从来离谱的一贯声誉。可惜刷屏再多,也刷不掉那几滴小雨点儿,天气预报这次好像一定要重建信誉,永远是5毫米的雨。
To ski,or not to ski?人们每当犹豫难决之时总要把哈姆雷特请出来走一下台步,老王子也是醉了,却也只是走台步,重复他几百年的古老徘徊。
理工男滑雪者推一推黑框眼镜,按捺住内心跃跃欲试的狂野:雨中,负离子活跃,空气清新,可滑雪。
修行滑雪者合眼沉思,决定以五识之外的心来体会:雨中,天地元气浓郁充沛,可吸取而供养之,可滑雪。
资深大悟滑雪者两手背在身后,踱了几步,却不是王子的台步,因为马上有所感悟: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之下,不同的雪质,滑雪板或滑,或切,或砸,就会有不一样的感悟,雨中,是一种难得的磨练。
雨中,再上雪山,我见雪山多朦胧, 料雪山见我应如是,因为雪山披着白色浓雾,而我,披着蓝色雨披。相看两不厌,唯有都善变。
雾雪一色,迫切感受自己已经与天地融为一体。蓝色,是水的颜色。我是文科生,可以姑且忽略理科生所谓“水是无色”的好心提醒。水汇集而成湖,成海,就是蓝色。即使蓝天也更像是无尽的水汇集而成。云,不过是水的浪花。那么雨中雪中的蓝色雨披,也就是一大滴强调了的水的惊叹号。穿着蓝色雨披的我,与雨,雪,雾,天,地,一色,一体,我在雨中滑雪,我在水的各种状态的组合中跳舞。“知者乐水”,因为水活,水会跳舞。忽然想明白了,我原来是文青滑雪者。
“雪裤不太防水,里面还是湿了。” LG坐在缆车的另一边忽然自言自语。文青形而上的诗意被他身体切身的物理湿意所替代。
有雨衣怎么会湿呢?百思而不得其解。直到跳下缆车之后的那一瞬间,我恍然大悟,原来LG雨披的背面已经空空如野了。
想起雪道上发现的蓝色片片编结成的那个神秘轨迹,原来竟来自LG。据说,曾有一位滑雪高手一路尾随他而来,捡起他雨披的碎片,好像认真完成一项特别训练任务一般,到了近前,还不忘一本正经地询问:“你还要这些碎片吗?” 不知LG的自悟雪技,需要怎么扭动身体才能够把一大片雨披撕成碎片,他可称之为倔强挑战滑雪者。那一条蓝色雨衣碎片铺出的轨迹,不是要伸向理想的远方,也不是要追逐什么信仰,而是一种执拗倔强的挑战,一条不服输不气馁的宣言。
雨滋润着的雪道显得要温柔许多,滑雪板感受到些许欢迎的态度,信心大增,原来不敢涉足的雪道都赶紧到此一游。毕竟体味雨中滑雪曼妙之处的人极少,不必排队等缆车,短短一上午,已经近20趟的来来回回。下午雨停,滑雪却已完美收官。
雨中,再上雪山,理科男深深呼吸一口满载负离子的清新空气,修行者张开怀抱迎纳天地元气,感悟者恣意于滑板与白雪的碰撞摩擦之间,挑战者继续着没有观众的只属于自己的坚持和倔强。而文青,在水的千姿百态的排列组合中,跳舞。
(原载《新华侨报》2016年1月22日第七版专版专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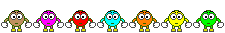
marry866
知名会员
- 注册
- 2015-07-23
- 消息
- 70
- 荣誉分数
- 21
- 声望点数
- 118
叔丁
捻冰箫以弄梅花,凝气剑而笑江湖
- 注册
- 2014-06-22
- 消息
- 158
- 荣誉分数
- 338
- 声望点数
- 173
诗,远方,私奔以及月亮
——读毛姆《月亮和六便士》
文/叔丁
——读毛姆《月亮和六便士》
文/叔丁
“生活不止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一个月来,这句话在朋友圈沸沸扬扬地刷屏,七珍八味的鸡汤鸭血一起装饰出一场与现实不太合拍的文艺宴席。也许高晓松自己也有点儿不好意思,所以搬出母亲大人来说出这句煽情的话。而高晓松那个穿着大裤衩儿,扇着大折扇,八卦着曾经父母近邻的民国女神林徽因的微胖随意形象一下子在眼前风雅诗意起来。尽管诗和远方让我联想起我不太情愿称之为诗人的汪国真,倒确实是标志性的理想的代名词。
十年前的古城西安,郑钧操着慵懒的摇滚歌手中稀有的磁性嗓音,拨弄着吉他,意淫着《私奔》,逃离和遥远城镇。因着理想,自由的意象缘故,本来歌词字面上的男女私情就升华到摇滚歌者人文意义上的彷徨,挣扎和抗争。
近七十年前的一个开了十七年公车而任劳任怨的纽约公车司机威廉·希米洛(william cimillo),在某一天,忽觉厌倦了每天雷同的车站街道,决定不回公车总站,而是把公车开出了纽约城,开去了阳光灿烂的佛罗里达。威廉的离谱行径没有受到法规制裁和舆论的谴责,相反却得到了一个英雄和超级明星才该获取的公众知名度和粉丝群。
一个世纪前的伦敦金融街,一个平凡证券所的乏味经纪人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在夏日假期结束后,离开可爱的妻儿,一个世俗公认的美满家庭,跑到巴黎画画儿。如果我们敬仰的英国小说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在《月亮和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里以这样的基调来杜撰他的主人公,虽然会流于俗套,却也不失读者共鸣。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永远骨感。理想和现实,这对人生永恒经典的矛盾,也可以成为文学的经久不衰的主题。
但是随着毛姆的笔,我们发现却似乎不仅此而已,思特里克兰德简直就是一个魔鬼附身的恶棍。他抛弃妻儿,没有丝毫内疚,更不给他们留下些许供养。他对自己在重病中救他一命的善良的荷兰画家施特略夫的绝好回报是夺走他挚爱的妻子勃朗什。而同样,他回报这个无可救药地爱上他的女人的方式仍然是抛弃,以至于她吞草酸自绝。他自私,粗鲁,毫无礼貌,毫无责任感,令人厌憎,这似乎怎么也不能和追逐理想的高贵灵魂扯上关系。
一位书友悠悠道来:这部小说好比一个桃花源,须缘溪行,忘路远近,入山口,穿窄径,才豁然开朗。那么毛姆究竟想展现给读者怎样一个桃花源呢?在这个五十八章节的小说中,毛姆用了四十几章描述了恶棍思特里克兰德抛妻弃子,恩将仇报的在巴黎令人憎恶鄙视的潦倒罪恶生活。当然也竭尽笔力来炫耀了一下自己对绘画艺术的修养和见识。他也坦诚地承认自己并没有敏锐的艺术鉴赏能力。思特里克兰德画中的简朴笨拙,变形不成比例的实物,夸张原始而不真实的色调,和他自己所习惯欣赏的古典主义的精美,以及早期印象画派的光影陆离的渲染美感,都有强烈反差。不过在画中,他看到了思特里克兰德挣扎着想要表现的一种力量,痛苦,扭曲。究竟怎样的艺术才算伟大的艺术?
与“我”的平常艺术鉴赏力相反,善良而平庸的荷兰画家施特略夫,却有一双识才慧眼,他实在更适合做一个艺术鉴赏家。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诹”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励志口号,如果认为《中华好诗词》上熟背诗词的诗柜词篓可以写出灵性好诗,似乎很值得怀疑。世界上最不靠谱的培训班之一莫过作家诗人培训班了,想象一纸培训证书所担保的一个批量生产千篇一律的诗歌小说的流水线。犀利刻薄的林妹妹也曾经这样讥笑宝哥哥的四平八稳的螃蟹咏:“这样的诗,一时要一百首也有”。果真如此,肯定无人去读。言归正传,艺术家需要天赋,需要敏锐而迥异超常的个性。只是小说中表现出的天才的自私怪诞,善良人的平庸,实在令人唏嘘。
在小说的四十几章之后毛姆终于写到了塔希提岛,思特里克兰德的桃花源。
思特里克兰德不是要逃到远方的某个虚无缥缈的理想中,而是那个塔希提小岛本来就是他的归属,就像阿伯拉罕医生的亚历山大港一样。“有些人诞生在某一个地方可以说未得其所。机缘把他们随便抛掷到一个环境中,而他们却一直思念着一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坐落在何处的家乡。在出生的地方他们好象是过客”,而世界上总有那么个地方,你一见到就似曾相识,而这个地方不是你的远方,而是你的归宿。没有找到这个地方时,他是烦躁的,粗鲁的,冷嘲热讽,自私冷漠。而在这个地方,四十七岁以后他才找到的地方,他是和蔼,平静的,很讨土人喜欢。在没有找到归属之前,他对思特里克兰德夫人冷漠离弃,对施特略夫夫人始乱终弃,而在找到归宿之后,与深爱着自己的年轻单纯专一的少女爱塔温馨相处如平静淡然的一对正常夫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默许她的陪伴。如果这个宿命归属在召唤,他别无选择。他在巴黎回答思特里克兰德夫人的说客“我”的责难时说的是:
“我要画画儿”。“我必须画画儿”。
不是他想画画,是必须。就好像雪雁在初春,在随时存在的暴风雪危险中毅然决然地向北飞行;就像男人在找到拥有自己肋骨的女人后失去理智的疯狂爱情;就像受到神的召唤的以色列先人一样,抛开一切奔向自己的应许之地。他不能自控,他不是他自己,“他好象是一个终生跋涉的朝香者,永远思慕着一块圣地。盘踞在他心头的魔鬼对他毫无怜悯之情。世上有些人渴望寻获真理,他们的要求非常强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是叫他们把生活的基础完全打翻,也在所不惜。”
毛姆对这个浩渺太平洋之中的归属地毫不吝啬笔墨。“与人寰隔绝的一个幽僻的角落,头顶上是蔚蓝的天空,四围一片郁郁苍苍的树木。那里是观赏不尽的色彩,芬芳馥郁的香气,荫翳凉爽的空气。这个人世乐园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 可爱的土著少女妻子爱塔,用椰子油炸五颜六色的鱼,有时还有龙虾,螃蟹。河里面洗澡钓鱼,用椰子的出产换肥皂和日用品,悠闲时就围着一条蓝红两色棉布的帕利欧躺在凉台上。这确实是伊甸园,人不必辛苦劳作忧烦困扰就可以有丰厚收获供给。毛姆似乎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老婆婆和孙女,不知名的少年,美丽少女爱塔,他们的孩子,他所有伊甸园的模特都在那里,他的归宿地在那里,他所痛苦挣扎追随的美都在那里,他把这一切大自然原始美的赞歌,通过他迥异的思维构想再现在小屋的壁画上,虽然伴随他的死而付之一炬,但是他找到了,他满足了,他的生命完全了。这遗失的壁画让人不自觉地联想起高更那幅《我们从哪里来》。但是小说写到这里,思特里克兰德这个人物,是不是以传奇绘画大师高更为原型,在这里已经不重要了,他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标志。
远方,是以本地为坐标来命名的;私奔,也是以正统的媒证婚娶来鄙视的。那么,它们就只能存在于幻想觊觎之中。高晓松在抛出远方和诗的石子儿溅起一波又一波的涟漪之后,还是摇着扇子以《晓松奇谈》谋生。郑钧在意淫之后,依然拥娇妻爱女,时不时在导师席上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或者在舞台上蹦跶几下来为跟他一样早过了不惑之年许久的粉丝们吼几句《赤裸裸》,一起追忆一下青春时的异想天开。纽约的公车司机威廉,玩儿一次招摇过市胆大妄为的把戏,又安心回去每天循规蹈矩地开公车长达十六年之久。
而月亮,是不是就不同呢?即使你低着头找着脚下的早已不再作为货币使用的英国六便士,或者刻印着加拿大大雁的卢尼,看不见头顶的月亮,但是月光似乎永远披在你的肩膀上,如水如银。
如果昆德拉的《庆祝无意义》,是让人明白微不足道的才可以长久,认识到平淡是真,那么毛姆的月亮就让人想入非非,就像月圆之夜总是诡异无常。你感受到了使命的召唤吗?你找到了你的归属吗?或者你的使命感已经在你的大脑中封印,或者你祖先遗留在你身体里的基因已经变异,转向。
最后编辑:
- 注册
- 2014-04-06
- 消息
- 8,610
- 荣誉分数
- 16,519
- 声望点数
- 1,323
叔丁好,拜读好文。诗,远方,私奔以及月亮
——读毛姆《月亮和六便士》
文/叔丁
“生活不止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一个月来,这句话在朋友圈沸沸扬扬地刷屏,七珍八味的鸡汤鸭血一起装饰出一场与现实不太合拍的文艺宴席。也许高晓松自己也有点儿不好意思,所以搬出母亲大人来说出这句煽情的话。而高晓松那个穿着大裤衩儿,扇着大折扇,八卦着曾经父母近邻的民国女神林徽因的微胖随意形象一下子在眼前风雅诗意起来。尽管诗和远方让我联想起我不太情愿称之为诗人的汪国真,倒确实是标志性的理想的代名词。
十年前的古城西安,郑钧操着慵懒的摇滚歌手中稀有的磁性嗓音,拨弄着吉他,意淫着《私奔》,逃离和遥远城镇。因着理想,自由的意象缘故,本来歌词字面上的男女私情就升华到摇滚歌者人文意义上的彷徨,挣扎和抗争。
近七十年前的一个开了十七年公车而任劳任怨的纽约公车司机威廉·希米洛(william cimillo),在某一天,忽觉厌倦了每天雷同的车站街道,决定不回公车总站,而是把公车开出了纽约城,开去了阳光灿烂的佛罗里达。威廉的离谱行径没有受到法规制裁和舆论的谴责,相反却得到了一个英雄和超级明星才该获取的公众知名度和粉丝群。
一个世纪前的伦敦金融街,一个平凡证券所的乏味经纪人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在夏日假期结束后,离开可爱的妻儿,一个世俗公认的美满家庭,跑到巴黎画画儿。如果我们敬仰的英国小说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在《月亮和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里以这样的基调来杜撰他的主人公,虽然会流于俗套,却也不失读者共鸣。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永远骨感。理想和现实,这对人生永恒经典的矛盾,也可以成为文学的经久不衰的主题。
但是随着毛姆的笔,我们发现却似乎不仅此而已,思特里克兰德简直就是一个魔鬼附身的恶棍。他抛弃妻儿,没有丝毫内疚,更不给他们留下些许供养。他对自己在重病中救他一命的善良的荷兰画家施特略夫的绝好回报是夺走他挚爱的妻子勃朗什。而同样,他回报这个无可救药地爱上他的女人的方式仍然是抛弃,以至于她吞草酸自绝。他自私,粗鲁,毫无礼貌,毫无责任感,令人厌憎,这似乎怎么也不能和追逐理想的高贵灵魂扯上关系。
一位书友悠悠道来:这部小说好比一个桃花源,须缘溪行,忘路远近,入山口,穿窄径,才豁然开朗。那么毛姆究竟想展现给读者怎样一个桃花源呢?在这个五十八章节的小说中,毛姆用了四十几章描述了恶棍思特里克兰德抛妻弃子,恩将仇报的在巴黎令人憎恶鄙视的潦倒罪恶生活。当然也竭尽笔力来炫耀了一下自己对绘画艺术的修养和见识。他也坦诚地承认自己并没有敏锐的艺术鉴赏能力。思特里克兰德画中的简朴笨拙,变形不成比例的实物,夸张原始而不真实的色调,和他自己所习惯欣赏的古典主义的精美,以及早期印象画派的光影陆离的渲染美感,都有强烈反差。不过在画中,他看到了思特里克兰德挣扎着想要表现的一种力量,痛苦,扭曲。究竟怎样的艺术才算伟大的艺术?
与“我”的平常艺术鉴赏力相反,善良而平庸的荷兰画家施特略夫,却有一双识才慧眼,他实在更适合做一个艺术鉴赏家。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诹”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励志口号,如果认为《中华好诗词》上熟背诗词的诗柜词篓可以写出灵性好诗,似乎很值得怀疑。世界上最不靠谱的培训班之一莫过作家诗人培训班了,想象一纸培训证书所担保的一个批量生产千篇一律的诗歌小说的流水线。犀利刻薄的林妹妹也曾经这样讥笑宝哥哥的四平八稳的螃蟹咏:“这样的诗,一时要一百首也有”。果真如此,肯定无人去读。言归正传,艺术家需要天赋,需要敏锐而迥异超常的个性。只是小说中表现出的天才的自私怪诞,善良人的平庸,实在令人唏嘘。
在小说的四十几章之后毛姆终于写到了塔希提岛,思特里克兰德的桃花源。
思特里克兰德不是要逃到远方的某个虚无缥缈的理想中,而是那个塔希提小岛本来就是他的归属,就像阿伯拉罕医生的亚历山大港一样。“有些人诞生在某一个地方可以说未得其所。机缘把他们随便抛掷到一个环境中,而他们却一直思念着一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坐落在何处的家乡。在出生的地方他们好象是过客”,而世界上总有那么个地方,你一见到就似曾相识,而这个地方不是你的远方,而是你的归宿。没有找到这个地方时,他是烦躁的,粗鲁的,冷嘲热讽,自私冷漠。而在这个地方,四十七岁以后他才找到的地方,他是和蔼,平静的,很讨土人喜欢。在没有找到归属之前,他对思特里克兰德夫人冷漠离弃,对施特略夫夫人始乱终弃,而在找到归宿之后,与深爱着自己的年轻单纯专一的少女爱塔温馨相处如平静淡然的一对正常夫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默许她的陪伴。如果这个宿命归属在召唤,他别无选择。他在巴黎回答思特里克兰德夫人的说客“我”的责难时说的是:
“我要画画儿”。“我必须画画儿”。
不是他想画画,是必须。就好像雪雁在初春,在随时存在的暴风雪危险中毅然决然地向北飞行;就像男人在找到拥有自己肋骨的女人后失去理智的疯狂爱情;就像受到神的召唤的以色列先人一样,抛开一切奔向自己的应许之地。他不能自控,他不是他自己,“他好象是一个终生跋涉的朝香者,永远思慕着一块圣地。盘踞在他心头的魔鬼对他毫无怜悯之情。世上有些人渴望寻获真理,他们的要求非常强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是叫他们把生活的基础完全打翻,也在所不惜。”
毛姆对这个浩渺太平洋之中的归属地毫不吝啬笔墨。“与人寰隔绝的一个幽僻的角落,头顶上是蔚蓝的天空,四围一片郁郁苍苍的树木。那里是观赏不尽的色彩,芬芳馥郁的香气,荫翳凉爽的空气。这个人世乐园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 可爱的土著少女妻子爱塔,用椰子油炸五颜六色的鱼,有时还有龙虾,螃蟹。河里面洗澡钓鱼,用椰子的出产换肥皂和日用品,悠闲时就围着一条蓝红两色棉布的帕利欧躺在凉台上。这确实是伊甸园,人不必辛苦劳作忧烦困扰就可以有丰厚收获供给。毛姆似乎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老婆婆和孙女,不知名的少年,美丽少女爱塔,他们的孩子,他所有伊甸园的模特都在那里,他的归宿地在那里,他所痛苦挣扎追随的美都在那里,他把这一切大自然原始美的赞歌,通过他迥异的思维构想再现在小屋的壁画上,虽然伴随他的死而付之一炬,但是他找到了,他满足了,他的生命完全了。这遗失的壁画让人不自觉地联想起高更那幅《我们从哪里来》。但是小说写到这里,思特里克兰德这个人物,是不是以传奇绘画大师高更为原型,在这里已经不重要了,他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标志。
浏览附件593526
远方,是以本地为坐标来命名的;私奔,也是以正统的媒证婚娶来鄙视的。那么,它们就只能存在于幻想觊觎之中。高晓松在抛出远方和诗的石子儿溅起一波又一波的涟漪之后,还是摇着扇子以《晓松奇谈》谋生。郑钧在意淫之后,依然拥娇妻爱女,时不时在导师席上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或者在舞台上蹦跶几下来为跟他一样早过了不惑之年许久的粉丝们吼几句《赤裸裸》,一起追忆一下青春时的异想天开。纽约的公车司机威廉,玩儿一次招摇过市胆大妄为的把戏,又安心回去每天循规蹈矩地开公车长达十六年之久。
而月亮,是不是就不同呢?即使你低着头找着脚下的早已不再作为货币使用的英国六便士,或者刻印着加拿大大雁的卢尼,看不见头顶的月亮,但是月光似乎永远披在你的肩膀上,如水如银。
如果昆德拉的《庆祝无意义》,是让人明白微不足道的才可以长久,认识到平淡是真,那么毛姆的月亮就让人想入非非,就像月圆之夜总是诡异无常。你感受到了使命的召唤吗?你找到了你的归属吗?或者你的使命感已经在你的大脑中封印,或者你祖先遗留在你身体里的基因已经变异,转向。
单这题目就很醒脑啊...<诗,远方,私奔以及月亮>

 ,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写的非常好,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角度的解读。对于艺术家我们一般不会在道德上过多的苛求,杰出的艺术家往往对世俗规范毫无顾忌,展现出特别自私任性和不稳定的一面,但也正是他们桀骜不驯的内心世界,才成就了他们的与众不同的艺术成就.
,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写的非常好,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角度的解读。对于艺术家我们一般不会在道德上过多的苛求,杰出的艺术家往往对世俗规范毫无顾忌,展现出特别自私任性和不稳定的一面,但也正是他们桀骜不驯的内心世界,才成就了他们的与众不同的艺术成就.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追求理想可能太空泛太遥远了,不如就说追求“自我”吧。
现代人比较讲究平衡,都有一点点,生活才有滋有味
最后编辑:
叔丁
捻冰箫以弄梅花,凝气剑而笑江湖
- 注册
- 2014-06-22
- 消息
- 158
- 荣誉分数
- 338
- 声望点数
- 173
- 注册
- 2014-04-15
- 消息
- 6,048
- 荣誉分数
- 11,373
- 声望点数
- 1,323
读了叔丁的文字,很亲切。写得很美! 回忆起很多年前读过这篇小说。 当时只觉得特别压抑,就看不出主人公的希望。很像中国一篇描写旧上海的小说,主人公也是极其懦弱,似乎每天都向一个深洞陷下去。从人性来讲, 可以理解。 从人格上来讲, 又是那么大的断层, 就像发生了地震和海啸沧海变成了桑田高山一样。 艺术的召唤被托出海面, 却干枯得裂痕万道,千疮百孔。毛姆把这种痛表达出来,这种撕痛一定是很多人都体会过的吧? 只是不知道它是镶在骨子里的东西。诗,远方,私奔以及月亮
——读毛姆《月亮和六便士》
文/叔丁
“生活不止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一个月来,这句话在朋友圈沸沸扬扬地刷屏,七珍八味的鸡汤鸭血一起装饰出一场与现实不太合拍的文艺宴席。也许高晓松自己也有点儿不好意思,所以搬出母亲大人来说出这句煽情的话。而高晓松那个穿着大裤衩儿,扇着大折扇,八卦着曾经父母近邻的民国女神林徽因的微胖随意形象一下子在眼前风雅诗意起来。尽管诗和远方让我联想起我不太情愿称之为诗人的汪国真,倒确实是标志性的理想的代名词。
十年前的古城西安,郑钧操着慵懒的摇滚歌手中稀有的磁性嗓音,拨弄着吉他,意淫着《私奔》,逃离和遥远城镇。因着理想,自由的意象缘故,本来歌词字面上的男女私情就升华到摇滚歌者人文意义上的彷徨,挣扎和抗争。
近七十年前的一个开了十七年公车而任劳任怨的纽约公车司机威廉·希米洛(william cimillo),在某一天,忽觉厌倦了每天雷同的车站街道,决定不回公车总站,而是把公车开出了纽约城,开去了阳光灿烂的佛罗里达。威廉的离谱行径没有受到法规制裁和舆论的谴责,相反却得到了一个英雄和超级明星才该获取的公众知名度和粉丝群。
一个世纪前的伦敦金融街,一个平凡证券所的乏味经纪人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在夏日假期结束后,离开可爱的妻儿,一个世俗公认的美满家庭,跑到巴黎画画儿。如果我们敬仰的英国小说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在《月亮和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里以这样的基调来杜撰他的主人公,虽然会流于俗套,却也不失读者共鸣。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永远骨感。理想和现实,这对人生永恒经典的矛盾,也可以成为文学的经久不衰的主题。
但是随着毛姆的笔,我们发现却似乎不仅此而已,思特里克兰德简直就是一个魔鬼附身的恶棍。他抛弃妻儿,没有丝毫内疚,更不给他们留下些许供养。他对自己在重病中救他一命的善良的荷兰画家施特略夫的绝好回报是夺走他挚爱的妻子勃朗什。而同样,他回报这个无可救药地爱上他的女人的方式仍然是抛弃,以至于她吞草酸自绝。他自私,粗鲁,毫无礼貌,毫无责任感,令人厌憎,这似乎怎么也不能和追逐理想的高贵灵魂扯上关系。
一位书友悠悠道来:这部小说好比一个桃花源,须缘溪行,忘路远近,入山口,穿窄径,才豁然开朗。那么毛姆究竟想展现给读者怎样一个桃花源呢?在这个五十八章节的小说中,毛姆用了四十几章描述了恶棍思特里克兰德抛妻弃子,恩将仇报的在巴黎令人憎恶鄙视的潦倒罪恶生活。当然也竭尽笔力来炫耀了一下自己对绘画艺术的修养和见识。他也坦诚地承认自己并没有敏锐的艺术鉴赏能力。思特里克兰德画中的简朴笨拙,变形不成比例的实物,夸张原始而不真实的色调,和他自己所习惯欣赏的古典主义的精美,以及早期印象画派的光影陆离的渲染美感,都有强烈反差。不过在画中,他看到了思特里克兰德挣扎着想要表现的一种力量,痛苦,扭曲。究竟怎样的艺术才算伟大的艺术?
与“我”的平常艺术鉴赏力相反,善良而平庸的荷兰画家施特略夫,却有一双识才慧眼,他实在更适合做一个艺术鉴赏家。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诹”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励志口号,如果认为《中华好诗词》上熟背诗词的诗柜词篓可以写出灵性好诗,似乎很值得怀疑。世界上最不靠谱的培训班之一莫过作家诗人培训班了,想象一纸培训证书所担保的一个批量生产千篇一律的诗歌小说的流水线。犀利刻薄的林妹妹也曾经这样讥笑宝哥哥的四平八稳的螃蟹咏:“这样的诗,一时要一百首也有”。果真如此,肯定无人去读。言归正传,艺术家需要天赋,需要敏锐而迥异超常的个性。只是小说中表现出的天才的自私怪诞,善良人的平庸,实在令人唏嘘。
在小说的四十几章之后毛姆终于写到了塔希提岛,思特里克兰德的桃花源。
思特里克兰德不是要逃到远方的某个虚无缥缈的理想中,而是那个塔希提小岛本来就是他的归属,就像阿伯拉罕医生的亚历山大港一样。“有些人诞生在某一个地方可以说未得其所。机缘把他们随便抛掷到一个环境中,而他们却一直思念着一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坐落在何处的家乡。在出生的地方他们好象是过客”,而世界上总有那么个地方,你一见到就似曾相识,而这个地方不是你的远方,而是你的归宿。没有找到这个地方时,他是烦躁的,粗鲁的,冷嘲热讽,自私冷漠。而在这个地方,四十七岁以后他才找到的地方,他是和蔼,平静的,很讨土人喜欢。在没有找到归属之前,他对思特里克兰德夫人冷漠离弃,对施特略夫夫人始乱终弃,而在找到归宿之后,与深爱着自己的年轻单纯专一的少女爱塔温馨相处如平静淡然的一对正常夫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默许她的陪伴。如果这个宿命归属在召唤,他别无选择。他在巴黎回答思特里克兰德夫人的说客“我”的责难时说的是:
“我要画画儿”。“我必须画画儿”。
不是他想画画,是必须。就好像雪雁在初春,在随时存在的暴风雪危险中毅然决然地向北飞行;就像男人在找到拥有自己肋骨的女人后失去理智的疯狂爱情;就像受到神的召唤的以色列先人一样,抛开一切奔向自己的应许之地。他不能自控,他不是他自己,“他好象是一个终生跋涉的朝香者,永远思慕着一块圣地。盘踞在他心头的魔鬼对他毫无怜悯之情。世上有些人渴望寻获真理,他们的要求非常强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是叫他们把生活的基础完全打翻,也在所不惜。”
毛姆对这个浩渺太平洋之中的归属地毫不吝啬笔墨。“与人寰隔绝的一个幽僻的角落,头顶上是蔚蓝的天空,四围一片郁郁苍苍的树木。那里是观赏不尽的色彩,芬芳馥郁的香气,荫翳凉爽的空气。这个人世乐园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 可爱的土著少女妻子爱塔,用椰子油炸五颜六色的鱼,有时还有龙虾,螃蟹。河里面洗澡钓鱼,用椰子的出产换肥皂和日用品,悠闲时就围着一条蓝红两色棉布的帕利欧躺在凉台上。这确实是伊甸园,人不必辛苦劳作忧烦困扰就可以有丰厚收获供给。毛姆似乎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老婆婆和孙女,不知名的少年,美丽少女爱塔,他们的孩子,他所有伊甸园的模特都在那里,他的归宿地在那里,他所痛苦挣扎追随的美都在那里,他把这一切大自然原始美的赞歌,通过他迥异的思维构想再现在小屋的壁画上,虽然伴随他的死而付之一炬,但是他找到了,他满足了,他的生命完全了。这遗失的壁画让人不自觉地联想起高更那幅《我们从哪里来》。但是小说写到这里,思特里克兰德这个人物,是不是以传奇绘画大师高更为原型,在这里已经不重要了,他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标志。
浏览附件593526
远方,是以本地为坐标来命名的;私奔,也是以正统的媒证婚娶来鄙视的。那么,它们就只能存在于幻想觊觎之中。高晓松在抛出远方和诗的石子儿溅起一波又一波的涟漪之后,还是摇着扇子以《晓松奇谈》谋生。郑钧在意淫之后,依然拥娇妻爱女,时不时在导师席上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或者在舞台上蹦跶几下来为跟他一样早过了不惑之年许久的粉丝们吼几句《赤裸裸》,一起追忆一下青春时的异想天开。纽约的公车司机威廉,玩儿一次招摇过市胆大妄为的把戏,又安心回去每天循规蹈矩地开公车长达十六年之久。
而月亮,是不是就不同呢?即使你低着头找着脚下的早已不再作为货币使用的英国六便士,或者刻印着加拿大大雁的卢尼,看不见头顶的月亮,但是月光似乎永远披在你的肩膀上,如水如银。
如果昆德拉的《庆祝无意义》,是让人明白微不足道的才可以长久,认识到平淡是真,那么毛姆的月亮就让人想入非非,就像月圆之夜总是诡异无常。你感受到了使命的召唤吗?你找到了你的归属吗?或者你的使命感已经在你的大脑中封印,或者你祖先遗留在你身体里的基因已经变异,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