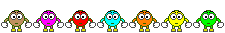斯坦福教授: 别给孩子一个清单式人生
文章来源 : 蓝橡树 2018年10月08日 分享文章 5117
这是一个竞争日渐激烈的时代,一方面我们在感慨孩子课业压力太大,社会对他们的要求太高,一方面我们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孩子成绩好不好,才艺学得够不够多,有没有按照常春藤大学标准打造履历表,能不能考入好大学,从而有一个看得见的光明的未来。
朱莉(Julie Lythcott-Haims),斯坦福大学前新生教导主任,对现代家长的育儿方式很担忧,提倡父母停止用分数去衡量孩子的成功,强调无私的爱才是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我们都希望孩子有一个幸福的未来,可是过高的期许和事无巨细的干预往往事与愿违。孩子有孩子的未来,我们给孩子的不应该是一份清单式的人生!

........................................
清单式人生
我可从没打算变成个育儿专家,甚至对于育儿都没有太大兴趣。只不过看到如今有些教育方式把孩子们搞得一团糟,让他们失去了做自己的机会,而且这些育儿方式正越来越大行其道。
我们总把焦点放在那些对孩子的成长教育投入不够的父母身上,这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那些与此做法截然相反的父母,他们对孩子们成长的危害同样不可估量。这些父母觉得一个孩子的成功有赖于他们的保护,他们密切地关注着孩子的每一刻,及时阻止每一个错误的决定,事无巨细,然后成功地把孩子导向某些自己满意的大学和职业中去。
如果我们这样养育自己的孩子——说“我们”,因为作为两个青春期孩子的妈妈,我也常常有这种倾向——那他们最后拥有的只能是个清单式的童年。
这个清单大致如下:
保证孩子安全健康吃饱喝足,然后保证他们去正确的学校,正确的班级,然后在那里他们要取得满意的分数。而且只有分数可不够,各种奖项,运动项目,校外活动,领导机会也必不可少。我们跟孩子说,别仅仅加入个俱乐部,你得自己组建一个,因为大学申请看重这个。哦别忘了社区服务也得要打勾,呃。。我的意思是申请大学时你得体现出对社区和其他人的关心。我们希望所有这些都完成得尽善尽美。
我们的孩子肩负着比我们自己曾经肩负过的更高的期望,于是我们觉得理所应当的,有必要和每一个老师、校长、教练,还有写推荐信的人去尽量争取,于是我们义不容辞地成为孩子的服务生、私人助理和秘书。
面对孩子们,这些我们无比珍视的孩子们,我们会花充足的时间去鼓励、激励、暗示、帮助、买通、喋喋不休,希望避免他们把事情搞糟弄乱,阻止他们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防止他们毁灭了自己的未来,这里的未来特别是指被那几个竞争极为严酷大学录取的可能性。
清单式人生对孩子的影响
生活在清单式童年中是什么感觉呢?
首先,没时间自由地玩儿。下午肯定没空,因为每件事都必须让孩子收获更充实。似乎每一份家庭作业,每一次测验,每一个活动对于我们预定好的将来都有着决定性意义。于是我们可以取消孩子做家务的义务,只要他们能保证完成清单上项目,睡眠不足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在清单式的童年里,父母通常会说:我只想让孩子快乐!可是当孩子们从学校回来,有太多次我们首先询问的是他们的作业和成绩。而我们脸上表达出的肯定、爱,以及他们的价值,却来自于许许多多的A。
然后我们走在他们身边,轻声地给他们一点点儿表扬,就好像 Westminster狗狗大赛(注:美国历史第二悠久的连续举行的体育赛事。奥运会可以被战争打断,可Westminster风雨无阻枪炮无阻地在纽约麦迪逊花园举行了129年)里的训养员一样引导着他们一天比一天跳得更高点,更远点。
当孩子们上了高中,他们不会问:“我在课外应该学点什么做点什么?” 他们会问学校的教员:“我需要怎么做才能去个好大学?”然后,当一份份高中成绩单陆续出炉,上面有几个B,甚至出现了上帝都不允许的C时,他们开始惊慌失措地给朋友发短信:“你知道有人曾经拿着这种成绩去了好大学吗?”
于是我们的孩子们,无论他们在高中的排名如何,他们都被压的喘不过气。他们变得脆弱、过劳,甚至有点老气横秋。他们希望听到父母说:“你已经做的足够了,你已经很努力了。” 在焦虑症和抑郁症高发的年龄段,他们开始凋零,开始怀疑:这样的生活值得吗?
父母们,我们这些父母们非常确定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们表现的 -- 就如我们真的相信--如果不能够进入那么几个大学或者那几种职业,我们的孩子就没有未来可言。
也许,我们只是担心害怕他们没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在朋友面前夸耀的未来,没法让我们在车尾贴上那几个精英学校的校徽。
清单式人生的害处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勇气仔细看看这样做的后果,你会发现不仅仅是孩子们把自己的价值简单地等同于成绩,而且就在我们把自己的意识强加于他们宝贵的成长中时,就像电影《Being JohnMalkovich》那样,我们就在发出这样的信号:“嘿宝贝,你能做到这一切全靠我。” 于是通过过分的帮助、保护和手把手的指挥,我们剥夺了孩子们发展自我效能的机会。
(注:自我效能(self-efficacy) 是当代最重要的心理学家之一Albert Bandura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个人对于通过自己的行动达成目的的信心,是一个包含了自信自律自强的概念,似乎和周易里面那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类同)。
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心理天赋,自我效能的重要性远高于他们从父母的表扬中所建立的自尊。自我效能建立在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能够导致某种结果,注意是自己的,而不是父母的行为。所以简单来说,如果我们的孩子要建立自我效能,那他们要有更多的思考、计划、决策、实践、期望、妥协、尝试、犯错、想象还有体验自己的人生。
我有没有说过每个孩子都是努力的,有主动性的,因而不需要父母的参与和关心,我们大可放手让他们自由发挥?我可没有!
我要说的是,当我们把分数,成绩,和奖项当作是童年的目标,完全为了将来能够有希望进入那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学或者职业,那我们对于孩子成功的定义就太狭隘了。即使我们通过过度帮助让他们达成一些短期的成果,例如帮他们完成作业拿到好成绩,或者让他们的简历更长点,可长远的代价却是孩子们的自我意识。
我要说的是,我们应该少把注意力放在那少数几个他们能够申请或者有希望进入的大学,而更多的关注他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掌握的技能,和健康状况,这些让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能取得成功的东西;
我要说的是,我们的孩子需要我们减少一点对分数成绩的苛求,而把更多的兴趣放在一个可以为未来成功打好基础的童年,放在一个建立在爱和“琐事”上的童年。
爱和琐事
我是不是提到了“琐事”?
的确如此。
历史上最长的关于人类的纵向研究(注:长期追踪一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叫做 Harvard Grant Study。这份研究发现事业有成,这种我们迫切期望孩子们能实现的成功,来自于在童年时做过细碎的,丝毫看不出重要的“琐事”。而且越早开始,效果就越好。
那种卷起袖子埋头苦干的意识会告诉他们:总要有个人去完成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任务,那个人也许就是我。这种意识还会告诉他们:我要用自己的努力成就集体的进步。在职场中,正是这种表现会让你得到赏识提升,走在前面。我想你我都已经知道这一点。
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可是在清单式童年中,我们默许孩子们别去碰那些细碎无聊的家务。于是当他们成年以后,这些孩子会在职场中等待着为他们准备的清单。可那份清单并不存在!而更严重的是,他们没有卷起袖子埋头苦干的热情,没有的环顾四周,想想能帮同事做点什么,能够提前帮老板准备点什么的习惯和本能。
Harvard Grant Study 的另一个发现是幸福来自于爱,不是对工作的爱,而是对人的爱,对伴侣、朋友、家庭的爱。所以童年应该教会孩子们如何去爱,他们只有先爱自己才能学会去爱别人,而只有得到了父母无条件的爱,他们才能学会爱自己。
没错!所以当我们的孩子从学校回来,或者我们下班回家,我们不应该再只去关注分数和成绩,我们应该暂时告别高科技的行头,把手机放到一边,看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读到那种当他们刚出生时我们发自内心的喜悦。然后我们应该说,“今天过的怎么样?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吗?”
如果他们像我青春期的女儿一样回答: “午饭,”,即使恰恰你像我一样真正想听到的是数学测验,而不是午饭,你还是要对午饭提起兴趣。你得说,“今天的午饭为什么那么有趣?”你要让孩子们知道我们在乎的是他们,而不是他们的GPA。
成功与幸福
好吧,现在你会想,“琐事”和爱,这些听起来是不错,不过别跟我扯这些,大学申请靠的是分数、成绩单、奖项。而我要说,不全是。那些最大牌的学校要求的确如此,不过好消息是:和那些让人无所适从的大学排名榜试图灌输给我们的理念不同,一个人幸福和成功并不需要来自于这几个大牌学校。幸福和成功的人有去州立大学、社区大学、没人听说过的小学校,或者在这上到一半退学了。
证据呢?证据就在这个房间里,在我们的社区里,如果我们愿意打开百叶窗,愿意多看看几所学校,愿意暂时把我们的自负放在一边,我们就可以接受并且拥抱这个事实。然后我们就会意识到,就算我的孩子没能进入那几个大牌学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们的童年不是在完成一份专制的清单,那么当他们进入大学时,无论是哪所大学,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做出了选择,他们已经做好准备,要靠着自己的能力去闪闪发光。
我得向你们承认,就像我之前提到过的,我有两个青春期的孩子 Sawyer 和 Avery。曾经有段时间,我觉得我对待他们俩就好像对盆景树一样,我会精心的剪裁,把他们塑造得完美无缺,完美到确保让他们进入那几所最难进的大学。但是通过养育自己的两个孩子,通过和上千位其他人的孩子一起共事,我意识到Sawyer 和 Avery 不是盆景。
他们是不知名不知种类的野花,而我的任务是为他们提供养分,让他们经历锤炼,爱他们使他们能去爱别人并收获爱,让他们能按照自己的轨迹收获学业和事业。我的任务不是让他们变成我想象中的 Sawyer 和 Avery,我的任务是支持他们成为熠熠发光的自己!
文章来源 : 蓝橡树 2018年10月08日 分享文章 5117
这是一个竞争日渐激烈的时代,一方面我们在感慨孩子课业压力太大,社会对他们的要求太高,一方面我们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孩子成绩好不好,才艺学得够不够多,有没有按照常春藤大学标准打造履历表,能不能考入好大学,从而有一个看得见的光明的未来。
朱莉(Julie Lythcott-Haims),斯坦福大学前新生教导主任,对现代家长的育儿方式很担忧,提倡父母停止用分数去衡量孩子的成功,强调无私的爱才是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我们都希望孩子有一个幸福的未来,可是过高的期许和事无巨细的干预往往事与愿违。孩子有孩子的未来,我们给孩子的不应该是一份清单式的人生!

........................................
清单式人生
我可从没打算变成个育儿专家,甚至对于育儿都没有太大兴趣。只不过看到如今有些教育方式把孩子们搞得一团糟,让他们失去了做自己的机会,而且这些育儿方式正越来越大行其道。
我们总把焦点放在那些对孩子的成长教育投入不够的父母身上,这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那些与此做法截然相反的父母,他们对孩子们成长的危害同样不可估量。这些父母觉得一个孩子的成功有赖于他们的保护,他们密切地关注着孩子的每一刻,及时阻止每一个错误的决定,事无巨细,然后成功地把孩子导向某些自己满意的大学和职业中去。
如果我们这样养育自己的孩子——说“我们”,因为作为两个青春期孩子的妈妈,我也常常有这种倾向——那他们最后拥有的只能是个清单式的童年。
这个清单大致如下:
保证孩子安全健康吃饱喝足,然后保证他们去正确的学校,正确的班级,然后在那里他们要取得满意的分数。而且只有分数可不够,各种奖项,运动项目,校外活动,领导机会也必不可少。我们跟孩子说,别仅仅加入个俱乐部,你得自己组建一个,因为大学申请看重这个。哦别忘了社区服务也得要打勾,呃。。我的意思是申请大学时你得体现出对社区和其他人的关心。我们希望所有这些都完成得尽善尽美。
我们的孩子肩负着比我们自己曾经肩负过的更高的期望,于是我们觉得理所应当的,有必要和每一个老师、校长、教练,还有写推荐信的人去尽量争取,于是我们义不容辞地成为孩子的服务生、私人助理和秘书。
面对孩子们,这些我们无比珍视的孩子们,我们会花充足的时间去鼓励、激励、暗示、帮助、买通、喋喋不休,希望避免他们把事情搞糟弄乱,阻止他们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防止他们毁灭了自己的未来,这里的未来特别是指被那几个竞争极为严酷大学录取的可能性。
清单式人生对孩子的影响
生活在清单式童年中是什么感觉呢?
首先,没时间自由地玩儿。下午肯定没空,因为每件事都必须让孩子收获更充实。似乎每一份家庭作业,每一次测验,每一个活动对于我们预定好的将来都有着决定性意义。于是我们可以取消孩子做家务的义务,只要他们能保证完成清单上项目,睡眠不足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在清单式的童年里,父母通常会说:我只想让孩子快乐!可是当孩子们从学校回来,有太多次我们首先询问的是他们的作业和成绩。而我们脸上表达出的肯定、爱,以及他们的价值,却来自于许许多多的A。
然后我们走在他们身边,轻声地给他们一点点儿表扬,就好像 Westminster狗狗大赛(注:美国历史第二悠久的连续举行的体育赛事。奥运会可以被战争打断,可Westminster风雨无阻枪炮无阻地在纽约麦迪逊花园举行了129年)里的训养员一样引导着他们一天比一天跳得更高点,更远点。
当孩子们上了高中,他们不会问:“我在课外应该学点什么做点什么?” 他们会问学校的教员:“我需要怎么做才能去个好大学?”然后,当一份份高中成绩单陆续出炉,上面有几个B,甚至出现了上帝都不允许的C时,他们开始惊慌失措地给朋友发短信:“你知道有人曾经拿着这种成绩去了好大学吗?”
于是我们的孩子们,无论他们在高中的排名如何,他们都被压的喘不过气。他们变得脆弱、过劳,甚至有点老气横秋。他们希望听到父母说:“你已经做的足够了,你已经很努力了。” 在焦虑症和抑郁症高发的年龄段,他们开始凋零,开始怀疑:这样的生活值得吗?
父母们,我们这些父母们非常确定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们表现的 -- 就如我们真的相信--如果不能够进入那么几个大学或者那几种职业,我们的孩子就没有未来可言。
也许,我们只是担心害怕他们没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在朋友面前夸耀的未来,没法让我们在车尾贴上那几个精英学校的校徽。
清单式人生的害处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勇气仔细看看这样做的后果,你会发现不仅仅是孩子们把自己的价值简单地等同于成绩,而且就在我们把自己的意识强加于他们宝贵的成长中时,就像电影《Being JohnMalkovich》那样,我们就在发出这样的信号:“嘿宝贝,你能做到这一切全靠我。” 于是通过过分的帮助、保护和手把手的指挥,我们剥夺了孩子们发展自我效能的机会。
(注:自我效能(self-efficacy) 是当代最重要的心理学家之一Albert Bandura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个人对于通过自己的行动达成目的的信心,是一个包含了自信自律自强的概念,似乎和周易里面那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类同)。
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心理天赋,自我效能的重要性远高于他们从父母的表扬中所建立的自尊。自我效能建立在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能够导致某种结果,注意是自己的,而不是父母的行为。所以简单来说,如果我们的孩子要建立自我效能,那他们要有更多的思考、计划、决策、实践、期望、妥协、尝试、犯错、想象还有体验自己的人生。
我有没有说过每个孩子都是努力的,有主动性的,因而不需要父母的参与和关心,我们大可放手让他们自由发挥?我可没有!
我要说的是,当我们把分数,成绩,和奖项当作是童年的目标,完全为了将来能够有希望进入那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学或者职业,那我们对于孩子成功的定义就太狭隘了。即使我们通过过度帮助让他们达成一些短期的成果,例如帮他们完成作业拿到好成绩,或者让他们的简历更长点,可长远的代价却是孩子们的自我意识。
我要说的是,我们应该少把注意力放在那少数几个他们能够申请或者有希望进入的大学,而更多的关注他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掌握的技能,和健康状况,这些让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能取得成功的东西;
我要说的是,我们的孩子需要我们减少一点对分数成绩的苛求,而把更多的兴趣放在一个可以为未来成功打好基础的童年,放在一个建立在爱和“琐事”上的童年。
爱和琐事
我是不是提到了“琐事”?
的确如此。
历史上最长的关于人类的纵向研究(注:长期追踪一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叫做 Harvard Grant Study。这份研究发现事业有成,这种我们迫切期望孩子们能实现的成功,来自于在童年时做过细碎的,丝毫看不出重要的“琐事”。而且越早开始,效果就越好。
那种卷起袖子埋头苦干的意识会告诉他们:总要有个人去完成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任务,那个人也许就是我。这种意识还会告诉他们:我要用自己的努力成就集体的进步。在职场中,正是这种表现会让你得到赏识提升,走在前面。我想你我都已经知道这一点。
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可是在清单式童年中,我们默许孩子们别去碰那些细碎无聊的家务。于是当他们成年以后,这些孩子会在职场中等待着为他们准备的清单。可那份清单并不存在!而更严重的是,他们没有卷起袖子埋头苦干的热情,没有的环顾四周,想想能帮同事做点什么,能够提前帮老板准备点什么的习惯和本能。
Harvard Grant Study 的另一个发现是幸福来自于爱,不是对工作的爱,而是对人的爱,对伴侣、朋友、家庭的爱。所以童年应该教会孩子们如何去爱,他们只有先爱自己才能学会去爱别人,而只有得到了父母无条件的爱,他们才能学会爱自己。
没错!所以当我们的孩子从学校回来,或者我们下班回家,我们不应该再只去关注分数和成绩,我们应该暂时告别高科技的行头,把手机放到一边,看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读到那种当他们刚出生时我们发自内心的喜悦。然后我们应该说,“今天过的怎么样?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吗?”
如果他们像我青春期的女儿一样回答: “午饭,”,即使恰恰你像我一样真正想听到的是数学测验,而不是午饭,你还是要对午饭提起兴趣。你得说,“今天的午饭为什么那么有趣?”你要让孩子们知道我们在乎的是他们,而不是他们的GPA。
成功与幸福
好吧,现在你会想,“琐事”和爱,这些听起来是不错,不过别跟我扯这些,大学申请靠的是分数、成绩单、奖项。而我要说,不全是。那些最大牌的学校要求的确如此,不过好消息是:和那些让人无所适从的大学排名榜试图灌输给我们的理念不同,一个人幸福和成功并不需要来自于这几个大牌学校。幸福和成功的人有去州立大学、社区大学、没人听说过的小学校,或者在这上到一半退学了。
证据呢?证据就在这个房间里,在我们的社区里,如果我们愿意打开百叶窗,愿意多看看几所学校,愿意暂时把我们的自负放在一边,我们就可以接受并且拥抱这个事实。然后我们就会意识到,就算我的孩子没能进入那几个大牌学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们的童年不是在完成一份专制的清单,那么当他们进入大学时,无论是哪所大学,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做出了选择,他们已经做好准备,要靠着自己的能力去闪闪发光。
我得向你们承认,就像我之前提到过的,我有两个青春期的孩子 Sawyer 和 Avery。曾经有段时间,我觉得我对待他们俩就好像对盆景树一样,我会精心的剪裁,把他们塑造得完美无缺,完美到确保让他们进入那几所最难进的大学。但是通过养育自己的两个孩子,通过和上千位其他人的孩子一起共事,我意识到Sawyer 和 Avery 不是盆景。
他们是不知名不知种类的野花,而我的任务是为他们提供养分,让他们经历锤炼,爱他们使他们能去爱别人并收获爱,让他们能按照自己的轨迹收获学业和事业。我的任务不是让他们变成我想象中的 Sawyer 和 Avery,我的任务是支持他们成为熠熠发光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