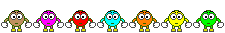“我要到联合国广场去绝食”
“我要到联合国广场去绝食” --白振侠绝食事件追踪报导之一
《多维时报》记者洪浩
白振侠站在曼哈顿42街最西端的丁字路口上,眉头紧锁。他的背后就是中国驻纽约的领事馆,一个他犹豫了许久但最后还是决定来拜见的机构,尽管他深知这里并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尽管他已经先后去过了洛杉矶领事馆和华盛顿的大使馆,都没有得到任何让他满意的答复。
他手里提着的塑料袋里是他特地订制的一套奶白色的中山装,上衣的领口两侧蘸贴着用英文书写的“绝食”,胸前别着的图案上印着一个蓝色大大的“冤”字,“冤”字下面被一把引有红五星的大锁锁住,锁的两旁写着“公正”和“人权”,被一丛绿叶拥托出。他本想穿上这套衣服走进领事馆,将它从带子里取出打量了一番,觉得那与自己此行的目的不相符,便又放回到塑料袋中。
白振侠另一只手提着的书包里放着他准备好的申诉材料,他曾经在另外两个地方递交过同样的内容,而得到的只是漫长的等待、无可奈何的劝告和毫无结果的回复。他在等待中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个陌生的国家,从西海岸到东海岸,他越来越清楚自己不可能通过中国的官方渠道使自己的诉求得到应有的重视。
“我要到联合国广场去绝食。”
这是他对领馆接待人员说的第一句话,也是他思考了许久后终于下定决心要采取的行动。其实,他原本在准备行动前决定到领馆拜访的初衷,并不是想把他已经向别人诉说过无数次的经历再来重复一次,“我觉得我应该到领馆门前磕个头。我这是要把咱中国人的家丑亮给外国人了,觉得有点对不住。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2001年12月,白振侠住在北京西城区德胜门外的房子被强制搬迁了,他认为当地拆迁办给予的搬迁赔偿--7万元人民币--远远低于他那在两间房子的市场价格,当左邻右舍的街坊们在无力的抗争之后不得不纷纷搬走的情况下,白振侠却将自己套上自制的盔甲,坚守在屋里,成了该地区最大的一个“钉子户”。“除非推土机将我一同铲走,否则我就和你们对峙下去了。”他对门外包围着的警察声明。
寒冬腊月的日子里,房间里被切断了水电,外面是两辆警车、十多名警察和保安、以及拆迁队推土机24小时的包围和封锁,不准他与任何人接近。他在屋里与警察对峙了二十五个日夜,事先囤积的半个月的食物消耗殆尽,只能靠冷水就着乾脆面度日,身体极度虚弱,每天腹泄七、八次,近乎崩溃边缘。然而,精神的损伤更大,造成了他精神衰弱,至今仍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白振侠与警察对峙了二十五天,脚上由一条铁练固定在地上。(多维资料)
“我实在是顶不住了,他们一直在同我讨价还价,价钱涨到了二十五万,这是我抗争来的啊。因为抗争才能带来谈判,才能有妥协,虽然那远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可我实在挺不下去了,我只好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可谁知,协议书上附带着两个条件,一是我必须进拘留所,理由是‘抗拒政府机构执行公务’;二是我得保证以后再也不能回西城区,不能找任何媒体,不做任何不利于拆迁公司的宣传。这是什么条件啊?这里是我生长了一辈子的地方啊,就不能回来了?我是在刀架在脖子上的情况下签的字,这能让人心服吗?”
白振侠越说越激动,禁不住泣不成声,他已经记不得将自己的经历向多少人倾诉过,住在一齐的室友,打工店的老板同事,媒体的记者。但是,在领事馆的接待人员面前,他第一次骨哽喉咽,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淌下来。“我没有做过对不起谁的事,安分守己,不偷不抢,凭什么就永远不能回西城区了呢?这是哪家的王法啊?拆迁公司的三个股东之一就是西城区政府,这是掠夺,是强占啊!权力保护下的掠夺。我就说,哪怕你想当奴隶主,你就是想更多地剥削奴隶,你也得让奴隶活下去吧?奴隶们活的好一点,才会更卖力。我们这些奴隶要是都没了活路,你们去剥削谁呢?”
白振侠被带出家门后,被警车直接送进了拘留所,他央求到:只关一、两天意思意思行不行?我的身体实在受不了呀。人民警察却毫不为之所动:“没有十天八天的根本不行,区长被你气坏了,太搓火,非要拘你,要不,解不了心头这股恶气。”
从拘留所被放出后,白振侠去医院作了检查,医生诊断,胃肠道三处糜烂。他一边治病疗养,一边整理材料找媒体申诉,没有一家报纸愿意登出他的事情。一家报纸的编辑对他说:“如果是个小地方的县长区长什么的,我们会给你反映反映,可北京的一个区长是能通天的啊。”一位采访过他的北京《信报》的记者,事后受到主编的警告,报导没有刊出。白振侠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政协、以及中央电视台等单位发出过十几封申诉信,无一回复。
医生诊断白振侠胃肠道三处糜烂的纪录。(多维资料)
2002年底,他设法来到美国,却从来没有想到要留下。他一心一意要通过适当的渠道让更高的政府部门知道他的情况,然而,一封封申诉信如石沉大海,根本没有回音。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想到,要一死了之,“要不是我上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父亲,下有十四岁的女儿,我早就去死了。”朋友们劝他,死有什么用呢?他们巴不得你死了呢,死了就再不会给他们找麻烦了。
白振侠并不在惜自己的生命,“我现在反正身体也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怎么着也是个死,活着可能比死还难受。可我知道,即使是死,也要死出个尊严来。人的尊严和被尊重的程度,是和你付出的代价成正比的。作为一个人,我们已经失去了许多权力,我们都忍受了,但是,这个最后的、最最基本的生存权力、居住权力,都被剥夺了,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值得的呢?”
领馆的接待人员对他的情况表示同情,同他在其它地方得到的回答一样,一方面答应他按照有关程序向国内有关部门反映,另一方面劝他向前看,“人生的路还长,还得向前走。”
白振侠理解领馆的难处,“他们有他们的程序,有他们的职权范围,”走出领馆大门时,他说,“他们对我的态度不错,我就已经挺感激了。我知道他们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把我的材料转到市人大信访办?侨务办公室?那能管什么用呢?直接就进了废纸篓。在洛杉矶,有个领事跟我说,想办法留下吧。他宁可让我流放,也不愿给自己找麻烦。”
他是听了朋友的劝告才来领馆的,对他来说,这不过是例行公事,“反正我已经通知他们了,我主意已定,没有别的选择了,联合国广场见。”
在绝食行动之前,白振侠来到曼哈顿中领馆门口求见侨务负责人。(多维资料)
注:另有2张照片过大,无法上传. 原文:
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4_9_28_11_17_39_284.html
“我要到联合国广场去绝食” --白振侠绝食事件追踪报导之一
《多维时报》记者洪浩
白振侠站在曼哈顿42街最西端的丁字路口上,眉头紧锁。他的背后就是中国驻纽约的领事馆,一个他犹豫了许久但最后还是决定来拜见的机构,尽管他深知这里并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尽管他已经先后去过了洛杉矶领事馆和华盛顿的大使馆,都没有得到任何让他满意的答复。
他手里提着的塑料袋里是他特地订制的一套奶白色的中山装,上衣的领口两侧蘸贴着用英文书写的“绝食”,胸前别着的图案上印着一个蓝色大大的“冤”字,“冤”字下面被一把引有红五星的大锁锁住,锁的两旁写着“公正”和“人权”,被一丛绿叶拥托出。他本想穿上这套衣服走进领事馆,将它从带子里取出打量了一番,觉得那与自己此行的目的不相符,便又放回到塑料袋中。
白振侠另一只手提着的书包里放着他准备好的申诉材料,他曾经在另外两个地方递交过同样的内容,而得到的只是漫长的等待、无可奈何的劝告和毫无结果的回复。他在等待中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个陌生的国家,从西海岸到东海岸,他越来越清楚自己不可能通过中国的官方渠道使自己的诉求得到应有的重视。
“我要到联合国广场去绝食。”
这是他对领馆接待人员说的第一句话,也是他思考了许久后终于下定决心要采取的行动。其实,他原本在准备行动前决定到领馆拜访的初衷,并不是想把他已经向别人诉说过无数次的经历再来重复一次,“我觉得我应该到领馆门前磕个头。我这是要把咱中国人的家丑亮给外国人了,觉得有点对不住。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2001年12月,白振侠住在北京西城区德胜门外的房子被强制搬迁了,他认为当地拆迁办给予的搬迁赔偿--7万元人民币--远远低于他那在两间房子的市场价格,当左邻右舍的街坊们在无力的抗争之后不得不纷纷搬走的情况下,白振侠却将自己套上自制的盔甲,坚守在屋里,成了该地区最大的一个“钉子户”。“除非推土机将我一同铲走,否则我就和你们对峙下去了。”他对门外包围着的警察声明。
寒冬腊月的日子里,房间里被切断了水电,外面是两辆警车、十多名警察和保安、以及拆迁队推土机24小时的包围和封锁,不准他与任何人接近。他在屋里与警察对峙了二十五个日夜,事先囤积的半个月的食物消耗殆尽,只能靠冷水就着乾脆面度日,身体极度虚弱,每天腹泄七、八次,近乎崩溃边缘。然而,精神的损伤更大,造成了他精神衰弱,至今仍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白振侠与警察对峙了二十五天,脚上由一条铁练固定在地上。(多维资料)
“我实在是顶不住了,他们一直在同我讨价还价,价钱涨到了二十五万,这是我抗争来的啊。因为抗争才能带来谈判,才能有妥协,虽然那远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可我实在挺不下去了,我只好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可谁知,协议书上附带着两个条件,一是我必须进拘留所,理由是‘抗拒政府机构执行公务’;二是我得保证以后再也不能回西城区,不能找任何媒体,不做任何不利于拆迁公司的宣传。这是什么条件啊?这里是我生长了一辈子的地方啊,就不能回来了?我是在刀架在脖子上的情况下签的字,这能让人心服吗?”
白振侠越说越激动,禁不住泣不成声,他已经记不得将自己的经历向多少人倾诉过,住在一齐的室友,打工店的老板同事,媒体的记者。但是,在领事馆的接待人员面前,他第一次骨哽喉咽,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淌下来。“我没有做过对不起谁的事,安分守己,不偷不抢,凭什么就永远不能回西城区了呢?这是哪家的王法啊?拆迁公司的三个股东之一就是西城区政府,这是掠夺,是强占啊!权力保护下的掠夺。我就说,哪怕你想当奴隶主,你就是想更多地剥削奴隶,你也得让奴隶活下去吧?奴隶们活的好一点,才会更卖力。我们这些奴隶要是都没了活路,你们去剥削谁呢?”
白振侠被带出家门后,被警车直接送进了拘留所,他央求到:只关一、两天意思意思行不行?我的身体实在受不了呀。人民警察却毫不为之所动:“没有十天八天的根本不行,区长被你气坏了,太搓火,非要拘你,要不,解不了心头这股恶气。”
从拘留所被放出后,白振侠去医院作了检查,医生诊断,胃肠道三处糜烂。他一边治病疗养,一边整理材料找媒体申诉,没有一家报纸愿意登出他的事情。一家报纸的编辑对他说:“如果是个小地方的县长区长什么的,我们会给你反映反映,可北京的一个区长是能通天的啊。”一位采访过他的北京《信报》的记者,事后受到主编的警告,报导没有刊出。白振侠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政协、以及中央电视台等单位发出过十几封申诉信,无一回复。
医生诊断白振侠胃肠道三处糜烂的纪录。(多维资料)
2002年底,他设法来到美国,却从来没有想到要留下。他一心一意要通过适当的渠道让更高的政府部门知道他的情况,然而,一封封申诉信如石沉大海,根本没有回音。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想到,要一死了之,“要不是我上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父亲,下有十四岁的女儿,我早就去死了。”朋友们劝他,死有什么用呢?他们巴不得你死了呢,死了就再不会给他们找麻烦了。
白振侠并不在惜自己的生命,“我现在反正身体也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怎么着也是个死,活着可能比死还难受。可我知道,即使是死,也要死出个尊严来。人的尊严和被尊重的程度,是和你付出的代价成正比的。作为一个人,我们已经失去了许多权力,我们都忍受了,但是,这个最后的、最最基本的生存权力、居住权力,都被剥夺了,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值得的呢?”
领馆的接待人员对他的情况表示同情,同他在其它地方得到的回答一样,一方面答应他按照有关程序向国内有关部门反映,另一方面劝他向前看,“人生的路还长,还得向前走。”
白振侠理解领馆的难处,“他们有他们的程序,有他们的职权范围,”走出领馆大门时,他说,“他们对我的态度不错,我就已经挺感激了。我知道他们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把我的材料转到市人大信访办?侨务办公室?那能管什么用呢?直接就进了废纸篓。在洛杉矶,有个领事跟我说,想办法留下吧。他宁可让我流放,也不愿给自己找麻烦。”
他是听了朋友的劝告才来领馆的,对他来说,这不过是例行公事,“反正我已经通知他们了,我主意已定,没有别的选择了,联合国广场见。”
在绝食行动之前,白振侠来到曼哈顿中领馆门口求见侨务负责人。(多维资料)
注:另有2张照片过大,无法上传. 原文:
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4_9_28_11_17_39_2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