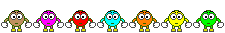六
黑蓝的夜幕里,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变得发红,通过一层透明的红云照进中国芭蕾舞大剧院的展览厅里。静谧的夜色带着一种血色的温柔,在空气中无声地蔓延。窗外一株高大的开始叶落的槐树,繁密的枝叶被秋风摇动着,在窗上扫来扫去。大厅的门口响起了脚步声,两个年轻人挽着手走了进来,站在门口向里面看着,小声说着什么。工作人员停止了故事,向门口看了一眼。
对不起,有人来参观了,我得去门口看一眼,工作人员道歉地对她说。
去吧,我等着你,她点头说。
工作人员向着门口走去了。她坐在藤椅上,身子有些佝偻地靠在椅背上,脸色苍白,面容显得有些疲惫。她觉得有些累了,就换了个姿势坐着,藤椅在身子下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咯吱。她默不作声地看着面前的玻璃柜。柜子的玻璃面上反射着窗外的黑蓝的夜幕,月亮的火红的影子模模糊糊在玻璃上闪耀,星星微弱得几乎看不见。柜里的波斯米亚红裙被顶上垂下来的一束黄色的灯光照射,灯光像是凝固不动一样地打在粗麻布的百褶裙面上。多年以前的一个傍晚,她背着书包放学回家,快到楼门口的时候,看见这件裙子被一个女人伸着胳膊从阳台上扔下来。黑红色的裙子像是一只风筝一样在半空中展开,在风中飘着,飘过了楼下枝叶茂盛的槐树和路边一个卖煎饼的小摊,落到了马路上行驶的一辆运货卡车的绿色篷子上。她拔腿向着卡车追去,向着卡车挥着手,希望能追上卡车叫司机停下来,或者裙子能落到地上好捡起。司机没有看见她,裙子没有落到地上,卡车也离她越来越远。那条红裙最后和卡车一起消失在一座立交桥下。她沮丧地走回家,心里充满了莫名的失落和痛苦,就好象失去了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件东西。她憎恨把那件红裙从阳台上扔下的女人,憎恨把这个女人娶回家的男人。那时她想永远永远的离开家,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再也不回家。
您累了吗?工作人员从门口走了回来问。要不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以后再讲?
你失恋过吗?她没有回答问题,而是直接问工作人员说。
有,也没有,工作人员说。以前有过一个男朋友,后来吹了,但是也算不上什么失恋,因为根本就没恋爱过。他是外地的,大概是看中了我的北京户口。我呢,觉得他人看着挺实在的,挣钱虽然不多,但是好歹有份儿工作,我们就在一起有了几个月,后来他可能找到更好的了,就把我给甩了。
你难受了吗?她继续问工作人员说。
没有,工作人员摇头说。吹就吹了吧,我还看不上他呢。外地的,没房子没车,家里没也钱,人也不是特别帅特别让人心动的那种。
那就好,她说。怕就怕两个人有感情,但是被迫分开,就像这个男芭蕾舞演员和女芭蕾舞演员似的。如果分开了,见不到还好,但是两个人还要天天在剧院里见面,那不是折磨吗?
像他们两个这样爱好芭蕾,与世无争,只想好好跳芭蕾的人,要是在现在的社会里,应该是很幸福的一对,工作人员叹息了一声说。
他们生错了年代,她说。你有什么办法?那个时候中苏关系正在破裂,苏联从老大哥变成了苏修,从同志加兄弟变成了霸权主义,一个中国的芭蕾舞演员爱上了一个苏联的芭蕾舞演员,这个女芭蕾舞演员的父亲还是中共党史上王明集团的核心人物,而中国的芭蕾舞演员迟早要回国,在那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了。这个男芭蕾舞演员唯一能够指望的是他的爸爸,他爸爸是芭蕾舞团长,也许能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保护他们,让他们继续跳芭蕾。但是,那时还没有人能够预见后来发生的文革,没有人能够预见文革时他爸爸也会被打倒。命运本身的残酷,有时不是人能预期和人能想象的。所以,当你遇见一个理想之中的人时,你真的不知道那是福是祸。也许你会幸福,也许那只是灾难的开始。
您还想接着听吗?工作人员低头问她说。后面的您都知道了吧?
想,她点头说。虽然我很早就听过这个故事,但是里面有些情节,还是跟我听到的不一样。我听到的版本是他们先是一起好了,然后女芭蕾舞演员带男芭蕾舞演员去家里见父母,男芭蕾舞演员才知道女方家里的背景,而不是在公寓楼门口知道的。但是,你接着讲吧,我想继续听。
好,那我就接着讲,工作人员说。
那天晚上,男芭蕾舞演员顶着风沿着路边被雪覆盖了的小径向着自己的公寓走的时候,心上蒙着一层更大的风雪。现在,他终于明白了她为何在从父母家回来之后躲着他,不想让他告诉她想说的话。他也很诧异自己上楼去在她的门口对她表白,平时他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并不后悔告诉了她,因为那是他的真实想法。莫斯科的严寒,异国的孤独,对芭蕾的共同爱好,对温暖的渴望,对她的舞艺和美貌的倾慕,让他爱上了她。在出国前,单位的外事部门给他讲过外事纪律,要求他在苏联时期不要谈恋爱,但是在美丽的她面前,他感到无法用纪律约束自己。他站在她的门口的时候,隔着屋门听见屋里的轻微的走步声,甚至听到了她的喘息。他猜到了她站在门后在听他讲,猜到了她不会说什么,因为她可能是在纠结之中,无法回答他。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下楼之后,她会从楼里追出来,告诉他,她的父亲是叛国者,是王明集团的人。
他压根儿没有想到她的家庭是这样一个背景。他知道跟这样一个家庭背景的人相恋,回国后会对他的事业有什么影响。跟一个叛国者,而且是王明集团的人的女儿相恋,意味着他回国后在政治上就不会得到信任,也就不可能在芭蕾舞团担任主要角色,在芭蕾上会一事无成。更重要的是,她要是跟他回中国,那她的芭蕾事业也就结束了。中央芭蕾舞团绝不会让一个有她这样背景的人去担任任何舞剧的主角,即使她的芭蕾舞跳得世界第一也不行。要想跟她在一起,而兼顾他们的芭蕾事业,他只能留在苏联,拒绝回国。那样,他就可能被视作叛逃中国,以后可能会像她父亲一样,终生不能回到故乡。而且他的家人也会受到牵连,特别是他父亲是中央芭蕾舞团的团长,一定会被免职。他知道他不能这样做。他不能连累自己的父亲。
回到寒冷而又空寂的公寓后,他坐在发旧的沙发上,没有开灯,就在黑暗里静静地坐着,静听着窗外呼啸而过的风雪,心乱如麻。他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跟她在楼门口的接吻。他记得雪在他们四周下着,有一些落到她的头发上和肩膀上。他记得她的脸颊冰凉,嘴唇湿润而又火热。他记得跟她亲吻和拥抱的时候,他的心像是燃起了一团火,被巨大的快乐淹没。当她推开他,自己跑回楼里的时候,他感受到了那种失去她的失落。他一直站在原地,眼睛看着她的阳台的方向,直到看见她在窗户后面出现,向他挥手,才带着一股惆怅转身离开。
第二天早上,几乎一夜未眠的他早早的起来,洗了一把脸,热了一碗牛奶,在牛奶里打了一个鸡蛋。吃完早点之后,他穿上厚厚的皮大衣,戴上鹿皮帽,蹬上黑色长靴,戴上厚厚的皮手套,提着他的拐棍一样的黑色雨伞,早早地出门,去了无轨电车站。清晨的空气很冷,人们的嘴里向外冒着白色的雾气,雪虽然不大,但是依然在持续不断地飘着。他在车站避雪的棚子里站着,隔着透明的玻璃看着外面,等着女芭蕾舞演员。他知道她不会来这么早,但是他怕错过了她,就早早的来这里等着。寒风中,一辆一辆的无轨电车挟裹着风雪来了,在站牌下停住。无轨电车上下来一些乘客,又载着更多的乘客在风雪中离开了。
等了四十多分钟后,他心情有些焦虑了起来。他不知道她会不会来了。也许她晚上没睡好觉,早上不去剧场了?也许她今天早上走的早,在自己来到车站之前就走了?他胡乱地猜想着,眼睛不断地看着她可能出现的方向,心神不宁魂不守舍地在车棚子里顿着快被冻麻木了的双脚。
一个小时之后,他眼前一亮,看见她从远处的街角终于路面了。她依旧穿着那件黑色大衣,脚上依旧是那双黑色的皮靴,手上依旧是戴着棕色的皮手套,头上依旧围着灰色的厚厚的围巾。看见她的身影的那一刻,他心里悬挂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踏实起来了。
她的步伐比平时有些慢,面容疲倦,像是一晚上都没睡觉一样。她在快走到车站的时候看见了他。看见他的那一瞬,本来愁眉不展的她,脸上露出了一种惊异和欣喜。一晚上的郁闷在看到他的那一瞬间突然云消雾散了,就好象他身上带着一股魔力,能够驱走她的任何烦恼。她的心里涌起了一种莫名的快乐。虽然昨晚没有睡好觉,她的身体和大脑依然觉得很疲累,但是见到他,她的心里是快乐的,身体的疲累似乎也一下消失了。她的脚步变得轻快,人也变得精神起来了。她的心好像燃起了一把火,眼睛也变得明亮了起来,脸上绽开了一个无法隐藏笑容。
看到她带着笑容向着他走来,他心里感到了一种莫大的安慰。他一直在担心她会很烦恼,不知道见了她会怎么样。昨夜的吻和她见到他时脸上显露出来的欣喜,都让他相信,她也是在爱着他,喜欢他。他举着黑伞迎了出去,在风雪中迎着她,快步走到她身边。他把伞举到了她的头顶,遮住了天空飘下来的片片雪花。
谢谢你,她仰头看着他说。你早就在这里了吗?
刚到没多久,他微笑着说。
别骗我,她瞥了一下嘴说。知道你起得早,一定在这里等了很久了。
是等了一个小时了,他承认说。
猜着就是,她扬起头来看着他的眼睛说。我想跟你说句话。
说吧,他停住脚步说。
我们去那边的墙下好吗?她的下巴向着车站左面的一堵石墙扬了一下,问他说。不想在人多的地方说。
他举着伞,跟她来到了车站左面的那堵石砌的矮墙边。他们在石墙边站定,像是恋人一样挨得很近的站着。他等着她讲话,但是她好像在犹豫着,嘴张了一下又闭上,没有说出来。雪花无声地落在石墙上和黑伞上,也落到了她的身上。
怎么了,他催问她说。说啊。
我昨晚特别难受,她垂下眼帘说。心里特别纠结,想爱你,但是又不敢。
看见她垂下的眼睫毛,听见她说也爱他,他的内心里起了一种冲动,有一种想抱她一下吻她一下的冲动。他突然伸手把她拉过来,让她的身子靠着他。她身体挣扎了一下,但是没能挣脱开,就顺从地让身子靠着他。他把伞往下放了放,让伞遮住他们的头部,然后一只手搂着她的柔软的腰部,低下头去吻她的嘴唇。她左右扭着头,不想让他吻到嘴唇。他的嘴唇在她的脸颊上吻着,吻到了她的眼睛和鼻子,最后终于触碰到了她的嘴唇。在触碰到她的嘴唇的一刹那,她不再扭动头部,而是闭上眼睛,伸手搂住了他的脖子,跟他吻了起来。第二个吻像是昨晚第一个一样的甜蜜和温柔,同样的湿润和热烈。像是有电流在身体里通过一样,他颤抖着,也能觉出她的身子在他的怀里颤栗。他们吻了好久,直到喘不过气来了,才松开嘴唇。
我爱你,他把嘴唇凑到她的耳边说。我想你。
她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像是几乎昏厥了一样的闭着眼靠着他。听到他在耳畔说爱她想她,感受着他的炽热的呼吸,听着他的心跳,她眼里几乎要留下泪水来。她从来没有爱上过一个人,从来没有人这样贴着她的耳朵说爱她想她,现在她体会到了那种爱的晕眩,那种爱的快乐,那种巨大的让人颤栗的快感。她昨晚下定了的决心,现在又开始动摇了,想说的话又说不出来了。她在他的肩头靠着,快乐,悲伤,难过,各种情感刹那间在心里像是汹涌的洪水一样流过。她把手伸进他的脖颈后面,抚摸着他的头发,身子整个贴在他的身上,让他拥抱着自己。过了一小会儿之后,她像是诀别一样地吻了他的脸颊一下,手松开他的脖子,身子挣脱了他的怀抱,手臂垂了下来。
不行,真的不行,她低头说。这是最后一个吻了,以后再也不能这样了。
你不喜欢吗?他问她说。
喜欢,但是再这样下去,我就把持不住自己了,她说。昨晚几乎一夜没睡,到了后半夜才睡了两个小时。虽然在见到你的第一眼我就开始喜欢上了你,但是我们不能相爱。真的不能相爱。我们做个。。。朋友吧。
可是我不想跟你做朋友,他目光温柔地看着她说。我想爱你,也想要你的爱。
你要真爱我,你就得为我想想,她抬头看着他的眼睛说。我也想爱你,但是我们以后怎么办?你能留在苏联吗?
不能,他有些痛苦地摇头说。我要成是留在这里不回中国,他们就会把我当作叛国者,我爸爸和一家都会跟着倒霉。
你不能,我也不能,她低下头说。你不能留在苏联,我不能去中国。我们相爱了又能怎样呢?你迟早得回中国,到时候我也不能跟你回去。爱得越深,分手就会越痛苦,还不如现在就不要相爱。你说对吗?
他没有接她的话。他知道她说得都对。看着她坚定的面容,他知道这一定是她昨晚仔细思考的结果,知道她已经下了决心。她的眼神像是在亲手撕毁一幅无比美丽的油画,眼瞳里充满了悲伤,那种发自内心的悲伤。他看见了她的憔悴。才一晚上,她的眼圈很黑,双颊已经凹陷,像是经历了巨大的折磨。他知道她心里的难受,也知道跟她相爱的唯一的办法是留在苏联,不回中国。但是他不能。他没有权利因为自己的爱给在北京的父亲和家里带来灾难。
他沮丧地看着脚下,把一堆雪踢到一边去。一辆无轨电车从远处的街角驶来,响着铃声开始进站了,站牌下等车的人们开始向着电车口蜂拥而去。雪在散漫地下着,给街道罩上了一层美丽而朦胧的面纱,让眼前的这一切都像是一场电影,一场梦,而不像是生活里的场景。
那边车来了,我们上车去吧,她的脸上呈现出一种无奈的微笑说。以后不要在车站等我了。
他们几乎是最后上车的,车上已经没有了座位。他们并排站在车中间,拉着中间竖立的铁管扶手。雪在车外下着,他们在车的摇晃中穿过市区。在红场一站,很多人下车去了,他们等到了一个空座。他让她坐下,自己在她的身边站着。不远处还有另外一个空座,她让他过去坐,他说不去,他宁愿站在她身边。她没有再说什么,眼睛一直凝视着被雪覆盖的冰冷的城市。
在剧场广场站,他们下了车。他们一起走过站前堆满了雪的喷水池,迈上台阶。他依旧扶着她上台阶,直到走到剧院大门才松开她的胳膊。走进厚重的剧场大门,他们在宽敞的前厅分开,她对他微笑了一下,说一会儿见,就沿着弧形的走廊去了后面她的化妆间。她走进化妆间,脱下黑大衣和靴子,解开围巾,换上一双练习用的舞鞋,在梳妆台前坐了下来。她看着镜子里的憔悴的面容,终于忍不住地趴在桌子上哭了。这是她第一次在心里真正爱上一个人。然而,她却不得不放弃了。
此后的两个月里,他们像是同事一样的相处。在剧场里,他们都尽量表现得很正常。他把对她的爱埋藏在了心里,不再对她提起。她也把自己的爱埋了起来,像是同事一样的对待他。她是一个很用功的芭蕾舞演员,每天早上七点就到了剧院的练功房,是芭蕾舞团里来到练功房最早的一个。虽然已经是剧团里担纲的舞剧主角,但是她从来没有主角的架子,而是总是跟其他芭蕾舞演员一样地参加训练,一丝不苟地做各种动作,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同一个动作。他比更用功,比她到大剧院更早,每天她到的时候,他已经在里面了。他认真地请教着,学习着,练习着。她手把手的教他,把自己对芭蕾的感悟都告诉他。
他的芭蕾舞技进步很快,在她的帮助和指导下,短短的两个月,他突飞猛进,已经完全不是刚来时的那个芭蕾舞演员了。剧团的团长很高兴地表扬他进步快,决定把《卡门》里的男军官唐何塞的B角交给他。在演出时,如果A角不能演出,就由他出演。他从此更加努力了。唐何塞和卡门有几段双人舞,他和她一起练习着,对每一个动作都跟认真,绝不放过一点纰漏。
他的俄文也进步很快。在她的帮助下,他从一开始的讲话磕磕巴巴,到能够流利的用俄文进行交谈。现在,无论剧团里有什么活动,只要她去参加,他也都跟着去参加。他除了热爱芭蕾,对艺术孜孜以求,力求完美之外,也喜欢俄罗斯文学,喜欢普希金的诗,托尔斯泰的小说和列宾的油画。莫斯科大剧院有一个内部电影资料室,他们可以在那里观摩芭蕾演出的电影。他们在那里一起观看《红舞鞋》那部电影。当看到电影中的芭蕾舞团团长莱蒙托夫询问女演员佩吉为何要跳芭蕾的时候,他们看见佩吉反问说,你为什么要活着?他们相视一眼,带着悲哀的笑了,因为他们都看见了对方眼里的回答。他们都是为了芭蕾而活着的人。他们只能放弃自己的爱。
然而,他们越是想禁锢自己的爱,越是想压抑他们的爱,他们内心的爱情燃烧得越是炽热。在一个下雪的夜晚,他们一起去参加了一个莫斯科文学爱好者自发组织的诗歌朗诵会。他在会上朗诵了一首普希金的诗:“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有如昙花一现的幻想/有如纯洁之美的天仙/在那无望的忧愁的折磨中/在那喧闹的浮华生活的困扰中/我的耳边长久地响著你温柔的声音/我还在睡梦中见到你可爱的倩影。。。”她听着他的略带嘶哑的嗓音,看着他原本英俊现在却变得憔悴了的面容,心里涌上一阵巨大的悲伤。在一起回公寓的摇晃着的电车上,他们站在一起。他想伸开胳膊,把她抱在怀里。他想再吻她一下,想跟她说,我爱你,我们继续相爱吧。但是他没有。他不得不用理智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此后的日子,他训练时经常心神不宁,她的舞蹈也频频出错。剧团的人用异样的眼光观察着他们,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每天练习结束的时候,她不再等着他一起离开剧场坐电车回公寓,而是自己走了。他也是自己坐电车回公寓,每天都觉得寓所冷清清,空荡荡的。他没有心情做饭和吃饭,发现自己完全丧失了食欲,什么都不想吃,也不想做。他开始失眠,整晚整晚的睡不好觉,在半夜里总是想起她来。从不抽烟喝酒的他,买了烈性伏特加酒回来,喝的烂醉,好让自己忘掉她。他开始抽烟,黑暗里坐在沙发上一只一只的抽,抽得屋子里全是烟雾。他除了去剧场之外,其余时间都是在公寓里待着,既不想去参观莫斯科的各种名胜古迹和看风景,也不想出门。孤寂,忧伤,郁闷,心疼,这些感情轮番地不断地吞噬着他,让他夜晚再也无法平静地入眠。一躺在床上,他的脑海里就全是她。他突然瘦了,瘦了很多,他觉得自己变得很空洞,好像以后再也无法爱上另外一个女人了。
在剧院里,她看到了他一天天在瘦下去,也觉得很心疼。她看出他把自己禁锢在绝望的情绪里,在一天天的毁灭下去。她不知道能为他做些什么。她不敢再接近他,怕他无法坚持下去。她尽量躲着他。她也忍着同样的痛苦,每天跟他一起练功,只有在回到她自己的寓所了,躲进黑暗里,才会悄悄地哭泣。周末回到莫斯科郊外父母家的时候,她的父母看了出来,知道她爱上了他,却又不能相爱。他们尽量安慰她,给她做爱吃的饭,讲一些愉快的事情。但是无论他们怎么说,怎么做,却依然无法解除她心中的痛苦和烦恼。他们心焦如焚,知道只有一个人能把她从这种痛苦和烦恼中解脱出来,那就是他。但是她不能跟他在一起。他们只能希望随着时间的过去,她会渐渐平静下来。再过一段时间,剧团排练的《卡门》就该正式上演了,那时他也就学完了,该回国了。等他走了之后,她会再也见不到他了。也许那时她会恢复过来,忘却他,重新爱上一个人。但是从目前的状况看来,她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已经无法上台出演卡门了。
文学城链接:
给我一条波斯米亚红裙(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