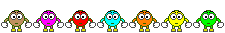- 注册
- 2014-04-06
- 消息
- 8,608
- 荣誉分数
- 16,518
- 声望点数
- 1,323
开始的两段让人震撼,第一段描写她的舞蹈,“黑红色火焰一样燃烧的长裙,森林里的鬼精灵一样跳跃的红舞鞋,魔鬼旋风一样的舞步......她的舞蹈如激弦,如幽曲,热烈之中带着一股无名的忧伤和缠绵。” 第二段紧接着写他二十年后的回望,惆怅,痛楚为悲剧埋下了伏笔,让欢快美好中有了感伤和忧郁。三
第一次见面,女芭蕾舞演员和她身上穿的那条波斯米亚吊带红裙就给男芭蕾舞演员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黑红色火焰一样燃烧的长裙,森林里的鬼精灵一样跳跃的红舞鞋,魔鬼旋风一样的舞步,年轻美丽光彩照人的容颜,栗色的头发,吊着红裙吊带的裸露着的光滑的肩膀,被红裙勒住的突出的胸部和细小的腰身,像是艺术家雕刻出来一样的胳膊,手腕,大腿和小腿。在舞台明亮灯光的照射下,她恣意地舞着,左手提着长裙的一角,头向后微扬,嘴角抿着,从舞台一头跳到另一头。她的步态轻盈,身躯矫健,弹跳力极好,舞蹈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灵气和让人震撼的美丽,既活泼又热烈。在节奏感很强的音乐下,她翩翩起舞,像是忘记了一切,变成了一个神采飞扬,自由不羁,野性未脱的吉普赛女郎,在舞台上炫影飞扬,带着让人无法抗拒的迷人的活力。舞台的灯光强烈地打在她的脸上,他能看见她的长长的忽闪的睫毛,眯着的细长眼睛里带着一股如水的柔情。她的舞蹈如激弦,如幽曲,热烈之中带着一股无名的忧伤和缠绵。
这一场景一直刻在男芭蕾舞演员的脑海之中,让他终生无法忘怀。二十年以后,早已告别舞台生涯他在中央芭蕾舞团四楼的小剧场门口又看到了这一幕,看到了这条黑红色波斯米亚长裙,看到了一个年轻姑娘穿着这条长裙在台上跳着同样的舞蹈,身形和舞姿宛若当年的她再现于舞台。那一瞬间,他五雷轰顶,恍若隔世,仿佛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又来到了多年前的莫斯科大剧院,站在门口,目瞪口呆地看着年轻的她跳着热烈而感伤的芭蕾。
那年冬天的莫斯科几乎总是阴云密布,大雪纷飞,雪像是下不完了一样,隔三差五地下着。即使是在寒冷中住习惯了的莫斯科人,也说那年冬天寒冷异常。天空总是有大块大块的厚重的云朵堆积在一起,像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在一刹那凝固住,把海浪,乱石堆和礁石挤在一处。肆虐的寒风夹带着指甲盖大的雪花,从白茫茫的被厚厚的冰封住的莫斯科河面呼啸而来,穿过河边银装素裹的树从,扑进莫斯科市中心的剧院广场,撞击到大剧院前巍峨的的圆柱上。
又是一个风雪的日子。夜深了,莫斯科大剧院前的广场上早已经空无一人,四周的建筑都已经熄了灯,诺大的广场只剩下大剧院的窗户里射出微弱的黄光,在风雪中显得孤单冷清,只有几盏路灯发出青色的光线,照在剧院门前的欧式喷水池和四周的积雪上。夜色像是一湖平静的水,把广场淹没。剧院四周的鳞次节比的建筑退到黑暗之中,屋舍变成了一个颜色,与光秃的树枝混在一起。从剧院门口看去,广场一片静寂,只有乱纷纷的雪花在灯下飞舞。
一辆电车摇晃着在剧场旁边的汽车站牌下停下,打破了广场的宁静。生锈的车门带着粗粝的嘎吱声打开,女芭蕾舞演员扶着把手从电车上迈步下来。她穿着一双黑色的长靴和黑色大衣,戴着棕色的皮手套,一条灰色的厚厚的围巾把头和脸颊围住。她把手插进兜里,大衣的纽扣一直扣到了脖颈。密集的雪花穿过光秃的树枝,在她的头上散落了下来,她紧走几步,迈上了通向大剧院门口的被雪覆盖的台阶。电车在她的身后哐当哐当的远去了,车灯在昏暗的夜里亮着雪白的光,在无人的街道上照射着肆意飞舞的雪花。
她在大剧院门口跺着脚,把靴子上的泥雪跺掉,推开大剧院厚重的大门,走了进去。剧院里的灯一多半都已经关了,只留下几盏照明灯照着前厅和走廊。她穿过空旷的前厅,沿着半圆形的走廊快步走到后台,走进了一个右手的一个化妆间。白天她把手包放在自己的化妆台上,走时忘记带走了。她推开化妆间的门,在堆满了化妆品的镜子前找到了自己的手包,舒了一口气。一晚上,她都在担心手包会丢了,因为以前就发生过把东西遗忘在化妆间丢了的事儿。她怀疑是单位的清洁工干的,但是从来没有证据。她把手包挎在肩上,走出化妆间,沿着半圆形的走廊向着门口走去,耳朵里突然听到了一阵熟悉的《卡门》舞曲声。声音微弱,像是从二楼传来。她转身踏上楼梯,扶着木质扶手走到二楼,听见乐曲声是从二楼右侧的一个亮着灯的练功房传出来的。已经都夜里十一点了,谁还在练功?她好奇地循着乐声走到练功房前,拉开练功房漆成蓝色的大门,探头向里面看去。她看见男芭蕾舞演员正把一条沾满了汗水的毛巾搭在脖子上,右腿放在镜子前的把杆上,一边压腿一边用毛巾的下摆擦着脸上的汗。他似乎听到门口的响动,扭头向着门口的方向看来,正看见了她往里探头。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这里练功啊?她好奇地问。
有几个动作老做不好,他不好意思地把腿从把杆上放下来说。我想把动作做好了再回去睡觉。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晚上去一个朋友的生日派对,突然想起手包忘在化妆间了,她举起手里提着的手包说。怕丢了,正好坐车从这里路过,就赶紧上来拿一下,幸好没丢。哎,对了,团长昨天夸奖你了,说你自从来到剧院之后,进步很快。
团长也直接告诉我了,他谦逊地笑了笑说。但是我知道自己的水平比起这里的芭蕾舞演员来说还有不少距离,只好自己增加时间多多练习。
你刚才说有几个动作拿不准,要不要我来帮你看看?
有一段单人舞,里面的几个动作我总觉得不对,他点头说。你要是能帮我看看最好了。
她在门口把靴子脱了,穿着袜子走进练功房来。他站在镜子前,把一晚上一直在练习的一段舞蹈表演给她看。
等等,她看到一半的时候说。你这个旋转动作做得不对。
她把手包放在一边,把大衣扣解开,脱掉大衣。她穿着一件淡黄色的毛衣,站在他前面,踮起脚尖,给他做了一个示范。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组合动作,要一气呵成,她边示范边说。你的问题是胳膊和腿有一点儿不协调,胳膊的动作比腿的动作快了半拍,转身和跳跃的时候,在衔接的地方也有些生硬。这套动作应该是给人感觉很舒缓的,腿转的时候应该保持这个角度,胳膊要这个弧度,然后很自然地打开,让整体动作和谐起来。每个单独的动作你做得都是不错的,只是连起来的时候变换有点儿生硬,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多练习,所有的动作都熟悉了就好了。
他按照她的示范做了几遍,果然动作好多了。他继续练习,她在旁边看着他,时不时的帮他纠正着动作。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已经过去了,已经快午夜了。他看了一眼墙上的表,停了下来。
真不好意思,他抱歉说。这么晚了,你还在这里教我,太耽误你时间了。
没事儿的,她笑笑说。我喜欢当老师,从来都不觉得烦。
这么晚了,不跳了,我们一起回去吧,他用毛巾擦了一把汗说。
好啊,她弯腰把放在地上的手包重新挎到胳膊上说。这个钟点儿我还真有点儿担心自己坐电车呢。你去换衣服,我在门口等你。
他把练功房的灯关了,去更衣室擦干了汗,脱下了练功服,换上了衬衣和裤子,穿上了厚厚的皮大衣,戴上了鹿皮帽和皮手套,套上了皮靴。十分钟之后,他来到了门口,看见她穿好了黑大衣,系好了厚厚的围巾,也穿上了皮靴,正站在门口等着他。他们一起走出剧场大门,反身把大门关好。下台阶的时候,冰冻的台阶有些滑,他一手拄着他一直带在身边的黑伞,一手扶着她的胳膊,跟她一起走下了台阶。他在台阶下把黑伞打开,让黑伞遮住夜幕里飘落的雪花。他跟她一起沿着覆盖着一层厚雪的石子路向着车站方向走去。
你知道,这里没人在雪天打伞,她侧过头来说。一看你就不是莫斯科人。
本来就不是,想冒充也冒充不了,我这面貌和口音,一说话就让人听出来了,他说。
喜欢莫斯科吗?她问他说。
喜欢,非常喜欢,他点头说。莫斯科一直是一个我很向往的地方,这里有这么多的名胜古迹,红场,克里姆林宫,列宁墓,大教堂,历史博物馆,美术馆,还有莫斯科大学,都很吸引人。当然最吸引人的是莫斯科大剧院。我觉得能到这里来学芭蕾,很有运气,也很值得。一直就很向往这个城市,现在终于来到这里,心情还是很激动的。
他们并肩沿着剧院广场被雪覆盖的石子路走着,在寂静里走过挂着冰凌的墙壁,走过蹲在雪中的喷水池,走过广场上的一盏盏发黄发青的路灯。灯光把他们的长长的身影印在留着两串脚印的光滑平整的雪地上。四周寂静如石,灯光下有点儿发蓝的雪花无声地在他们的周围坠落,厚厚的雪把电灯杆,高压线,路边的草地和白杨树,草地四周的石凳和铁栅栏,车站牌以及四周的建筑都挂上一层松软的厚厚的雪,冻成了一个白雪宫殿。她很自然地用手挽着他的胳膊,一边走一边随意地聊着。
你知道这座大剧场曾经三次被烧毁,又三次被重建吗?她问他说。
不知道啊,他惊奇地说。真了不起,一定是每次重建都比以前更辉煌。特别钦佩你们国家的文艺,像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托尔斯泰的小说,普希金的诗歌 --- 我在中国读过很多你们国家的文艺作品,来之前还读了《静静的顿河》,非常喜欢。有个问题我一直没搞懂,你们的歌曲,比如说《卡秋莎》,《三套车》,都应该是很欢快的歌,但是为什么听起来都让人感觉很忧伤呢?
可能是因为我们牺牲了许多吧,她想了一下说。战争里死了很多人,好多家庭都有人在战争里伤亡。我有一个舅舅在卫国战争的时候为了保卫莫斯科牺牲了,在一个工厂里战死了,那个工厂被德军的飞机大炮夷为平地,最后尸体都没有找到。经历很多痛苦和磨难的人创作的东西,总是免不了带着忧伤吧。
不知不觉中,他们已经来到了电车站,走进站牌下避风的棚子里。他把黑伞收了起来,让黑伞重新变成了一根手杖。她跺着脚,把靴子上的雪泥甩掉,手拍打着头巾上和黑大衣上的雪。
看你天天晚上都在剧院里练习芭蕾,有没有抽空去出去转转,看看莫斯科的风景?她问他说。
还没有来得及,他摇头说。这个星期想去红场,列宁墓和克里姆林宫看看,下个星期去看看莫斯科大学和历史博物馆。
这个周末我带你去看吧,她看着他说。我也正好想去看看,好久没去了。
那太好了,他点头说。我俄文不好,交通不熟,对这些地方的背景也不太了解,要是你能带我去最好了。不过,你方便吗?
一般我周末都回我父母家,他们住在郊区,她说。但是这个星期六,我上午要去少年宫给一些喜欢芭蕾的孩子们讲讲芭蕾,下午和晚上都没事儿,我们可以一起去。你住的公寓离我的不远,星期六下午两点你到我公寓来找我吧 --- 下车后我带你去认认我公寓的门 --- 我带你去市区转转去。入冬之后都懒得出门了,正好一起去看看,希望那天晴天才好。
他们一边等车,一边在电车站随意地聊着。她告诉他说,虽然她出生在莫斯科,但是父亲是中国最早去苏联留学的,娶了一个莫斯科姑娘,自从她出生后就一直在莫斯科工作,再也没有回中国过。她的中文流利,是因为父亲在家里一直用中文交谈,而且从小送她去莫斯科的中国家庭组织的中文学校的缘故。父亲对她的中文要求很严,经常坐下来,陪着她认中国字,写中文,给她用中文讲故事,读历史书和文学书,让她了解中国文化。
电车迟迟不来,他们在车站交谈了很多。他们发现双方对芭蕾的热爱极其相似。她把芭蕾当作生命一样热爱,他也是,甚至认为芭蕾比生命还要重要。他说第一次远离故乡,生活在异国他乡,觉得不太习惯,而且比起北京来,莫斯科要寒冷得多。她说很能理解一个人来到异国他乡的感觉,没有家人没有朋友的孤单,更何况他俄文也不太好,也会造成一些不便。她说可以帮着他练习俄文,可以带他去比较便宜的商店买东西,生活上有什么需要的,也可以尽量帮着他。
他们的公寓相隔不远,在同一站下车。他们一起走回公寓。她带他去看了她住的公寓楼,告诉了他房间号。分手的时候,他们已经觉得互相很了解,像是老朋友一样了。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他就对她一见钟情。现在,他更喜欢她了。
浏览附件505887
星期六是男芭蕾舞演员来到莫斯科后看见的第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往日阴郁的天空一扫阴霾,变得晴朗,天空上只飘着几小片云朵,火红的太阳暖暖地挂在澄净的蓝天上。下午两点,按照他们的约定,他去了她的公寓楼,到了她房间的门口敲门。她早已经准备好了,依旧穿着她的黑色大衣,黑色的皮靴,灰色的厚厚的围巾,挎着她的手包。她跟着他一起下楼,出门坐车去了红场。
他们在红场下车,看到广场上有很多人。因为天气好,这天广场上的游人特别多,很多游人在雪中摆好姿势拍照。他们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到西侧,来到了列宁墓边。列宁墓前的墙边栽种着一排松树,松树上堆着雪,墓门前的甬道上排着一条长长的队伍。队伍里主要是各地来的苏联人,中间也夹杂着一些外国人的面孔,其中也有一些中国人。墓地由磨光了的红色花岗石和黑色大理石构成,结构庄严肃穆。墓地的甬道边站着一个大学生样子的年轻男人,在阳光下拉着小提琴。
沿着灰色石碑构成的甬道排了半个小时的队后,他们终于通过墓口的窄门,走进了墓内的悼念大厅。大厅的墙壁上雕刻着苏联国徽和国旗,四周镶着红砖。他们沿着一级级光线昏暗的墓道向下走,走到了安置水晶棺的墓室中央。墓室的墙壁上没有安置灯,只有水晶棺内透出几缕柔和的光线,像是静夜里书桌上的台灯散发出的黄光。灯光照在平躺在棺内的列宁的脸上和身上,好像是照着一个刚刚入眠的安详的老人。她告诉他说,列宁生前想葬在自己母亲的墓地旁,但是斯大林不想让这样的一个革命领袖葬在一个普通的墓地上,所以盖了这么一个列宁墓,让所有人都可以来瞻仰列宁的遗体。
从列宁墓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开始落山了。他们走到克里姆林宫正门,沿着克里姆林宫的红墙在夕阳余辉下散步。克里姆林宫的围墙很长,红墙的顶上堆着一层厚厚的白雪,五个高高的塔楼耸立成一排,最高的塔楼上悬挂着一个罗马数字的大钟,塔楼的尖顶上竖立着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宫墙外是高大的干枯了的墨绿色的枞树,树枝上堆满了积雪。几株雪松立在一处红墙拐角处,松枝上堆着厚厚的雪,几乎要把松枝压弯。
他们一边沿着红墙散步,一边像是老朋友一样说话,聊起芭蕾,聊起艺术,聊起俄罗斯文学。她给他讲了莫斯科大剧院的历史,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建立大剧院开始,到三次被火焚毁,到经历十月革命和二次大战,历经沧桑而更加辉煌。她也给他讲了芭蕾舞团的辉煌的历史,讲述剧团排练的《天鹅湖》,《睡美人》,《吉赛尔》,《胡桃夹子》,《灰姑娘》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传统剧目,以及新编的《青铜骑士》,《红罂粟花》,《宝石花的传说》和《英雄诗篇》等。
他们走过克里姆林宫的侧门,看见侧门门口有两个黄色的岗哨亭,里面站着执勤的士兵。士兵穿着深绿色的双排扣军服大衣,银灰色的领子又宽又厚,像是两个菱形块在脖子下分开。大衣的双排纽扣是银白色的,在深绿色的军大衣上特别显眼,中间系着一条厚厚的深棕色皮带。士兵头上的厚厚的皮军帽也是银灰色的,帽子正中镶着一个红色的徽章。士兵带着一双白色的手套,左臂上戴着一个红色的徽章,腿上是黑色的军裤和黑色的军靴。士兵的左手笔直地贴在左腿上,右手四指靠拢,圈住一杆上着闪亮的刺刀的栗色步枪。他看见有三个士兵并排从侧门内威风地走出来,一个像是军官的样子,戴着白手套的手扶着腰间的长长的军刀,大衣的下摆在风中抖动着。
沿着克里姆林宫,他们走到了覆盖着冰雪的莫斯科河。走到河边的时候,路灯亮了,朦胧而温柔的夜色悄悄地随着灯光倾泻了下来。站在河边,他们都不太想回去。她挽着他的胳膊在河边走了一圈,直到夜色完全笼罩了城市,他们才依依不舍地上车回去。
在她的公寓门口,她邀请他一起上楼去她的房间吃晚饭。她烧了一锅牛肉,做了一个蔬菜沙拉和红菜汤,他炒了一个中式素炒土豆丝。他们继续一边吃一边聊。他给她讲在北京的生活,讲中央芭蕾舞团的成立,讲他们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排练《天鹅湖》。她给他讲莫斯科的生活和逸闻趣事,讲俄国的历史。他们都很喜欢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她屋里有一个唱机,于是吃完饭之后,她放上了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一起坐在沙发上倾听美妙的乐曲。她给他煮了黑咖啡。他说他不习惯咖啡的苦味儿。她给他的瓷杯子里夹了好几块白色的方糖。他跟她并排坐在沙发上,胳膊和腿有时会无意中触碰到一起,每一次都让他的心跳加快。他们沉浸在柴可夫斯基的缠绵悱恻的音乐之中:《天鹅湖》,《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忧伤小夜曲》,每一首都让他们感动。他闻着咖啡的扑鼻的香气,也能够闻到她身上和头发上散发出来的芳香。
听完音乐,已经快晚上十点了,他从她的住处告辞出来,沿着路边的人行道踩着积雪向着自己的寓所方向走去,心中充满了快乐。他们的寓所很近,只隔着几条街。月光从楼房和屋舍的空隙之中照过来,把建筑物,树丛和砖墙的一半隐藏在黑暗之中。黑蓝的夜幕里闪耀着迷人的黄色,四周的楼房和屋舍的窗口闪着红色的光,柏油马路上的雪反射着路灯的光线,把青白的微光投射在半空中。冬夜的空气既清新又潮湿,漂浮着黄色,青色和红色混杂在一起的光粒子。
他在黑暗和光亮之间穿行,心情愉快,脚步也轻快了很多。他忍不住哼起了早就学会的一首苏联歌:“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树叶也不再沙沙响/夜色多么好/令人心神往,多么幽静的晚上。。。/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默默看着我不作声/我想对你讲/但又难为情,多少话儿留在心上。”
这是他到了莫斯科以来最快乐的一天。他喜欢跟她在一起的每一分钟。无论是一起走路,坐车,参观,散步,吃饭,还是聊天,每一秒钟他都觉得很愉快。她不光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内心也温柔,直爽,真诚,可爱。想起以后每天还能在大剧场见到她,他就觉得更快乐了。
第一次,他觉得莫斯科没有那么孤寂和寒冷了。过去他每天回到潮湿的公寓后,看着阴沉的天气和落在窗户上的大片的雪花,心里总会涌起一阵孤寂的感觉。过去虽然他睡觉时裹紧被子,却好像依然无法抵御日渐寒冷的冬夜带来的孤寂。那种异乡的孤独感随着呼啸的寒风在半夜侵入,渗入骨髓。今天,他回到寓所,站在窗户前,出神地盯着窗户上冻出的冰凌,依然在回想着和她在一起的时刻。他心神恍惚地用手指在窗户的冰霜上一遍又一遍地写着她的名字,心里涌起了一种甜蜜,随后又感到了一种失落和惆怅。
半夜时分,他从梦中醒来,看着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一缕月光的微光照在靠着窗口的书桌上,又想起了她:她的舞姿,她说话的声音,她的蓝色的眸子,她的眼神,她的长睫毛,她微笑的样子,她纠正他动作的时候的身体接触,她比他略高的体温和光滑的肌肤,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女人的温热的气味儿,她挽着他手臂走路的样子。漆黑的房间里,书柜,暖气铁皮,书桌,靠在墙角的旅行箱,全都变成了一种颜色,只有不同形状的模糊的轮廓在黑暗中浮现出来。窗外一片寂静,间或有一阵的轻微的风声拂过玻璃窗。偶尔远处有汽车在街上驶过,车轮碾雪的声音不久就消失了。他睡一会儿,醒一会儿,想她一会儿,对她的思念像是雪雾中的飞鸟,不断消失又不断出现。他感觉额头像是发烧一样的灼热和昏沉。
他知道,他爱上她了。他爱上了她,在这个陌生而寒冷的城市里。他只是不知道,她是否也喜欢他,是否也在这样的黑夜里,睁开眼看着窗外投射进来的微光,想起他。
文学城链接:
给我一条波斯米亚红裙(三)
这一篇的景物描写一如既往的出彩,(帮助爱看评论的同学回顾一下
她的舞蹈如激弦,如幽曲,热烈之中带着一股无名的忧伤和缠绵。
天空总是有大块大块的厚重的云朵堆积在一起,像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在一刹那凝固住,把海浪,乱石堆和礁石挤在一处。肆虐的寒风夹带着指甲盖大的雪花,从白茫茫的被厚厚的冰封住的莫斯科河面呼啸而来,穿过河边银装素裹的树从,扑进莫斯科市中心的剧院广场,撞击到大剧院前巍峨的的圆柱上。
夜色像是一湖平静的水,把广场淹没。
四周寂静如石,灯光下有点儿发蓝的雪花无声地在他们的周围坠落....
经历很多痛苦和磨难的人创作的东西,总是免不了带着忧伤吧。
走到河边的时候,路灯亮了,朦胧而温柔的夜色悄悄地随着灯光倾泻了下来。
他睡一会儿,醒一会儿,想她一会儿,对她的思念像是雪雾中的飞鸟,不断消失又不断出现。
.........
有一个小质疑,一对互怀情愫的男女第一次出游,本来很轻松很美好,有那么多的景点不写,拥抱偏偏写了一个列宁墓地,挺煞风景的,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是为了和后面的情节做呼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