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使用一款已经过时的浏览器!部分功能不能正常使用。
请尝试升级或使用 其他浏览器。
请尝试升级或使用 其他浏览器。
精华 杜杜《玫红色的艾玛》《大路朝天》《一叶书签》等书籍出版信息及内容分享
- 主题发起人 青草地
- 开始时间
- 注册
- 2014-04-15
- 消息
- 6,048
- 荣誉分数
- 11,373
- 声望点数
- 1,323
我觉得啊,写作,创作是孤独的一件事。有时候必须准备好,世界上没有人理解和应和。 写出自己真正想要的,才能出好作品。 我一开始很在意有没有人注意自己,尤其是一开始在新浪博客中。 现在不太在意了,做回自己最重要。前几天去文学城看到渥太华玩音乐的几个前辈都在那里,就想,为啥渥太华自己的论坛反而这么冷清呢?
看看时空和缺口两位大牛在这里贴歌的应和,我就明白了。本地缺乏应和呀。
难道他们的歌不好?我看不是。他们的歌在文学城都是巨受欢迎的。渥太华原创音乐在文学城可以说是半壁江山了,为啥本地论坛反而经常是乏人喝彩?
对音乐我几乎是不通的,所有也不大关注。 他们去文学城是因为那里有更多的互动,更多的交流吧?
- 注册
- 2004-03-10
- 消息
- 1,422
- 荣誉分数
- 1,083
- 声望点数
- 323
我这本新书《玫红色的艾玛》短篇小说集收录了我的50余篇短篇小说。时间跨度较大。书的题目用了其中一篇小说的题目,这篇小说,我现在贴一下:
玫红色的埃玛
杜杜
“善欣,你能过来吗?”电话里埃玛的声音含混不清。
“哦,怎么?”周日,我通常不工作。
“我想请你过来帮我弄弄指甲。眉毛,对了,我的眉毛,已经没有什么眉毛了。”埃玛的嘴里长着的似乎不是舌头,而是一个圆球,我很努力才听得清八成。上次是杰克逊开车送她来我店里美容的,当时她脸色虽然略显苍白,但口齿清晰,精神愉悦。现在除了声音含混不清,意思也混沌,难道?
“好,我过20分钟就到。一会儿见!”我和家人打了招呼,就翻出外出工具箱,把美容工具整齐装箱。
开门的是杰克逊,他脸上松弛的皱纹对称地画着十几个括号,蓝眼睛一如既往地含着笑,一层灰暗淡淡地罩着。“护士在给她量血压,我带你进去。”说着,他接过我的大衣,缓慢地挂进壁橱。
阳光从宽敞的落地玻璃窗放肆地涌进来,起居室里被一片耀眼的光明吞没,一切都白得刺眼,阳光所及之处就有了一种出人意料的圣洁之感。我眯着眼睛定了定神,光雾之中,看见长沙发上埃玛半躺着,护士坐在她身边拿着本子写着什么。见我进来,埃玛伸手示意,让我坐在对面沙发上,对护士嘟囔说:“这是善欣,我好朋友,来给我修修指甲。”
护士点头微笑,又低头在本子上做记录。
“药吃过了?”护士问,一边把侧血压和脉搏的小夹子夹在埃玛指头上,笑呵呵地看着手里的机器屏幕说:“挺好,都正常。”说罢,就给埃玛听心脏。
护士检查完毕,起身冲埃玛说:“你真是个幸运的女孩儿!指甲可以在家里修,多好!”说完冲我笑着告别,又轻声对杰克逊约定了明天来访的时间。
杰克逊送走护士,埃玛已经歪歪斜斜地坐起身来,嘟嘟囔囔说:“善欣,到那天,你能来给我修指甲吗?也许还应该给我化化妆。”
“我不是在这里了?就是来帮你修指甲的。化妆?你想化妆?”和埃玛认识十几年了,她从来没有要求过化妆的美容服务。
她似乎没有听到我的话,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杰克逊把一个平衡车推到她面前,她推着车子慢慢往厨房走。我克制着震惊的心情,静静地看着她每一步艰难的行走。六周,离上次见面仅仅六周,那个行走如常的人,怎么会突然衰老到这个程度?
她缓慢地走进厨房,问杰克逊:“茶包在哪里?我得给善欣泡茶,她最爱喝那个南瓜味儿的植物香茶了。”
我和杰克逊都迅速起身,我忙不迭地说我在家刚喝了很多茶,现在不想喝茶。杰克逊一反平时温吞缓慢的习惯,已经快步走进厨房,说:“你指挥,我来泡茶。你去和善欣说话。”
“埃玛,我们来修指甲吧。”我走过去伸手想扶她走回来,中途又缩回手来,她推车能走就让她自己走吧。当年那个情景,瞬息浮现在眼前。
那时我在Spa工作,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做完头发从店里离开,要下好几个高台阶,我热心地替她推开门并伸出手去搀扶,竟意外地遭到拒绝,她尖锐地说:“不!不用!”刚出国不久的我雾水一头,这种尊老爱幼的行为是我们民族一贯遵从的美德,怎么会受到这位西方老人如此强烈的抵抗和不满?我百思不得其解。当时间的流水渐渐冲刷去心头的疑惑,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点点滴滴流淌在生活里,我才学会用另一种眼光看待曾经习惯了的事物。我没有经老人同意去搀扶她,无意中侵犯了老人的独立自主,藐视了她行走的能力,如同在对她宣布“你老了,需要帮助!”,我的善意侵犯的是她高贵的自尊。
埃玛一步步往回走,她身材矮小,我走在她身边,正好直视她头顶。只见一小块一小块裸露的头皮穿插在本来就稀少的灰白发丝之间,如同一张世界地图,陆地和海洋星罗棋布。这是放疗的结果,放射线照过的地方就不再生长头发。
埃玛坐下,我翻出修甲工具开始忙活,和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儿。
“一直坚持不做化疗?放疗呢,还在做?”我问。
“都不做了,我累了,这样挺好。”
“护士每天都来?”
“可不!有个医生也来,我哪儿都不用去,呵呵,好方便!感谢上帝!”埃玛这句话是分段说出来的,嘴里那个无形的圆球不是咯着舌头就是撞了牙。她脸上毫无血色,眼窝深陷,眉毛果然如她所说,几乎没有了一样,灰白稀少,和苍白的皮肤连成一片,额前几根发丝软绵绵耷拉着,嘴唇萎缩得只剩下两根线。
一种奇怪的不安让我浑身不适,我抓起她的手时,浑身过电似的打了一个冷战。这无骨般柔软而温热的手,被我抓了十几年了,可此刻它让我清楚地感觉到,那件重大的事情,近在眼前。
心中难过,我不敢再抬头看她。克制着颤抖,我认真对待这双手上的每一寸皮肤,指甲的每一个角落,像捧着一个罕见的珍宝,一不小心,它就会从我手中滑落、破碎。
八年前,一辈子从未吸过烟的埃玛被诊断为肺癌,肺子切除了一个,化疗放疗折腾过去,竟渐渐好了过来。八年来,她每周三次去商场大厅参加老人步行俱乐部,每周两次在小区图书馆做义工,每周一次接孙儿孙女来家团聚,一个月做一次头发修一次指甲。岁月平安逝去,癌症销声匿迹,没有在这八年之间再来骚扰她。
埃玛举行家庭茶点聚会,一定会邀请我这个年轻朋友。她自制的巧克力,形状各异,口味新颖。来找我修甲,她常常会带一包巧克力送给我孩子吃。巧克力用透明塑料纸和丝带精心包装,有小猫小狗小乌龟各种形状,味道也多变,草莓味儿、牛奶味儿、黑白巧克力双味儿的。孩子一见这些巧克力,就欢天喜地:“妈妈,你又见到埃玛了?耶!”
半年前,埃玛向我宣布了新闻,她剩下的那个肺子上发现沙状颗粒,她仍谈笑风生:“善欣,不管是不是癌,我都不想化疗了,八年前那个罪受够了,生不如死。”
上次来见我,她告诉我脑袋里刚发现了肿块,她当时精神抖擞地夸口说:”定位放疗照射,肿瘤会局部萎缩,现代医学科技日新月异,真了不得!治疗的痛苦越来越小。放心,我可以再活八年呢。”
她的手被我细致地把玩修剪,埃玛一直在含含糊糊说着话。我只猜得出一半,是在聊她三个孙孩儿,说着说着,埃玛的眼睛就红了,我抬头向杰克逊投去求助的目光,杰克逊就笑着翻译道:“她说她本来没有什么遗憾,唯独觉得没机会看到孙孩们一点点长大、大学毕业、结婚成家,是件伤心事。”
我无言以对,百感交集。我这是在哪里?是在谈论什么?埃玛的手攥在我手里,她手指纤细柔软,即便横横竖竖满是皱纹,仍是一双修长秀美的手。我握着这只手,感觉着它柔和的温暖,这一切难道终将结束?
门铃响,杰克逊迎进来的是邻居杰尼,杰尼和我在埃玛家的茶点聚会上见过几面,算得上是熟人。她笑嘻嘻坐在埃玛身旁,热热闹闹和埃玛聊起一个共同的朋友。我心中恍惚忐忑,给杰克逊使了一个眼色,抽身出来,说要上厕所。
杰克逊把我带到主卧房,关了门,我问:“杰克逊,你老实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儿?怎么突然就连路也走不稳了?我胡涂了。”
“脑瘤有发展,压迫了腿部神经,所以走不稳,压迫了说话神经,所以口齿不清。现在已经停止全部治疗,等着。她不要去医院,一定要在家里。所以医生护士一天来检查一次,晚上有另一位护士到我家来做夜间护理,晚上10点来,早晨6点走,看,这就是护士的床。”杰克逊平静地说着,抬手指了指新加的一张沙发床,然后他想起了什么,说:“你别介意她的话,她刚才是问你能不能在她死后的葬礼上给她修指甲做化妆。我们已经定了丧葬公司,化妆修甲的服务是包括的,那里有专门给尸体化妆的专业人员。我知道你开美容店是给活人服务,给亡人化妆你不做。她胡涂,这么多年她不是只信任你吗?你不要见怪!”
我克制着心中的惊涛骇浪,伸出臂膀搂住杰克逊,他也紧紧抱住我,两个身体都轻微地颤抖着。不需要语言,我们不需要语言。
我回到埃玛身边,装着没事儿,笑嘻嘻地说:“我去你主卧卫生间上了厕所,你洗手台摆的那瓶插花,杰克逊说是你自己插的? 非常好看!”
“给你!你今天就拿走!”埃玛兴奋地指挥杰克逊把插花包起来,对我的竭力推辞不予理睬。
我一边给埃玛涂指甲,一边听埃玛和杰尼讨论首饰和着装。
“耳环,你准备戴哪付耳环?”杰尼问。
“杰克逊,请把我首饰盒拿来。”埃玛等杰克逊端来首饰盒,从里面挑出一对珍珠耳钉和配套项链。项链很细,吊着同样大小的一颗白色珍珠坠。“就这套,你看,是不是很好看?”
“真好看!”杰尼赞着,把首饰递给我看,我也赞:“好雅致!”。心里嘀咕,这是要去参加什么活动呢?
“衣服呢?衣服选了哪套?”杰尼紧追不舍。
“杰克逊,请把那套新装拿来!”
眼前一亮,这是一套玫瑰红西装套裙,里面衬着一件真丝白衬衫,端庄大气又活泼喜庆。
“这是我儿子结婚时,我穿的行头。好看吧?就穿过那一次,这次要再派一次大用场。”埃玛高兴地说着,又招呼丈夫把墙上一张照片取下来给我们看。照片上是埃玛、杰克逊和儿子媳妇的婚礼合影照。埃玛娇小的身体在那身做工讲究的红色西装裙里喜气洋洋,掐腰恰到好处,显出她骄傲的胸脯,裙摆及膝,露出两条匀称的小腿。她脸上的笑容如一朵菊花盛开着,确切说,照片里每个人脸上都开着这样的菊花,这照片就有了花园盛放的温暖和生气。
“太好看了!”我情不自禁地赞道。“你真美!”
“完美!”杰尼也赞。
“感谢上帝,这些年我身材几乎没有变化,穿上这套裙子还那么合适。”埃玛自豪地说:“怎么样?棒吧?我总嫌它红,后来不好意思再穿。现在什么都不用在乎了,就让它陪我去那里。”她的手朝天指了指。“我要漂漂亮亮欢欢喜喜地去。”这时她脸上的苍白消失不见,脸颊泛出一片粉红,眼睛晶亮闪烁,星星似的。
我吃了一惊,这才明白,杰尼和埃玛一直在讨论埃玛死后葬礼上的穿著打扮。
我加入了她俩的研讨说笑,像在谈论一个大人物的就职庆典,又像筹划一个盛大的狂欢节。
“无论瞻仰遗容、参加葬礼还是家里的纪念会,都不许穿黑衣裤,只穿平时的T恤衫牛仔裤,花花绿绿就好,来庆祝我的一生,不是来悼念我的一生!杰克逊,你记住了?请帖上一定要注明!”埃玛千叮咛万嘱咐。
“我这一生,没有遗憾!一点儿都没有!感谢上帝!”埃玛笑道,她脸上皱纹的缝隙都被红晕充满,像晚霞中一湖涟漪。
其实,埃玛一生劳碌,和杰克逊新婚之后就从意大利移民加拿大,儿子生下后高烧,得了小儿麻痹,一条腿几乎废掉,埃玛从此一心一意照顾儿子,杰克逊在食品公司当运货员,收入有限,家里的房子只好租出去两间贴补家用。
“我每天很早起床,给房客烧饭吃,那时的租客都是管饭的。”埃玛聊起过去的事儿面带微笑,“房客都喜欢我烧得饭菜,每顿饭菜我从不马虎应付。”
“累不?”我问。
“你说呢?儿子不方便走路,你可以想象一个母亲的责任和工作量,加上照顾房客,早晨五点半起床,一天不停顿,有时做着饭,就会站着打盹。这双手,哎,似乎时刻在水里泡着!”
“真看不出!这双手现在一点儿不像劳动人民!”我笑说。
她也笑,夸张地把我面前的两只手伸展了左摇右摆,道:“就是因为用了它们一辈子,现在有条件了,才格外在乎它们,动不动就带它们来见你。”
我于是每次面对这对手的时候,心里除了装有工作的细致认真,还多加了一份尊重和爱戴的温情。
“现在想那时的事儿,感觉上帝对我们真是恩待,谁能想到我儿子那样的残疾人能过上和健全人一模一样的生活?上学、工作、结婚生子!”埃玛说,“无可抱怨!”
这时,埃玛正端详着那身玫红套裙,薄薄的嘴唇轻松地咧着,眼睛在窗外明亮阳光的照耀下,弯成优美的一线。看着埃玛欢喜的面容,听着她含混不清的说笑,我的每颗细胞都在经受前所未有的洗礼。这是一种不放过一分一毫的擦洗,擦得每一根汗毛都干净地耸立,每一寸肌肤都轻松地舒展。埃玛的放得下,是早晨出门上班道别似的不以为然,是招招手说明天见的潇洒。毫无造作的坦然,温泉一般从她松弛的微笑里涓涓涌出。那一刻,一切似乎和过去一模一样,一切却又变得完全不同。我切身体会着什么是淡然,什么是对生命的感激。
我没收费,离开时和埃玛紧紧拥抱,我笑,她也笑。
七天之后,埃玛走了。
瞻仰遗容时,我穿了绿色绣花衬衫,白色牛仔裤。埃玛在那套玫红套装里安静地闭着眼睛,有一丝若隐若现的笑容挂在嘴角,似乎一个香甜的梦还没做完。妆化的很好,颧骨淡淡地红着,似乎刚喝过一杯酒,嘴唇是和衣服一色的玫红,晶莹圆润,似乎刚刚跟我说笑完毕。看不到白被单下她的纤纤玉指,但我分明感觉到那手指的柔软和温暖,椭圆的指尖平滑光润,在我眼前轻轻晃动。
“埃玛,玫红色的埃玛,别了!”我微笑,轻声说。
此时此刻,那瓶小巧的插花正摆在我书桌面前,一朵乳白色的百合在几支紫色的勿忘我中间安静地绽放。这朵绢花,永远不会衰败。
玫红色的埃玛
杜杜
“善欣,你能过来吗?”电话里埃玛的声音含混不清。
“哦,怎么?”周日,我通常不工作。
“我想请你过来帮我弄弄指甲。眉毛,对了,我的眉毛,已经没有什么眉毛了。”埃玛的嘴里长着的似乎不是舌头,而是一个圆球,我很努力才听得清八成。上次是杰克逊开车送她来我店里美容的,当时她脸色虽然略显苍白,但口齿清晰,精神愉悦。现在除了声音含混不清,意思也混沌,难道?
“好,我过20分钟就到。一会儿见!”我和家人打了招呼,就翻出外出工具箱,把美容工具整齐装箱。
开门的是杰克逊,他脸上松弛的皱纹对称地画着十几个括号,蓝眼睛一如既往地含着笑,一层灰暗淡淡地罩着。“护士在给她量血压,我带你进去。”说着,他接过我的大衣,缓慢地挂进壁橱。
阳光从宽敞的落地玻璃窗放肆地涌进来,起居室里被一片耀眼的光明吞没,一切都白得刺眼,阳光所及之处就有了一种出人意料的圣洁之感。我眯着眼睛定了定神,光雾之中,看见长沙发上埃玛半躺着,护士坐在她身边拿着本子写着什么。见我进来,埃玛伸手示意,让我坐在对面沙发上,对护士嘟囔说:“这是善欣,我好朋友,来给我修修指甲。”
护士点头微笑,又低头在本子上做记录。
“药吃过了?”护士问,一边把侧血压和脉搏的小夹子夹在埃玛指头上,笑呵呵地看着手里的机器屏幕说:“挺好,都正常。”说罢,就给埃玛听心脏。
护士检查完毕,起身冲埃玛说:“你真是个幸运的女孩儿!指甲可以在家里修,多好!”说完冲我笑着告别,又轻声对杰克逊约定了明天来访的时间。
杰克逊送走护士,埃玛已经歪歪斜斜地坐起身来,嘟嘟囔囔说:“善欣,到那天,你能来给我修指甲吗?也许还应该给我化化妆。”
“我不是在这里了?就是来帮你修指甲的。化妆?你想化妆?”和埃玛认识十几年了,她从来没有要求过化妆的美容服务。
她似乎没有听到我的话,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杰克逊把一个平衡车推到她面前,她推着车子慢慢往厨房走。我克制着震惊的心情,静静地看着她每一步艰难的行走。六周,离上次见面仅仅六周,那个行走如常的人,怎么会突然衰老到这个程度?
她缓慢地走进厨房,问杰克逊:“茶包在哪里?我得给善欣泡茶,她最爱喝那个南瓜味儿的植物香茶了。”
我和杰克逊都迅速起身,我忙不迭地说我在家刚喝了很多茶,现在不想喝茶。杰克逊一反平时温吞缓慢的习惯,已经快步走进厨房,说:“你指挥,我来泡茶。你去和善欣说话。”
“埃玛,我们来修指甲吧。”我走过去伸手想扶她走回来,中途又缩回手来,她推车能走就让她自己走吧。当年那个情景,瞬息浮现在眼前。
那时我在Spa工作,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做完头发从店里离开,要下好几个高台阶,我热心地替她推开门并伸出手去搀扶,竟意外地遭到拒绝,她尖锐地说:“不!不用!”刚出国不久的我雾水一头,这种尊老爱幼的行为是我们民族一贯遵从的美德,怎么会受到这位西方老人如此强烈的抵抗和不满?我百思不得其解。当时间的流水渐渐冲刷去心头的疑惑,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点点滴滴流淌在生活里,我才学会用另一种眼光看待曾经习惯了的事物。我没有经老人同意去搀扶她,无意中侵犯了老人的独立自主,藐视了她行走的能力,如同在对她宣布“你老了,需要帮助!”,我的善意侵犯的是她高贵的自尊。
埃玛一步步往回走,她身材矮小,我走在她身边,正好直视她头顶。只见一小块一小块裸露的头皮穿插在本来就稀少的灰白发丝之间,如同一张世界地图,陆地和海洋星罗棋布。这是放疗的结果,放射线照过的地方就不再生长头发。
埃玛坐下,我翻出修甲工具开始忙活,和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儿。
“一直坚持不做化疗?放疗呢,还在做?”我问。
“都不做了,我累了,这样挺好。”
“护士每天都来?”
“可不!有个医生也来,我哪儿都不用去,呵呵,好方便!感谢上帝!”埃玛这句话是分段说出来的,嘴里那个无形的圆球不是咯着舌头就是撞了牙。她脸上毫无血色,眼窝深陷,眉毛果然如她所说,几乎没有了一样,灰白稀少,和苍白的皮肤连成一片,额前几根发丝软绵绵耷拉着,嘴唇萎缩得只剩下两根线。
一种奇怪的不安让我浑身不适,我抓起她的手时,浑身过电似的打了一个冷战。这无骨般柔软而温热的手,被我抓了十几年了,可此刻它让我清楚地感觉到,那件重大的事情,近在眼前。
心中难过,我不敢再抬头看她。克制着颤抖,我认真对待这双手上的每一寸皮肤,指甲的每一个角落,像捧着一个罕见的珍宝,一不小心,它就会从我手中滑落、破碎。
八年前,一辈子从未吸过烟的埃玛被诊断为肺癌,肺子切除了一个,化疗放疗折腾过去,竟渐渐好了过来。八年来,她每周三次去商场大厅参加老人步行俱乐部,每周两次在小区图书馆做义工,每周一次接孙儿孙女来家团聚,一个月做一次头发修一次指甲。岁月平安逝去,癌症销声匿迹,没有在这八年之间再来骚扰她。
埃玛举行家庭茶点聚会,一定会邀请我这个年轻朋友。她自制的巧克力,形状各异,口味新颖。来找我修甲,她常常会带一包巧克力送给我孩子吃。巧克力用透明塑料纸和丝带精心包装,有小猫小狗小乌龟各种形状,味道也多变,草莓味儿、牛奶味儿、黑白巧克力双味儿的。孩子一见这些巧克力,就欢天喜地:“妈妈,你又见到埃玛了?耶!”
半年前,埃玛向我宣布了新闻,她剩下的那个肺子上发现沙状颗粒,她仍谈笑风生:“善欣,不管是不是癌,我都不想化疗了,八年前那个罪受够了,生不如死。”
上次来见我,她告诉我脑袋里刚发现了肿块,她当时精神抖擞地夸口说:”定位放疗照射,肿瘤会局部萎缩,现代医学科技日新月异,真了不得!治疗的痛苦越来越小。放心,我可以再活八年呢。”
她的手被我细致地把玩修剪,埃玛一直在含含糊糊说着话。我只猜得出一半,是在聊她三个孙孩儿,说着说着,埃玛的眼睛就红了,我抬头向杰克逊投去求助的目光,杰克逊就笑着翻译道:“她说她本来没有什么遗憾,唯独觉得没机会看到孙孩们一点点长大、大学毕业、结婚成家,是件伤心事。”
我无言以对,百感交集。我这是在哪里?是在谈论什么?埃玛的手攥在我手里,她手指纤细柔软,即便横横竖竖满是皱纹,仍是一双修长秀美的手。我握着这只手,感觉着它柔和的温暖,这一切难道终将结束?
门铃响,杰克逊迎进来的是邻居杰尼,杰尼和我在埃玛家的茶点聚会上见过几面,算得上是熟人。她笑嘻嘻坐在埃玛身旁,热热闹闹和埃玛聊起一个共同的朋友。我心中恍惚忐忑,给杰克逊使了一个眼色,抽身出来,说要上厕所。
杰克逊把我带到主卧房,关了门,我问:“杰克逊,你老实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儿?怎么突然就连路也走不稳了?我胡涂了。”
“脑瘤有发展,压迫了腿部神经,所以走不稳,压迫了说话神经,所以口齿不清。现在已经停止全部治疗,等着。她不要去医院,一定要在家里。所以医生护士一天来检查一次,晚上有另一位护士到我家来做夜间护理,晚上10点来,早晨6点走,看,这就是护士的床。”杰克逊平静地说着,抬手指了指新加的一张沙发床,然后他想起了什么,说:“你别介意她的话,她刚才是问你能不能在她死后的葬礼上给她修指甲做化妆。我们已经定了丧葬公司,化妆修甲的服务是包括的,那里有专门给尸体化妆的专业人员。我知道你开美容店是给活人服务,给亡人化妆你不做。她胡涂,这么多年她不是只信任你吗?你不要见怪!”
我克制着心中的惊涛骇浪,伸出臂膀搂住杰克逊,他也紧紧抱住我,两个身体都轻微地颤抖着。不需要语言,我们不需要语言。
我回到埃玛身边,装着没事儿,笑嘻嘻地说:“我去你主卧卫生间上了厕所,你洗手台摆的那瓶插花,杰克逊说是你自己插的? 非常好看!”
“给你!你今天就拿走!”埃玛兴奋地指挥杰克逊把插花包起来,对我的竭力推辞不予理睬。
我一边给埃玛涂指甲,一边听埃玛和杰尼讨论首饰和着装。
“耳环,你准备戴哪付耳环?”杰尼问。
“杰克逊,请把我首饰盒拿来。”埃玛等杰克逊端来首饰盒,从里面挑出一对珍珠耳钉和配套项链。项链很细,吊着同样大小的一颗白色珍珠坠。“就这套,你看,是不是很好看?”
“真好看!”杰尼赞着,把首饰递给我看,我也赞:“好雅致!”。心里嘀咕,这是要去参加什么活动呢?
“衣服呢?衣服选了哪套?”杰尼紧追不舍。
“杰克逊,请把那套新装拿来!”
眼前一亮,这是一套玫瑰红西装套裙,里面衬着一件真丝白衬衫,端庄大气又活泼喜庆。
“这是我儿子结婚时,我穿的行头。好看吧?就穿过那一次,这次要再派一次大用场。”埃玛高兴地说着,又招呼丈夫把墙上一张照片取下来给我们看。照片上是埃玛、杰克逊和儿子媳妇的婚礼合影照。埃玛娇小的身体在那身做工讲究的红色西装裙里喜气洋洋,掐腰恰到好处,显出她骄傲的胸脯,裙摆及膝,露出两条匀称的小腿。她脸上的笑容如一朵菊花盛开着,确切说,照片里每个人脸上都开着这样的菊花,这照片就有了花园盛放的温暖和生气。
“太好看了!”我情不自禁地赞道。“你真美!”
“完美!”杰尼也赞。
“感谢上帝,这些年我身材几乎没有变化,穿上这套裙子还那么合适。”埃玛自豪地说:“怎么样?棒吧?我总嫌它红,后来不好意思再穿。现在什么都不用在乎了,就让它陪我去那里。”她的手朝天指了指。“我要漂漂亮亮欢欢喜喜地去。”这时她脸上的苍白消失不见,脸颊泛出一片粉红,眼睛晶亮闪烁,星星似的。
我吃了一惊,这才明白,杰尼和埃玛一直在讨论埃玛死后葬礼上的穿著打扮。
我加入了她俩的研讨说笑,像在谈论一个大人物的就职庆典,又像筹划一个盛大的狂欢节。
“无论瞻仰遗容、参加葬礼还是家里的纪念会,都不许穿黑衣裤,只穿平时的T恤衫牛仔裤,花花绿绿就好,来庆祝我的一生,不是来悼念我的一生!杰克逊,你记住了?请帖上一定要注明!”埃玛千叮咛万嘱咐。
“我这一生,没有遗憾!一点儿都没有!感谢上帝!”埃玛笑道,她脸上皱纹的缝隙都被红晕充满,像晚霞中一湖涟漪。
其实,埃玛一生劳碌,和杰克逊新婚之后就从意大利移民加拿大,儿子生下后高烧,得了小儿麻痹,一条腿几乎废掉,埃玛从此一心一意照顾儿子,杰克逊在食品公司当运货员,收入有限,家里的房子只好租出去两间贴补家用。
“我每天很早起床,给房客烧饭吃,那时的租客都是管饭的。”埃玛聊起过去的事儿面带微笑,“房客都喜欢我烧得饭菜,每顿饭菜我从不马虎应付。”
“累不?”我问。
“你说呢?儿子不方便走路,你可以想象一个母亲的责任和工作量,加上照顾房客,早晨五点半起床,一天不停顿,有时做着饭,就会站着打盹。这双手,哎,似乎时刻在水里泡着!”
“真看不出!这双手现在一点儿不像劳动人民!”我笑说。
她也笑,夸张地把我面前的两只手伸展了左摇右摆,道:“就是因为用了它们一辈子,现在有条件了,才格外在乎它们,动不动就带它们来见你。”
我于是每次面对这对手的时候,心里除了装有工作的细致认真,还多加了一份尊重和爱戴的温情。
“现在想那时的事儿,感觉上帝对我们真是恩待,谁能想到我儿子那样的残疾人能过上和健全人一模一样的生活?上学、工作、结婚生子!”埃玛说,“无可抱怨!”
这时,埃玛正端详着那身玫红套裙,薄薄的嘴唇轻松地咧着,眼睛在窗外明亮阳光的照耀下,弯成优美的一线。看着埃玛欢喜的面容,听着她含混不清的说笑,我的每颗细胞都在经受前所未有的洗礼。这是一种不放过一分一毫的擦洗,擦得每一根汗毛都干净地耸立,每一寸肌肤都轻松地舒展。埃玛的放得下,是早晨出门上班道别似的不以为然,是招招手说明天见的潇洒。毫无造作的坦然,温泉一般从她松弛的微笑里涓涓涌出。那一刻,一切似乎和过去一模一样,一切却又变得完全不同。我切身体会着什么是淡然,什么是对生命的感激。
我没收费,离开时和埃玛紧紧拥抱,我笑,她也笑。
七天之后,埃玛走了。
瞻仰遗容时,我穿了绿色绣花衬衫,白色牛仔裤。埃玛在那套玫红套装里安静地闭着眼睛,有一丝若隐若现的笑容挂在嘴角,似乎一个香甜的梦还没做完。妆化的很好,颧骨淡淡地红着,似乎刚喝过一杯酒,嘴唇是和衣服一色的玫红,晶莹圆润,似乎刚刚跟我说笑完毕。看不到白被单下她的纤纤玉指,但我分明感觉到那手指的柔软和温暖,椭圆的指尖平滑光润,在我眼前轻轻晃动。
“埃玛,玫红色的埃玛,别了!”我微笑,轻声说。
此时此刻,那瓶小巧的插花正摆在我书桌面前,一朵乳白色的百合在几支紫色的勿忘我中间安静地绽放。这朵绢花,永远不会衰败。
- 注册
- 2014-04-15
- 消息
- 6,048
- 荣誉分数
- 11,373
- 声望点数
- 1,323
贴出版权原作! 太好了!感谢分享!我这本新书《玫红色的艾玛》短篇小说集收录了我的50余篇短篇小说。时间跨度较大。书的题目用了其中一篇小说的题目,这篇小说,我现在贴一下:
玫红色的埃玛
杜杜
“善欣,你能过来吗?”电话里埃玛的声音含混不清。
“哦,怎么?”周日,我通常不工作。
“我想请你过来帮我弄弄指甲。眉毛,对了,我的眉毛,已经没有什么眉毛了。”埃玛的嘴里长着的似乎不是舌头,而是一个圆球,我很努力才听得清八成。上次是杰克逊开车送她来我店里美容的,当时她脸色虽然略显苍白,但口齿清晰,精神愉悦。现在除了声音含混不清,意思也混沌,难道?
“好,我过20分钟就到。一会儿见!”我和家人打了招呼,就翻出外出工具箱,把美容工具整齐装箱。
开门的是杰克逊,他脸上松弛的皱纹对称地画着十几个括号,蓝眼睛一如既往地含着笑,一层灰暗淡淡地罩着。“护士在给她量血压,我带你进去。”说着,他接过我的大衣,缓慢地挂进壁橱。
阳光从宽敞的落地玻璃窗放肆地涌进来,起居室里被一片耀眼的光明吞没,一切都白得刺眼,阳光所及之处就有了一种出人意料的圣洁之感。我眯着眼睛定了定神,光雾之中,看见长沙发上埃玛半躺着,护士坐在她身边拿着本子写着什么。见我进来,埃玛伸手示意,让我坐在对面沙发上,对护士嘟囔说:“这是善欣,我好朋友,来给我修修指甲。”
护士点头微笑,又低头在本子上做记录。
“药吃过了?”护士问,一边把侧血压和脉搏的小夹子夹在埃玛指头上,笑呵呵地看着手里的机器屏幕说:“挺好,都正常。”说罢,就给埃玛听心脏。
护士检查完毕,起身冲埃玛说:“你真是个幸运的女孩儿!指甲可以在家里修,多好!”说完冲我笑着告别,又轻声对杰克逊约定了明天来访的时间。
杰克逊送走护士,埃玛已经歪歪斜斜地坐起身来,嘟嘟囔囔说:“善欣,到那天,你能来给我修指甲吗?也许还应该给我化化妆。”
“我不是在这里了?就是来帮你修指甲的。化妆?你想化妆?”和埃玛认识十几年了,她从来没有要求过化妆的美容服务。
她似乎没有听到我的话,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杰克逊把一个平衡车推到她面前,她推着车子慢慢往厨房走。我克制着震惊的心情,静静地看着她每一步艰难的行走。六周,离上次见面仅仅六周,那个行走如常的人,怎么会突然衰老到这个程度?
她缓慢地走进厨房,问杰克逊:“茶包在哪里?我得给善欣泡茶,她最爱喝那个南瓜味儿的植物香茶了。”
我和杰克逊都迅速起身,我忙不迭地说我在家刚喝了很多茶,现在不想喝茶。杰克逊一反平时温吞缓慢的习惯,已经快步走进厨房,说:“你指挥,我来泡茶。你去和善欣说话。”
“埃玛,我们来修指甲吧。”我走过去伸手想扶她走回来,中途又缩回手来,她推车能走就让她自己走吧。当年那个情景,瞬息浮现在眼前。
那时我在Spa工作,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做完头发从店里离开,要下好几个高台阶,我热心地替她推开门并伸出手去搀扶,竟意外地遭到拒绝,她尖锐地说:“不!不用!”刚出国不久的我雾水一头,这种尊老爱幼的行为是我们民族一贯遵从的美德,怎么会受到这位西方老人如此强烈的抵抗和不满?我百思不得其解。当时间的流水渐渐冲刷去心头的疑惑,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点点滴滴流淌在生活里,我才学会用另一种眼光看待曾经习惯了的事物。我没有经老人同意去搀扶她,无意中侵犯了老人的独立自主,藐视了她行走的能力,如同在对她宣布“你老了,需要帮助!”,我的善意侵犯的是她高贵的自尊。
埃玛一步步往回走,她身材矮小,我走在她身边,正好直视她头顶。只见一小块一小块裸露的头皮穿插在本来就稀少的灰白发丝之间,如同一张世界地图,陆地和海洋星罗棋布。这是放疗的结果,放射线照过的地方就不再生长头发。
埃玛坐下,我翻出修甲工具开始忙活,和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儿。
“一直坚持不做化疗?放疗呢,还在做?”我问。
“都不做了,我累了,这样挺好。”
“护士每天都来?”
“可不!有个医生也来,我哪儿都不用去,呵呵,好方便!感谢上帝!”埃玛这句话是分段说出来的,嘴里那个无形的圆球不是咯着舌头就是撞了牙。她脸上毫无血色,眼窝深陷,眉毛果然如她所说,几乎没有了一样,灰白稀少,和苍白的皮肤连成一片,额前几根发丝软绵绵耷拉着,嘴唇萎缩得只剩下两根线。
一种奇怪的不安让我浑身不适,我抓起她的手时,浑身过电似的打了一个冷战。这无骨般柔软而温热的手,被我抓了十几年了,可此刻它让我清楚地感觉到,那件重大的事情,近在眼前。
心中难过,我不敢再抬头看她。克制着颤抖,我认真对待这双手上的每一寸皮肤,指甲的每一个角落,像捧着一个罕见的珍宝,一不小心,它就会从我手中滑落、破碎。
八年前,一辈子从未吸过烟的埃玛被诊断为肺癌,肺子切除了一个,化疗放疗折腾过去,竟渐渐好了过来。八年来,她每周三次去商场大厅参加老人步行俱乐部,每周两次在小区图书馆做义工,每周一次接孙儿孙女来家团聚,一个月做一次头发修一次指甲。岁月平安逝去,癌症销声匿迹,没有在这八年之间再来骚扰她。
埃玛举行家庭茶点聚会,一定会邀请我这个年轻朋友。她自制的巧克力,形状各异,口味新颖。来找我修甲,她常常会带一包巧克力送给我孩子吃。巧克力用透明塑料纸和丝带精心包装,有小猫小狗小乌龟各种形状,味道也多变,草莓味儿、牛奶味儿、黑白巧克力双味儿的。孩子一见这些巧克力,就欢天喜地:“妈妈,你又见到埃玛了?耶!”
半年前,埃玛向我宣布了新闻,她剩下的那个肺子上发现沙状颗粒,她仍谈笑风生:“善欣,不管是不是癌,我都不想化疗了,八年前那个罪受够了,生不如死。”
上次来见我,她告诉我脑袋里刚发现了肿块,她当时精神抖擞地夸口说:”定位放疗照射,肿瘤会局部萎缩,现代医学科技日新月异,真了不得!治疗的痛苦越来越小。放心,我可以再活八年呢。”
她的手被我细致地把玩修剪,埃玛一直在含含糊糊说着话。我只猜得出一半,是在聊她三个孙孩儿,说着说着,埃玛的眼睛就红了,我抬头向杰克逊投去求助的目光,杰克逊就笑着翻译道:“她说她本来没有什么遗憾,唯独觉得没机会看到孙孩们一点点长大、大学毕业、结婚成家,是件伤心事。”
我无言以对,百感交集。我这是在哪里?是在谈论什么?埃玛的手攥在我手里,她手指纤细柔软,即便横横竖竖满是皱纹,仍是一双修长秀美的手。我握着这只手,感觉着它柔和的温暖,这一切难道终将结束?
门铃响,杰克逊迎进来的是邻居杰尼,杰尼和我在埃玛家的茶点聚会上见过几面,算得上是熟人。她笑嘻嘻坐在埃玛身旁,热热闹闹和埃玛聊起一个共同的朋友。我心中恍惚忐忑,给杰克逊使了一个眼色,抽身出来,说要上厕所。
杰克逊把我带到主卧房,关了门,我问:“杰克逊,你老实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儿?怎么突然就连路也走不稳了?我胡涂了。”
“脑瘤有发展,压迫了腿部神经,所以走不稳,压迫了说话神经,所以口齿不清。现在已经停止全部治疗,等着。她不要去医院,一定要在家里。所以医生护士一天来检查一次,晚上有另一位护士到我家来做夜间护理,晚上10点来,早晨6点走,看,这就是护士的床。”杰克逊平静地说着,抬手指了指新加的一张沙发床,然后他想起了什么,说:“你别介意她的话,她刚才是问你能不能在她死后的葬礼上给她修指甲做化妆。我们已经定了丧葬公司,化妆修甲的服务是包括的,那里有专门给尸体化妆的专业人员。我知道你开美容店是给活人服务,给亡人化妆你不做。她胡涂,这么多年她不是只信任你吗?你不要见怪!”
我克制着心中的惊涛骇浪,伸出臂膀搂住杰克逊,他也紧紧抱住我,两个身体都轻微地颤抖着。不需要语言,我们不需要语言。
我回到埃玛身边,装着没事儿,笑嘻嘻地说:“我去你主卧卫生间上了厕所,你洗手台摆的那瓶插花,杰克逊说是你自己插的? 非常好看!”
“给你!你今天就拿走!”埃玛兴奋地指挥杰克逊把插花包起来,对我的竭力推辞不予理睬。
我一边给埃玛涂指甲,一边听埃玛和杰尼讨论首饰和着装。
“耳环,你准备戴哪付耳环?”杰尼问。
“杰克逊,请把我首饰盒拿来。”埃玛等杰克逊端来首饰盒,从里面挑出一对珍珠耳钉和配套项链。项链很细,吊着同样大小的一颗白色珍珠坠。“就这套,你看,是不是很好看?”
“真好看!”杰尼赞着,把首饰递给我看,我也赞:“好雅致!”。心里嘀咕,这是要去参加什么活动呢?
“衣服呢?衣服选了哪套?”杰尼紧追不舍。
“杰克逊,请把那套新装拿来!”
眼前一亮,这是一套玫瑰红西装套裙,里面衬着一件真丝白衬衫,端庄大气又活泼喜庆。
“这是我儿子结婚时,我穿的行头。好看吧?就穿过那一次,这次要再派一次大用场。”埃玛高兴地说着,又招呼丈夫把墙上一张照片取下来给我们看。照片上是埃玛、杰克逊和儿子媳妇的婚礼合影照。埃玛娇小的身体在那身做工讲究的红色西装裙里喜气洋洋,掐腰恰到好处,显出她骄傲的胸脯,裙摆及膝,露出两条匀称的小腿。她脸上的笑容如一朵菊花盛开着,确切说,照片里每个人脸上都开着这样的菊花,这照片就有了花园盛放的温暖和生气。
“太好看了!”我情不自禁地赞道。“你真美!”
“完美!”杰尼也赞。
“感谢上帝,这些年我身材几乎没有变化,穿上这套裙子还那么合适。”埃玛自豪地说:“怎么样?棒吧?我总嫌它红,后来不好意思再穿。现在什么都不用在乎了,就让它陪我去那里。”她的手朝天指了指。“我要漂漂亮亮欢欢喜喜地去。”这时她脸上的苍白消失不见,脸颊泛出一片粉红,眼睛晶亮闪烁,星星似的。
我吃了一惊,这才明白,杰尼和埃玛一直在讨论埃玛死后葬礼上的穿著打扮。
我加入了她俩的研讨说笑,像在谈论一个大人物的就职庆典,又像筹划一个盛大的狂欢节。
“无论瞻仰遗容、参加葬礼还是家里的纪念会,都不许穿黑衣裤,只穿平时的T恤衫牛仔裤,花花绿绿就好,来庆祝我的一生,不是来悼念我的一生!杰克逊,你记住了?请帖上一定要注明!”埃玛千叮咛万嘱咐。
“我这一生,没有遗憾!一点儿都没有!感谢上帝!”埃玛笑道,她脸上皱纹的缝隙都被红晕充满,像晚霞中一湖涟漪。
其实,埃玛一生劳碌,和杰克逊新婚之后就从意大利移民加拿大,儿子生下后高烧,得了小儿麻痹,一条腿几乎废掉,埃玛从此一心一意照顾儿子,杰克逊在食品公司当运货员,收入有限,家里的房子只好租出去两间贴补家用。
“我每天很早起床,给房客烧饭吃,那时的租客都是管饭的。”埃玛聊起过去的事儿面带微笑,“房客都喜欢我烧得饭菜,每顿饭菜我从不马虎应付。”
“累不?”我问。
“你说呢?儿子不方便走路,你可以想象一个母亲的责任和工作量,加上照顾房客,早晨五点半起床,一天不停顿,有时做着饭,就会站着打盹。这双手,哎,似乎时刻在水里泡着!”
“真看不出!这双手现在一点儿不像劳动人民!”我笑说。
她也笑,夸张地把我面前的两只手伸展了左摇右摆,道:“就是因为用了它们一辈子,现在有条件了,才格外在乎它们,动不动就带它们来见你。”
我于是每次面对这对手的时候,心里除了装有工作的细致认真,还多加了一份尊重和爱戴的温情。
“现在想那时的事儿,感觉上帝对我们真是恩待,谁能想到我儿子那样的残疾人能过上和健全人一模一样的生活?上学、工作、结婚生子!”埃玛说,“无可抱怨!”
这时,埃玛正端详着那身玫红套裙,薄薄的嘴唇轻松地咧着,眼睛在窗外明亮阳光的照耀下,弯成优美的一线。看着埃玛欢喜的面容,听着她含混不清的说笑,我的每颗细胞都在经受前所未有的洗礼。这是一种不放过一分一毫的擦洗,擦得每一根汗毛都干净地耸立,每一寸肌肤都轻松地舒展。埃玛的放得下,是早晨出门上班道别似的不以为然,是招招手说明天见的潇洒。毫无造作的坦然,温泉一般从她松弛的微笑里涓涓涌出。那一刻,一切似乎和过去一模一样,一切却又变得完全不同。我切身体会着什么是淡然,什么是对生命的感激。
我没收费,离开时和埃玛紧紧拥抱,我笑,她也笑。
七天之后,埃玛走了。
瞻仰遗容时,我穿了绿色绣花衬衫,白色牛仔裤。埃玛在那套玫红套装里安静地闭着眼睛,有一丝若隐若现的笑容挂在嘴角,似乎一个香甜的梦还没做完。妆化的很好,颧骨淡淡地红着,似乎刚喝过一杯酒,嘴唇是和衣服一色的玫红,晶莹圆润,似乎刚刚跟我说笑完毕。看不到白被单下她的纤纤玉指,但我分明感觉到那手指的柔软和温暖,椭圆的指尖平滑光润,在我眼前轻轻晃动。
“埃玛,玫红色的埃玛,别了!”我微笑,轻声说。
此时此刻,那瓶小巧的插花正摆在我书桌面前,一朵乳白色的百合在几支紫色的勿忘我中间安静地绽放。这朵绢花,永远不会衰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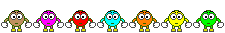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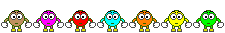
- 注册
- 2004-03-10
- 消息
- 1,422
- 荣誉分数
- 1,083
- 声望点数
- 323
我的 新书短篇小说集《玫红色的艾玛》近日出版并在Amazon世界各地网站上架销售。加拿大Amazon链接如下:
https://www.amazon.ca/Emma-Rose-Ant...8&qid=1521832832&sr=8-1&keywords=emma+in+Rose
Amazon搜索词:Dudu, Dudu fiction, Zhanqing Du, Dudu Anthology, Emma in Rose
渥太华的村民欲购买签名书,可直接与作者我联络,请加我微信 dudu201311
此书收录了我的50余篇小说,时间跨度较大。 移民们把他乡做故乡,落地生根过程中所遭遇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心路历程等在书中有多方位体现。
英文简介:The anthology collects over 50 short fictions by DuDu (Zhanqing Du). Her main characters focused on the Chinese immigrants with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different ages, different occupations and different genders, who settled down and started their new life overseas. These stories not only gave a panoramic view of the new immigrants culture clashes, sense and sensibility, love and hate, life and death in the adaption stages from an apprehensive newcomer to a confident citizen in their beloved second homeland, but also sketched many colourful facets of humanities as well as the exotic overseas life style to her readers. The book vividly manifests that the two opposite sides in our human nature are universal and inter-changeable, and prevailing despite of culture and distance. This book is written in Chinese.


https://www.amazon.ca/Emma-Rose-Ant...8&qid=1521832832&sr=8-1&keywords=emma+in+Rose
Amazon搜索词:Dudu, Dudu fiction, Zhanqing Du, Dudu Anthology, Emma in Rose
渥太华的村民欲购买签名书,可直接与作者我联络,请加我微信 dudu201311
此书收录了我的50余篇小说,时间跨度较大。 移民们把他乡做故乡,落地生根过程中所遭遇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心路历程等在书中有多方位体现。
英文简介:The anthology collects over 50 short fictions by DuDu (Zhanqing Du). Her main characters focused on the Chinese immigrants with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different ages, different occupations and different genders, who settled down and started their new life overseas. These stories not only gave a panoramic view of the new immigrants culture clashes, sense and sensibility, love and hate, life and death in the adaption stages from an apprehensive newcomer to a confident citizen in their beloved second homeland, but also sketched many colourful facets of humanities as well as the exotic overseas life style to her readers. The book vividly manifests that the two opposite sides in our human nature are universal and inter-changeable, and prevailing despite of culture and distance. This book is written in Chinese.
附件
最后编辑:

 读了杜杜的小说,我忽然有一种对死亡的顿悟, 包括原来的朋友 (表哥)讲的故事,和朋友的探讨都连成一条线了。 我甚至觉得你不是在写小说,而是画了一条线,怎样经过人生的最后阶段。好书要推荐给更多的人!
读了杜杜的小说,我忽然有一种对死亡的顿悟, 包括原来的朋友 (表哥)讲的故事,和朋友的探讨都连成一条线了。 我甚至觉得你不是在写小说,而是画了一条线,怎样经过人生的最后阶段。好书要推荐给更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