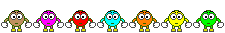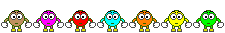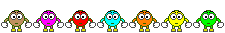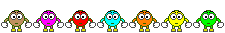三十四
我没有能等到小萍醒来就到C大去上课去了。快到期中考试了,上午有一门复习课我不想给错掉。下课后我到图书馆去还书借书,耽搁了一会儿,等开车回到寓所时,小萍已经走了。我在客厅里遇到哲学博士,他说小萍醒了后跟房东和他聊了一会儿天后走的。哲学博士一直对小萍挺有好感的,见到小萍总是要跟小萍聊半天。
小镇上的她跟我分手后,我好久都没有能恢复过来。晚上我独自披着月光在街上散步,像是一个疲惫而沮丧的旅人。有时我在想,其实是我错了,我不该这么快这么深地爱上一个人,也不该指望或者期望这么短的时间的感情会变成永恒的爱情。小镇上的她做了她自己的选择,她的选择是合情合理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伤口在慢慢地愈合,小镇上的她由开始的每天都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变成每隔几天才会出现一次。
树上的落叶逐渐落光了,白白的雪花代替了枯黄的落叶,绿草被埋在厚厚的雪地底下,积雪越积越高。漫长的冬天过后,有一天积雪一下都融化了,绿色的草地重新露了出来,街上的风也变暖了。等到一年之后的夏天,我几乎已经不再会想起她来了。二月份放春假的时候,我曾经有个念头想开到小镇上去看看她。但是想了想,终究没有去,因为我怕心底的疮疤再被揭开,怕自己会再一次伤心。
这一年里,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小萍经常打电话来找我。小萍的感情生活也不顺利,她交了一个男朋友,交往了三个月后,发现男朋友太花心,就吹了,此后一直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过圣诞和新年的时候她回国去看父母了,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了一包我家里人托她带给我的东西。平时我们有时一起去外面吃饭,有时一起做饭,偶尔有好片子的时候也会一起去看电影。我知道小萍在家里是独身子女,从来娇生惯养,不会做饭,她做出来的饭菜不是糊了,就是咸了,就是淡了,但是我也不会做饭,所以倒谁也不用笑话谁,每次嘻嘻哈哈的多难吃的饭也都给吃了。我们像是小的时候一样无话不谈,互相拿对方开心,有时说话说过了头,会生气一阵,过不了多久又和好如初。
自从哲学博士有了代课的临时工作后,他有了收入,经常约我去一起去泡吧。周末的时候我开车带着他一起去酒吧喝酒,有时也约上小萍一起去。跟哲学博士一起去泡吧只能给我带来暂时的快乐,无论头天晚上多么的沉迷,第二天我依然会回到空虚之中,感觉单调而乏味。那一年,我一直像一个神不守舍的游魂一样,茫然地上学,打工,做着每天该做的事,周末晚上在酒吧里渡过,好像一块心里的一块永远地失去了。
哲学博士有些想跟小萍好,但是小萍看不上哲学博士,我也觉得他们不般配。哲学博士问过我,我直截了当的告诉哲学博士,小萍喜欢的不是他这一类的,把哲学博士给打击回去了。哲学博士倒也不在意,每次出去泡吧的时候都要我叫上小萍。小萍周末没事儿,也愿意跟我们一起出去。于是我们成了三人团,周末总是一起出去,一起喝酒,一起聊天,一起嘻嘻哈哈。我跟哲学博士在酒吧里跟女孩们套磁,小萍也不生气,有时还像个媒婆一样热心地告诉我们哪个桌子上有女孩往我们这边看了,蹿叨我们去把女孩叫到我们桌子上来,给女孩们买酒喝,一起聊天,但是一旦有哪个女孩跟我们聊得情投意合,有想跟我们一起回去的意向时,小萍就开始捣乱了,她会讲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来,直到女孩识趣的自己离开。有时哲学博士和我回去之后都发誓以后再也不带小萍一起泡吧去了,但是等到下一个周末,我们想出去的时候,又很自然的给小萍打电话,于是在酒吧里重演每次的喜剧和悲剧。
今天咱们去哪里?小萍把脚踩在沙发边上,一边撩起裙子把黑色的丝袜往腿上套,一边问站在门口等着她的哲学博士和我说。
老地方吧,哲学博士盯着她的腿说。
今天你不能喝太多,小萍瞥了我一眼说。上次你喝多了,把车差点儿开到运河里去。
还说我呢,你上次不也喝多了吗,非要到河边去看月亮,那河边的月亮有什么好看的?要不是往河边开,我的车还不至于撞到树上呢,把前面的制冷器都撞坏了,水流了一地,后来花了好几百块才修好。今天我只喝一杯,好好给你们当司机。
说的好听,上次你也是这么说的。小萍往嘴上涂着唇膏说。你们谁还有大麻?
没了,哲学博士说,要有就带来了。
那个卖大麻的老在舞厅那里蹲点儿,我说。一会儿我去找他买点儿。你快点儿倒扯,都等了你快半个小时了,说好的在门口见,你总是磨磨蹭蹭的,从来没准时过。
女人都这样,小萍往脸上扑了一些粉说。再说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我还睡觉呢,前两天都开夜车来的,今天早上刚考完试,睡了一天。
算了吧,我说。别老给自己找借口了,你从来就没有准时过,不是这就是那的,谁要做你的男朋友得有多大耐心啊。怪不得你男朋友跟你吹了呢。
是我蹬了他的好不好,小萍对着镜子仔细检查着自己的脸说。
你这屋子真热,我说。怎么还不装空调啊,没空调夏天怎么过啊?
我不会装,小萍说。你们会装吗?要不帮我装一个。
没问题,咱哲学博士学问那么大,装个空调算什么,是吧?我问哲学博士说。
我没装过,哲学博士说。不过不应该很难吧,要不现在出去买个空调来,按照说明装装试试?
太好了,小萍说,楼下不远的地方的超市就有卖空调的,劳驾你们先帮我把空调装了,装完空调我请你们喝酒。
我们一起下楼开车去了附近的超市买了一个窗式空调,一把锤子,一个改锥,一卷胶带。我跟哲学博士把空调抬到楼上来,哲学博士打开空调的箱子,仔细读了一遍说明书,然后按照说明书上写的步骤,指挥着我一起把靠阳台的一个窗玻璃卸下。我们抬起空调,把长方形的空调塞进窗户框,让它的尾部冲着阳台,用胶带固定住,然后把窗户框剩余的空间用纸板塞住,又在空调底下塞了一块阳台上找到的半截砖头,让空调不能活动。用胶带把窗户框重新封好之后,我把空调电源接上,随着嗡嗡的一阵响声,凉气从空调口冒了出来。小萍把空调开到最大,又到阳台上去看了看,皱着眉头说噪音太大了,而且阳台被空调尾部喷出来的热气搞得很热。哲学博士说那怎么办呢,要不把空调卸下来,重新把窗玻璃装上?小萍说先就这样吧,以后再说。装空调给我和哲学博士身上都弄了一身汗,我们站在空调前,让冷气把汗吹干。
这回能走了吧?我看着小萍说。
好了好了,走吧,催命鬼。小萍挎上手包,换了一双高跟鞋,跟我们一起下了楼。
我在酒吧的肮脏的洗手间里小便后,看到镜子里面自己的面颊消瘦,眼睛和皮肤都泛着酒醉的红色。玻璃镜子上有几道划痕,像是谁用刀子在玻璃上打了个叉子。空气像玻璃一样压着我,让我喘不过气来。我顺着楼梯走回吧台时,看见小萍和哲学博士正坐在吧台的高脚凳上聊得热乎。外面在下着小雨,我坐到小萍的一边,一边继续喝我的啤酒,一边看着打在窗户上的雨滴。我最不喜欢夏天,夏天的闷热总是让我抑郁,我无法忍受夏天的炎热,不喜欢被那种潮湿和闷热的空气包围着,无论走到哪里,身上都是黏糊糊的感觉。那种感觉让我觉得烦躁,让我想找个清凉的地方躲进去不再出来。我喜欢看着雨水淅淅沥沥地滴到窗户上。自从跟小镇上的她分手后,我总是觉得空虚和孤独,会随时随地的被这种感觉笼罩,只有熙熙攘攘的酒吧里喝啤酒的时候才会让我暂时忘掉这种空虚和孤独,虽然在离开酒吧后,重新返回来的那种失落会让我感到更为空虚。
从酒吧的玻璃窗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进对面的舞厅之后,我拍了小萍的肩膀一下,告诉她看着我的座位和啤酒,我到对面去去就来。
你干嘛去?小萍扭头问我说。
去买大麻,我说。顺便抽根烟。
外面的小雨停了。我走过湿湿的街道,在对面的舞厅里找到了那个卖大麻的家伙,他正在跟几个女孩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讲话。我真不知道这么吵闹的音乐声中怎么能听见说什么。我走进舞厅,用眼光四处寻找他的时候,他认出了我,看见我跟他点头,知道我是来找他买药的,就甩下了身边的女孩,向我走来。他示意我跟他到了门外。我们站在还滴着水的门口,身边是一些抽烟的人,一个喝醉酒的女孩正坐在路边的湿漉漉的台阶上,正在呕吐,身边是一大滩湿漉漉的呕吐物。
你带烟了吗?给我一只,他说。
我掏出烟来,给了他一只,自己点上一只,把打火机递给他。
你看那些女孩,跟没穿衣服似的,你都能看见里面,他把打火机还给我时看着身边走过的两个穿得很少的女孩说。
你带着呢吗?我问他说。
他点点头,很自信地拍了拍兜。你该试试药片,药片的效果更好,更快,保证你会喜欢,他深吸了一口烟说。
我点点头,从钱包里掏出三十块钱,卷在手里塞给了他。他把钱快速地放进兜里,从另一个兜里拿出一个小朔料袋子来,用身子挡住街灯射过来的光线,在黑暗的阴影里数了几片药片,包在一张纸里递给我。我看了一眼周围的人,周围抽烟的人似乎司空见惯,没人在意。
要不要更厉害一点儿的?他一边咧着嘴笑着,一边问我说。
不用,要是需要再找你,我把药片揣进裤兜里说。
他从兜里拿出一张纸来,写了一个电话号码给我。伙计,有事儿打这个电话找我,Have fun。他把纸条塞给我,拿拳头顶了一下我的拳头,暧昧地笑了一下,掐灭了烟蒂,摇摇晃晃地走回舞厅去了。
我走到街边去继续吸烟,觉得心里在不安分的躁动。突然想起小镇上的她此刻大概正在跟男朋友在一起吧,想起这些来我就觉得很烦恼。路边一个穿着吊带衫和很短的裙子的女孩走过来找我要了一根烟。我给她点上烟的时候看见她的腰部鼓鼓囊囊的,像是有什么东西隐藏在吊带衫里面。
那是什么?我指着她吊带衫下鼓起的地方问。
哦,是啤酒瓶,我出来的时候忘了,把啤酒也带了出来,她说。她掀开吊带衫的下摆让我看,果然一瓶啤酒插在短裙的贴着肚子的地方,她的腰身很细很平坦,肚脐眼很可爱,挨着短裙的地方露出一点粉色的内裤边沿。
谁在乎呢,这里也没有警察管着,我看看四周说。
那让人看见也不好,她把吊带衫的下摆放下说。所以藏在衣服里面。你哪儿人啊?
中国,我说。
没去过那里,但是我去过日本和韩国,待过几个月,你喜欢这里吗?女孩问。
喜欢,很不错的一个小城。我说。
我刚才看见你跟那谁在一起来的,她诡秘的说。你找他买药呢吧?
嗯,我点点头说。你认识他?
谁不认识他啊,她说。这家伙靠这个赚了不少钱。
我的朋友们在对面的酒吧里等着我呢,我指指酒吧说。你要是有功夫到对面去找我吧.
好的,再会,她夹着烟的手对我挥挥说。
我把烟头扔到路边一个上面罩着铁丝网的水泥烟灰缸里,跨过黑湿黑湿的马路回到了酒吧。
走回刚才坐着的吧台前,我看见昏暗的灯光下,一个高个子帅哥坐在我刚才坐的高脚凳上,正端着一杯酒在跟小萍套磁。这是我男朋友,小萍见我过来后就指着我对那个帅哥说。高个子尴尬地举起酒杯跟我打了个招呼,讪讪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离开,找别的女孩接着套磁去了。我坐回到小萍旁边的高脚凳上,拿过刚才喝了一半的啤酒来喝了一口。我们坐在吧台的一边,旁边是几个男人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头上的电视里直播的冰球比赛。今天是一场关键的比赛,W城的冰球队能否进入下一轮比赛就全看今天的比赛结果了。
哲学博士呢?我问小萍说。
跟人套磁去了,小萍用嘴指了指酒吧的一头。我看见哲学博士在跟一个年龄大的女人一起喝酒。你买到了吗?小萍问我说。
买到了,是药片,我拍拍裤兜说。
给我一片,小萍说。
我从兜里摸索着掏出两片白色的长方形药片,一片丢进了小萍的鸡尾酒杯,一片丢进了我的啤酒瓶。药片悄无声息地滑落在酒里,缓慢地溶解。
嗨,你怎么在这里?有人拍了我的后背一下说。
我回过头,看见是系里的一个同学站在我的侧面。他好像喝多了酒,端着酒杯有些站立不稳地扶着吧台。
今晚系里的同学们都在老闷家里开party,特别热闹,一起去吧,他醉眼熏熏的说。他家离这里不远,走着一会儿就到。
老闷是我们的一个沙特同学的绰号,家里送出来留学的,好像很有钱,学的不怎么样,人倒是不错,很实在,乐于助人,每个周末都在家里搞派对。
我们去party玩吧,我对小萍说。同学的party,都不是坏人。
走吧走吧,一起去吧,我正要去呢,正好一起过去,那个同学喷着酒气说。老闷那里有免费的白粉,不吸白不吸。
我跟小萍把酒干了,和同学一起往外走。经过哲学博士身边的时候,我在喧闹的人声中凑到哲学博士的耳边,大声问他去不去,哲学博士对我指了指身边的女人,摇头说不跟我们去了。
老闷的房子在河边的一处风景美丽的地方,距离沙特大使馆不远。我们到的时候,party早已经开始了。他的房子有个很大的客厅,里面中间的大圆桌上摆满了酒和饮料,有不少人在屋子的各个角落喝酒聊天。我在门口看见了几个同学,走过去跟他们打招呼,把小萍介绍给他们。聊天的时候,老闷走过来,见了我寒暄了几句话之后,就热情地带我和小萍去参观他的大房子的各个房间,他的室内的大游泳池,和车库里新买的红色跑车。
以后你到沙特去,提我爸的名字,没人不知道我爸的,老闷一边炫耀他的新车一边跟我们说。
老闷最后把我们带到一个书房一样的屋子里,书房的一个圆桌上摆着放在锡纸上的白粉。他递给我一个小黑包,让我们随意,就继续去招呼客人去了。小萍好奇地看着黑包,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我原来参加过老闷家里的party,知道黑包里是一套清洁的针管。我拉开黑包的棕色的拉索,把里面的一个透明的刻着液体刻度的玻璃针管,一个银色的针头和一个弯成九十度的不锈钢勺拿出来摆在桌子上。拿过钢勺来,我让小萍帮着用手捏着勺把,让勺面冲上。我把桌上的锡箔纸包着的白色的粉末抖入一些到勺子的凹进去的勺底,把锡箔纸放回桌上,从桌子上的冰水杯子里往勺子底部滴了几滴水。
小萍的手紧张得有些颤抖。我从小黑包里拿出玻璃针管和针头,针管在灯光下显得壁管很厚,颜色有些浑浊,一头的高光点反射着耀眼的光。针头有十几个厘米长,一头是细长的几个毫米的钢丝一样的针,一头是银色的底座,底座上一个六角形的套筒连着一个圆形的螺旋。我用两只手指捏住银色的六角形套筒,把针头底座上的螺旋对准针管的圆形的顶端,轻轻地插入,然后向右旋转,把针头旋入针管的头上。把组装好的注射器放下,我伸手拿过桌子上的一个黑色的防风打火机,掀开打火机的防风盖,用大拇指向下按动黑色的带着螺纹的小圆石磨,石磨与底下的火石相摩擦,一股细长的火焰从打火机里腾空而起。火焰的底部几乎是透明的,中部是橘红色,上面摇晃的火苗是明黄色。
我把打火机凑近小萍捏着的钢勺的底部,从底下烧灼勺子里的白色粉末。在火焰的热度烘烤下,白色的粉末在勺底开始融化,开始冒出一个一个小气泡,发出滋滋的响声。打火机在勺子底部缓慢地移动着,把所有白末都融化成冒着蒸汽的液体。我用嘴把液体吹凉,然后拿起注射器来,把液体从细细的针头小心翼翼地吸入针管,直到勺子上的液体全部被吸进去,一滴不剩。
先给你打吧,我跟小萍说。
你先来,小萍说。看看你怎么打我再打。
那你帮我勒住点儿胳膊,我把黑包里的一根黑色皮管拿出来递给小萍说。
我把袖子卷起来,让小萍把皮管勒住我的胳膊上部,让血管在肘弯处的皮肤上暴露出来。我举起注射器,用手推动针管外管,把针管里面的空气排挤出去,只剩下浑浊的液体在里面。我用黑包里的一个酒精棉球擦了肘弯的血管一下,把针头对准突出的血管,轻轻扎了进去。肘弯的皮肤在针头的压力之下凹陷了进去,伴随着一阵轻微的疼痛,我看见针头扎入我的血管,血管周围渗出红色的血滴来。一股红色的血液冲进针管,在针管的底部蹿动,像一团蹦紧了的海绵猛然松开一样,刹那间充满了针管的三分之一的底部,跟里面的液体混合起来。我轻轻地推动针管外管,把混合着血的液体推入血管里。拔出针头后,我用一个小棉球堵住了往外渗血珠的血管。
感觉怎么样?小萍问我说。
恶心,晕,我说。
小萍的脸庞在我的眼前逐渐模糊起来。我觉得身子热得像是发了高烧,头脑晕眩,身体开始升腾起来,像是在北极上空飞越一望无际的冰川。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块一块蓝色的浮冰,透明的呈不规则形状的冰块漂浮在蓝色的洋面上,四周耸立着巨大的白色的冰山。屋顶的灯光像是桔黄色的星星,在蓝色的天花板上闪着神秘莫测的光。我感觉透不过气来,无数的金星在眼前旋转,犹如四周下起了黄色的流星雨。流星雨坠落在蓝色的浮冰上,在空中划出一道道转瞬即逝的炫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