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使用一款已经过时的浏览器!部分功能不能正常使用。
请尝试升级或使用 其他浏览器。
请尝试升级或使用 其他浏览器。
精华 蓝色的浮冰
- 主题发起人 让我拥抱你
- 开始时间
- 注册
- 2010-04-24
- 消息
- 33,189
- 荣誉分数
- 17,601
- 声望点数
- 1,373
六十九
我把画架侧对着窗口支上。每次我画画的时候,我都喜欢站在这个地方。因为这里自然光线充足,而且可以看见门外的石桌,矮矮的树篱,石子铺成的小路,暗绿色的松枝,蓝色的或者苍白的天空,眺望到海面上驶过的白帆,还可以看见礁石上屹立的灯塔。窗户的四周结着一些冰,玻璃上也有些哈气,但是这并不妨碍我看见灯塔窗户上的那块残破的砖,因为那一切早已都印在我的脑海里,即使那块砖现在已经被一层厚厚的雪盖住。晚上有时我也坐在这里,听着窗外传来的海水退潮声,看着蓝色的月亮在海面上孤单地升起。月光把树篱,小径,松枝,甚至灯塔,都染上一层神秘的蓝色。那时我会想起月光下一颗火红的树,树叶上泛着蓝光,蓝鸟消失在海上的雾气里,灯塔的红灯扫过海面,那样的一个沉醉的夏夜。
离我不远的地方的棕色沙发上坐着两个女人,她们在专注地叽叽喳喳地聊天,连手边的咖啡都忘记了喝。她们在那里坐了两个小时了,咖啡的热气和香味早已经消失在空气里。每天中午吃完饭,她们都会坐在这里,要一杯咖啡,聊着镇上发生的事。冬天的小镇人们无处去消遣,海面也不适合于捕鱼,男人们在家里看电视或者去酒吧喝酒,女人们找个暖和的地方扎堆聊天,这就是小镇上的生活。她们早已经习惯于看到我坐在窗前画画,没有人惊讶或者想凑过来看一眼,只有在压低声音说到镇里发生的秘密时,她们才会向我的方向瞥来一眼。
我的身后是咖啡馆的柜台,一个十五六岁大,个子跟我差不多高的少年站在柜台里,正在无聊地用搌布擦着盛满咖啡豆的一个玻璃盆。他是一个勤奋的孩子,没有客人的时候,就清理柜台,擦桌子,扫地,总是闲不住。我知道他在等待镇上的一个女孩来,那个女孩经常到咖啡馆来找他,凑在柜台边上跟他说话。我听见女孩有一次跟少年说,想高中毕业后离开这个小镇去H城读书,问少年想不想去。少年憨厚地笑了笑,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我知道女孩喜欢这个少年,因为她看他的时候,眼里总是带着似水的柔情和一种别样的眼神。
十年了。
十年以前这个少年还只是一个很小的小男孩,但已经是一个很懂事的男孩。在那个飓风和海水淹没H城的早上,他趴在四面是水的一颗枫树上,双手绕过树枝紧紧地抓着我的手腕。如果没有他,精疲力竭的我和处在昏迷状态的她可能都被大水冲走了,葬身在那场飓风带来的灾难之中。一架直升飞机在他快拉不住的时候找到了我们,那架飞机是来搜寻掉到海里的大巴上的幸存者的。因为大巴上逃生的一些人报告了市政府组成的紧急抢险队,抢险队了解到大巴翻到海里的情况和大致的位置,派了一家直升飞机来查看附近是否还有水底逃生的幸存者。直升飞机的经验老道的驾驶员看见海边的一幢被淹到屋顶的房子,猜到了房子里或者附近可能有从大巴里逃出来的人,就飞到房顶上空来低空查看,发现了淹在水里的我和她,还有紧紧抓住我的手腕的小男孩。直升飞机把我们救出,送到了一个大体育馆里,那里有义务医生在值班,他们给她打了针,让她的烧退了。我们和其它的避难者一样在体育馆里住了三天三夜,在那里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我们遇见了戒毒所的白大褂,他带着一百多个戒毒所的瘾君子住在体育馆的一个角落。那些瘾君子们安安静静的,互相帮助和照料,没有一个寻衅滋事的。我遇到了那个贩毒的大学生,他在体育馆里当义工,帮助市政府分发食品和饮用水。在一个领饮用水的摊位,他把一瓶瓶纯净水递给排队领水的人。我跟他打了个招呼,要三瓶水,他满面热情地点点头,把纯净水递给我,但像是不认识我一样,又弯腰去给下一位拿水瓶去了。也许他真的认不出我来了:领水的人排着队鱼贯而过,亚洲人的面孔又都相似,在他的眼里,我跟一个陌生人毫无两样。其实我对他现在也只是一个陌生人,他已经不是过去的他,我也不是过去的我了。
在体育馆里我还遇到了那个年轻警察,他带着家人呆在体育馆里无所事事。在体育馆的洗手间里他认出了我,出来后他给了我一包烟,跟我坐在体育馆门口丢弃着乱七八糟的垃圾的台阶上抽烟。我问他怎么在这里,而不是跟其他警察一样忙着维护秩序,他说他辞职了。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呢?现在不是最需要警察的时候吗?他白了我一眼问我说,家和工作哪个更重要?我想了一下说家更重要,工作没了还可以再找,家不能丢。他说你这不是挺明白的吗,警察也是一份工作,我家在海边,能看着老婆孩子淹在水里去维持他妈的什么治安去吗?我争辩说,警察和别的工作不一样,要是警察都像你这样,关键时刻都溜了,那不就乱了吗?他说你当辞职的少啊,我们局里百分之十的警察都辞职了,爱怎么样怎么样,反正我不能让我家里人给淹死。我问他说那天晚上我在大学生的屋子里跳窗逃跑,会不会以后在警察局留下案底,惹来麻烦。开玩笑,年轻警察把一截烟灰弹到一个空罐子里耻笑我说。你这个根本算不了什么,那天我们抓了好几个,够交差的了,你跑了就跑了,没人在意。说实话,那天我们就是吓唬吓唬你,后来想起把你吓得从二楼的窗户跳出去,就觉得很好笑,幸亏你没摔成个残废什么的。你的车应该还在那里,我们既没抄你的车牌,也没人开走。不过现在可能也被水淹了,你该去找保险公司,让他们赔你一辆车。现在大家都在找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这次是赔惨了。我们抽着烟聊了一下各自看见的被淹死的人,感叹了一下生命的短暂和脆弱,把烟蒂弹到不远处的一处水洼里,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尘分手,各自会走各自在体育馆里的角落。临走之前我问他怎么能够尽快地找到小男孩的父母,他告诉我说有一个义务人员组成的寻人登记处,要我到那里去试试看。
我们没有能够找到小男孩的父母。他们失踪了。医院里的人最后见到小男孩母亲的时候,是在医院的院子里,她扶着丈夫的轮椅,和院长站在一起,等待着上最后一辆车。跟随医院最后一辆车逃出来的人说,在飓风带着海水到达的时候,最后一辆车没能载上所有的人。没有人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从那之后再也没人见到过院长和他们,直到今天也没有他们的消息。没有人抱有他们还会生还的希望,虽然他们的名字仍被列在H城失踪的人名单里。也许他们被卷到了海里?也许他们被鲨鱼或者鳄鱼吞噬?在被海水冲走的时候,也许他们心里依旧在惦记着小男孩?在生命垂危的最后的时刻,也许他们很欣慰的庆幸小男孩上了大巴?我想小男孩的母亲是可以自己逃避飓风和海水的,她把小男孩放在大巴上的时候,自己可以留在大巴上。但是她下去了,为了去照顾坐在轮椅上的丈夫。你不能不感叹,世间有些看似平凡的爱情,在生死之际会爆发出炫目的光彩。我总想起看过的那部《美丽人生》电影,当里面的男主角被纳粹押上火车,和其他犹太人一起运往死亡集中营的时候,他太太本不是犹太人,却自愿上了那辆押送犹太人的闷罐一样的火车,跟他一起踏上了死亡之路。
咖啡馆里的音乐换成了一首轻柔的乐曲,我不知道那是一首什么歌,那是柜台后的少年喜欢的一首流行歌曲。我把一张已经画了一多半的画夹上,开始用画笔在上面涂抹起来。红色,黄色和紫色,不同的色块落在了画布上,画面上的人物和背景逐渐清晰起来。我喜欢画美丽的背景,让各种各样的树,房子,街道,篱笆,花和石子充斥画面的每一个角落。雪在外面落着,像是一只漫长的无穷无尽的士兵排成的队伍,冰冷的,严肃的,无声无息地,不断地从灰黑色的云层迈下来,互相压着挤着摞在灯塔下面的一幢灰色的平房的顶上。我在给画面上的背景涂颜色的时候,抬起头,从窗户里想看一眼远处的海面,目光却落到了那个沉默地耸立的平房。外面没有风的呼啸,湿重的鹅毛一样的雪片几乎是笔直地坠下,像是一张羽毛串成的珠帘,让灯塔显得更加朦胧和遥远起来。我茫然地看着被雪雾遮住的平房,目光穿过平房的窗户,走进了宽敞的,聚集着一群穿着黑衣服的人群里。人群在面容严肃地小声地讲着话,有的人在看着我。我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步履沉重地走向前面的花从中的一座棺木,身后跟着个子比我矮很多的小男孩。
三年以前,她的葬礼也是在一个下雪的冬天,在灯塔下的那座充作教堂的平房里举行的。这个小镇太小,没有一个很像样的教堂,只有这一间宽敞的平房,平时是镇上的小学的教室,周末用来举办小镇上的各种活动,星期日在这里做弥撒。葬礼那天早上下着很大的雪,全小镇的人都踏着雪来到了平板房。从平板房的窗户里看去,天空被沉重的阴霾笼罩着,白色的雪片不断地从天上翻落下来,融化在蓝色的波涛里。大海一片平静,沉默得像一块岩石。平房的最前面挂着一张她的放大的相片,相片上的她面容消瘦,眼神凝重,像是在思索什么。这是那次在H城看完医生后,她说我们还没有一起照过一张像,于是我们找到了一家摄影室,在里面拍了几张合影和单人照。照片下是她的棺木,棺材盖打开着,她躺在木质的棺材里,神色安详,嘴唇被化妆师涂得鲜红。一个秃头的挺着大啤酒肚的镇长兼牧师主持了葬礼。他用带着夸张的悲痛的神情和语调,赞颂了她在小镇上所做的一切。镇上的所有的人都喜欢她开的咖啡馆,那个咖啡馆后来变成了一个社交沙龙,镇上的人都喜欢到她的咖啡馆来要一杯浓香的咖啡,聊聊天。学生们在咖啡馆里做作业,主妇们推着放在婴儿车里孩子在咖啡馆里交流育儿心得和八卦镇上的发生的事,男人们打渔归来在这里歇歇脚,镇长在这里拉选民的票。她系着一条绿围裙,在装饰现代的屋里穿梭着,给每个人的桌上送去热气腾腾的咖啡,或者冰镇的饮料。镇长的讲话引起了一片掌声,有的女人被镇长的讲话感动得哭了起来。我站在镇长旁边,眼里湿润着,喉头哽咽着,过去的很多往事一起涌上心头。我尽力压抑着悲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不让别人看出我的难受。当镇长问我想不想讲什么的时候,我摇了摇头,因为我知道我无法开口,一旦开口我就会抑制不住的留下眼泪来。
如果开口,我想说什么呢?
在小镇上的七年时光,她是快乐的吗?我想她是的。她和我都喜欢这个咖啡馆,每天我们在里面忙碌的时候,从来不觉得累。小镇上的民风朴素,经常有小镇上的人从咖啡馆门前路过时,给我们送来几条鲜鱼。她很会熬鱼汤。我把鱼刮鳞清洗干净后,递给她。她把鱼放在锅里,放进祖传的佐料,熬成青色的汤,味道鲜美,胜过宫廷厨师精心制作的御膳。咖啡店里没什么事的时候,我把画架支起来,开始继续画我的漫画。她坐在我的身后看我画画,无论我画成什么样,她都会说喜欢。每个月我们都收到出版社寄来的一张支票和几本样本杂志,金额虽然不大,但是足够铺贴家用的。小镇上的人不多,但是因为经常有外来游客的缘故,而且小镇消费很低,咖啡馆挣的钱和出版社寄来的钱,让我们能在海边过一个舒心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海洛因对她身体造成的损害比我想象的要厉害一些,我带她去医院做年度体检的时候,医生建议她住院治疗,但是她不想在医院里。那时她自己一定已经知道活不了多久,想在海边过一个快乐而宁静的生活,不想待在医院里。小男孩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他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上学上得很好,心地淳朴善良,从很小就知道帮着我们做一些事情。看着小男孩一天天健康快乐的长大,她觉得很开心,空闲的时候,我们领着小男孩一起去海边散步,或者在夜里带着小男孩仰望银河。巨大的蓝色苍穹上,密密麻麻的星星如城市闹市区夜晚的灯火,点缀着不眠的夜空。每天晚上,在小男孩睡觉之后,我们倒一杯红酒,坐在一起看电视或者看租来的电影。我喜欢看电视时触摸着她,无论是她身体的哪一个地方,头发,耳朵,脸颊,肩膀,手臂,乳房,肚子,腿,甚至脚,我都喜欢。我喜欢跟她的亲吻,她的吻总是湿湿的,带着缠绵和热度。只要跟她的身体一接触,我的心里就会燃起欲望,想要她,想把她压在身下,想进入她,占有她,想听她告诉我说她爱我。往往电视还没看完,我们就缠在一起,无法分开。我关上电视,抱着她回到卧室。她搂着我的脖子,温顺得像是一只迷人的小猫。我把她抱到床上,撩开她的头发,把头埋在她的脖子里,呼吸着她的身上的味道,抚摸和亲吻她的全身。她搂着我的身体,敞开两条腿接纳我,要我进到她里面。我们在床上缠绵,用身体诉说着无尽的爱,在一阵阵战栗之间让爱的飓风和浪潮把我们淹没。当我进入她的身体的时候,我看着她的眼睛,看着她的紧促的呼吸,听着她对我说爱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之后我们搂抱在一起,呢喃着爱的细语,倾诉着心底的感觉,探讨着往世今生,在蓝色的月光下和窗外的一阵阵涛声中紧紧搂着入眠。世界上有没有人会永远相爱呢?她有一次枕着我的胳膊问我说。有,我亲了一下她的鼻子说。我们就是,我们会永远相爱,直到有一天离开人世。
小镇上没有焚化炉,死去的人都还像是过去一样,被放在棺材里,埋在墓地里。墓地挨着一座小山,离平房有几分钟的车程。我和几个人把她的棺材抬到一辆皮卡上,雪不断地落下来,落到了每个抬棺人的肩膀上。皮卡缓慢地开动了,后面跟着一溜车。我开车跟在皮卡后面,经过小镇上的咖啡馆时,似乎透过玻璃窗看见了她在咖啡馆里忙碌的身影,看见她在招呼客人,把一杯杯香浓的冒着热气的咖啡递到客人手中。
我站在飘着大雪的墓地棺木的旁边,木然地伫立着,心里很空落。送葬的人们散在四周,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悲痛的神情,空气里飘动着阴郁忧伤的气氛,连雪花也悄悄地停住下坠,悬在半空中。看着自己所爱的人被钉在棺木里,棺木缓缓下沉,放到了坑底,那样一种心情,好象是眼前的一切都不是真实发生的一样。当最后一锹土盖住了棺木的时候,我觉得风呼啸着卷着雪花穿过了心口,好像那里一下子都空了一样。
她走了。带着微笑走了。
但是我知道她给我留下了什么:记忆。无法失去的清晰的记忆。每当我拿起画笔来,我就能感觉到身后有一双温暖的眼睛在看着我,能看到她脸上的舒心的微笑。她知道我喜欢画画,当我画画的时候,心里是快乐的。只要你快乐,我就很快乐;只要你幸福,我就很幸福,她曾经对我说。在我落下画笔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过去,回到了跟她在一起的温馨的时光。我无法留住她的身体,但是我可以把她留在画里。她走后的三年以来,我每天都在画,每天让她都在我的画里出现,陪着我。我在画里倾听她的话语,带她去她想去的地方,做她想做的事情,说她想说的话,让她在画里总是那样的年轻,美丽,轻盈,像是一只翩翩飞起的蝴蝶。
画布在我的眼前动了起来,我看到风儿和他的心爱的女孩从画面上走下来,手里牵着一个可爱的小男孩,走出门口,沿着鹅卵石铺成的小径,走向了海边的沙滩。在一棵紫色的树下,他们停驻脚步,对视了一眼。风儿亲吻了一下女孩,女孩伸手抚摸了一下风儿的头发,小孩仰着头看着他们。花瓣从树上纷纷飘落,落了他们一身。他们领着小孩继续前行,背影渐渐从我的眼中消失了。
把画笔停顿下来,我疲惫地审视了一下画板上的画,在画的右下角签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
这是最后的一幅画。我终于完成了这一套《风儿》连续漫画。这套漫画并没有像我一开始画的时候想得那样好,中间还发生了许多转折,甚至无法继续画下去。它情节散漫,结构也有些凌乱,前后甚至还有些脱节,想来也不会有很多人喜欢。
但是我把它画完了,就像漫长的生命旅途中,你疲惫不堪地到达了终点,终于可以停下脚步来说,是结束的时候了。
我把画架侧对着窗口支上。每次我画画的时候,我都喜欢站在这个地方。因为这里自然光线充足,而且可以看见门外的石桌,矮矮的树篱,石子铺成的小路,暗绿色的松枝,蓝色的或者苍白的天空,眺望到海面上驶过的白帆,还可以看见礁石上屹立的灯塔。窗户的四周结着一些冰,玻璃上也有些哈气,但是这并不妨碍我看见灯塔窗户上的那块残破的砖,因为那一切早已都印在我的脑海里,即使那块砖现在已经被一层厚厚的雪盖住。晚上有时我也坐在这里,听着窗外传来的海水退潮声,看着蓝色的月亮在海面上孤单地升起。月光把树篱,小径,松枝,甚至灯塔,都染上一层神秘的蓝色。那时我会想起月光下一颗火红的树,树叶上泛着蓝光,蓝鸟消失在海上的雾气里,灯塔的红灯扫过海面,那样的一个沉醉的夏夜。
离我不远的地方的棕色沙发上坐着两个女人,她们在专注地叽叽喳喳地聊天,连手边的咖啡都忘记了喝。她们在那里坐了两个小时了,咖啡的热气和香味早已经消失在空气里。每天中午吃完饭,她们都会坐在这里,要一杯咖啡,聊着镇上发生的事。冬天的小镇人们无处去消遣,海面也不适合于捕鱼,男人们在家里看电视或者去酒吧喝酒,女人们找个暖和的地方扎堆聊天,这就是小镇上的生活。她们早已经习惯于看到我坐在窗前画画,没有人惊讶或者想凑过来看一眼,只有在压低声音说到镇里发生的秘密时,她们才会向我的方向瞥来一眼。
我的身后是咖啡馆的柜台,一个十五六岁大,个子跟我差不多高的少年站在柜台里,正在无聊地用搌布擦着盛满咖啡豆的一个玻璃盆。他是一个勤奋的孩子,没有客人的时候,就清理柜台,擦桌子,扫地,总是闲不住。我知道他在等待镇上的一个女孩来,那个女孩经常到咖啡馆来找他,凑在柜台边上跟他说话。我听见女孩有一次跟少年说,想高中毕业后离开这个小镇去H城读书,问少年想不想去。少年憨厚地笑了笑,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我知道女孩喜欢这个少年,因为她看他的时候,眼里总是带着似水的柔情和一种别样的眼神。
十年了。
十年以前这个少年还只是一个很小的小男孩,但已经是一个很懂事的男孩。在那个飓风和海水淹没H城的早上,他趴在四面是水的一颗枫树上,双手绕过树枝紧紧地抓着我的手腕。如果没有他,精疲力竭的我和处在昏迷状态的她可能都被大水冲走了,葬身在那场飓风带来的灾难之中。一架直升飞机在他快拉不住的时候找到了我们,那架飞机是来搜寻掉到海里的大巴上的幸存者的。因为大巴上逃生的一些人报告了市政府组成的紧急抢险队,抢险队了解到大巴翻到海里的情况和大致的位置,派了一家直升飞机来查看附近是否还有水底逃生的幸存者。直升飞机的经验老道的驾驶员看见海边的一幢被淹到屋顶的房子,猜到了房子里或者附近可能有从大巴里逃出来的人,就飞到房顶上空来低空查看,发现了淹在水里的我和她,还有紧紧抓住我的手腕的小男孩。直升飞机把我们救出,送到了一个大体育馆里,那里有义务医生在值班,他们给她打了针,让她的烧退了。我们和其它的避难者一样在体育馆里住了三天三夜,在那里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我们遇见了戒毒所的白大褂,他带着一百多个戒毒所的瘾君子住在体育馆的一个角落。那些瘾君子们安安静静的,互相帮助和照料,没有一个寻衅滋事的。我遇到了那个贩毒的大学生,他在体育馆里当义工,帮助市政府分发食品和饮用水。在一个领饮用水的摊位,他把一瓶瓶纯净水递给排队领水的人。我跟他打了个招呼,要三瓶水,他满面热情地点点头,把纯净水递给我,但像是不认识我一样,又弯腰去给下一位拿水瓶去了。也许他真的认不出我来了:领水的人排着队鱼贯而过,亚洲人的面孔又都相似,在他的眼里,我跟一个陌生人毫无两样。其实我对他现在也只是一个陌生人,他已经不是过去的他,我也不是过去的我了。
在体育馆里我还遇到了那个年轻警察,他带着家人呆在体育馆里无所事事。在体育馆的洗手间里他认出了我,出来后他给了我一包烟,跟我坐在体育馆门口丢弃着乱七八糟的垃圾的台阶上抽烟。我问他怎么在这里,而不是跟其他警察一样忙着维护秩序,他说他辞职了。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呢?现在不是最需要警察的时候吗?他白了我一眼问我说,家和工作哪个更重要?我想了一下说家更重要,工作没了还可以再找,家不能丢。他说你这不是挺明白的吗,警察也是一份工作,我家在海边,能看着老婆孩子淹在水里去维持他妈的什么治安去吗?我争辩说,警察和别的工作不一样,要是警察都像你这样,关键时刻都溜了,那不就乱了吗?他说你当辞职的少啊,我们局里百分之十的警察都辞职了,爱怎么样怎么样,反正我不能让我家里人给淹死。我问他说那天晚上我在大学生的屋子里跳窗逃跑,会不会以后在警察局留下案底,惹来麻烦。开玩笑,年轻警察把一截烟灰弹到一个空罐子里耻笑我说。你这个根本算不了什么,那天我们抓了好几个,够交差的了,你跑了就跑了,没人在意。说实话,那天我们就是吓唬吓唬你,后来想起把你吓得从二楼的窗户跳出去,就觉得很好笑,幸亏你没摔成个残废什么的。你的车应该还在那里,我们既没抄你的车牌,也没人开走。不过现在可能也被水淹了,你该去找保险公司,让他们赔你一辆车。现在大家都在找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这次是赔惨了。我们抽着烟聊了一下各自看见的被淹死的人,感叹了一下生命的短暂和脆弱,把烟蒂弹到不远处的一处水洼里,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尘分手,各自会走各自在体育馆里的角落。临走之前我问他怎么能够尽快地找到小男孩的父母,他告诉我说有一个义务人员组成的寻人登记处,要我到那里去试试看。
我们没有能够找到小男孩的父母。他们失踪了。医院里的人最后见到小男孩母亲的时候,是在医院的院子里,她扶着丈夫的轮椅,和院长站在一起,等待着上最后一辆车。跟随医院最后一辆车逃出来的人说,在飓风带着海水到达的时候,最后一辆车没能载上所有的人。没有人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从那之后再也没人见到过院长和他们,直到今天也没有他们的消息。没有人抱有他们还会生还的希望,虽然他们的名字仍被列在H城失踪的人名单里。也许他们被卷到了海里?也许他们被鲨鱼或者鳄鱼吞噬?在被海水冲走的时候,也许他们心里依旧在惦记着小男孩?在生命垂危的最后的时刻,也许他们很欣慰的庆幸小男孩上了大巴?我想小男孩的母亲是可以自己逃避飓风和海水的,她把小男孩放在大巴上的时候,自己可以留在大巴上。但是她下去了,为了去照顾坐在轮椅上的丈夫。你不能不感叹,世间有些看似平凡的爱情,在生死之际会爆发出炫目的光彩。我总想起看过的那部《美丽人生》电影,当里面的男主角被纳粹押上火车,和其他犹太人一起运往死亡集中营的时候,他太太本不是犹太人,却自愿上了那辆押送犹太人的闷罐一样的火车,跟他一起踏上了死亡之路。
咖啡馆里的音乐换成了一首轻柔的乐曲,我不知道那是一首什么歌,那是柜台后的少年喜欢的一首流行歌曲。我把一张已经画了一多半的画夹上,开始用画笔在上面涂抹起来。红色,黄色和紫色,不同的色块落在了画布上,画面上的人物和背景逐渐清晰起来。我喜欢画美丽的背景,让各种各样的树,房子,街道,篱笆,花和石子充斥画面的每一个角落。雪在外面落着,像是一只漫长的无穷无尽的士兵排成的队伍,冰冷的,严肃的,无声无息地,不断地从灰黑色的云层迈下来,互相压着挤着摞在灯塔下面的一幢灰色的平房的顶上。我在给画面上的背景涂颜色的时候,抬起头,从窗户里想看一眼远处的海面,目光却落到了那个沉默地耸立的平房。外面没有风的呼啸,湿重的鹅毛一样的雪片几乎是笔直地坠下,像是一张羽毛串成的珠帘,让灯塔显得更加朦胧和遥远起来。我茫然地看着被雪雾遮住的平房,目光穿过平房的窗户,走进了宽敞的,聚集着一群穿着黑衣服的人群里。人群在面容严肃地小声地讲着话,有的人在看着我。我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步履沉重地走向前面的花从中的一座棺木,身后跟着个子比我矮很多的小男孩。
三年以前,她的葬礼也是在一个下雪的冬天,在灯塔下的那座充作教堂的平房里举行的。这个小镇太小,没有一个很像样的教堂,只有这一间宽敞的平房,平时是镇上的小学的教室,周末用来举办小镇上的各种活动,星期日在这里做弥撒。葬礼那天早上下着很大的雪,全小镇的人都踏着雪来到了平板房。从平板房的窗户里看去,天空被沉重的阴霾笼罩着,白色的雪片不断地从天上翻落下来,融化在蓝色的波涛里。大海一片平静,沉默得像一块岩石。平房的最前面挂着一张她的放大的相片,相片上的她面容消瘦,眼神凝重,像是在思索什么。这是那次在H城看完医生后,她说我们还没有一起照过一张像,于是我们找到了一家摄影室,在里面拍了几张合影和单人照。照片下是她的棺木,棺材盖打开着,她躺在木质的棺材里,神色安详,嘴唇被化妆师涂得鲜红。一个秃头的挺着大啤酒肚的镇长兼牧师主持了葬礼。他用带着夸张的悲痛的神情和语调,赞颂了她在小镇上所做的一切。镇上的所有的人都喜欢她开的咖啡馆,那个咖啡馆后来变成了一个社交沙龙,镇上的人都喜欢到她的咖啡馆来要一杯浓香的咖啡,聊聊天。学生们在咖啡馆里做作业,主妇们推着放在婴儿车里孩子在咖啡馆里交流育儿心得和八卦镇上的发生的事,男人们打渔归来在这里歇歇脚,镇长在这里拉选民的票。她系着一条绿围裙,在装饰现代的屋里穿梭着,给每个人的桌上送去热气腾腾的咖啡,或者冰镇的饮料。镇长的讲话引起了一片掌声,有的女人被镇长的讲话感动得哭了起来。我站在镇长旁边,眼里湿润着,喉头哽咽着,过去的很多往事一起涌上心头。我尽力压抑着悲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不让别人看出我的难受。当镇长问我想不想讲什么的时候,我摇了摇头,因为我知道我无法开口,一旦开口我就会抑制不住的留下眼泪来。
如果开口,我想说什么呢?
在小镇上的七年时光,她是快乐的吗?我想她是的。她和我都喜欢这个咖啡馆,每天我们在里面忙碌的时候,从来不觉得累。小镇上的民风朴素,经常有小镇上的人从咖啡馆门前路过时,给我们送来几条鲜鱼。她很会熬鱼汤。我把鱼刮鳞清洗干净后,递给她。她把鱼放在锅里,放进祖传的佐料,熬成青色的汤,味道鲜美,胜过宫廷厨师精心制作的御膳。咖啡店里没什么事的时候,我把画架支起来,开始继续画我的漫画。她坐在我的身后看我画画,无论我画成什么样,她都会说喜欢。每个月我们都收到出版社寄来的一张支票和几本样本杂志,金额虽然不大,但是足够铺贴家用的。小镇上的人不多,但是因为经常有外来游客的缘故,而且小镇消费很低,咖啡馆挣的钱和出版社寄来的钱,让我们能在海边过一个舒心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海洛因对她身体造成的损害比我想象的要厉害一些,我带她去医院做年度体检的时候,医生建议她住院治疗,但是她不想在医院里。那时她自己一定已经知道活不了多久,想在海边过一个快乐而宁静的生活,不想待在医院里。小男孩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他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上学上得很好,心地淳朴善良,从很小就知道帮着我们做一些事情。看着小男孩一天天健康快乐的长大,她觉得很开心,空闲的时候,我们领着小男孩一起去海边散步,或者在夜里带着小男孩仰望银河。巨大的蓝色苍穹上,密密麻麻的星星如城市闹市区夜晚的灯火,点缀着不眠的夜空。每天晚上,在小男孩睡觉之后,我们倒一杯红酒,坐在一起看电视或者看租来的电影。我喜欢看电视时触摸着她,无论是她身体的哪一个地方,头发,耳朵,脸颊,肩膀,手臂,乳房,肚子,腿,甚至脚,我都喜欢。我喜欢跟她的亲吻,她的吻总是湿湿的,带着缠绵和热度。只要跟她的身体一接触,我的心里就会燃起欲望,想要她,想把她压在身下,想进入她,占有她,想听她告诉我说她爱我。往往电视还没看完,我们就缠在一起,无法分开。我关上电视,抱着她回到卧室。她搂着我的脖子,温顺得像是一只迷人的小猫。我把她抱到床上,撩开她的头发,把头埋在她的脖子里,呼吸着她的身上的味道,抚摸和亲吻她的全身。她搂着我的身体,敞开两条腿接纳我,要我进到她里面。我们在床上缠绵,用身体诉说着无尽的爱,在一阵阵战栗之间让爱的飓风和浪潮把我们淹没。当我进入她的身体的时候,我看着她的眼睛,看着她的紧促的呼吸,听着她对我说爱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之后我们搂抱在一起,呢喃着爱的细语,倾诉着心底的感觉,探讨着往世今生,在蓝色的月光下和窗外的一阵阵涛声中紧紧搂着入眠。世界上有没有人会永远相爱呢?她有一次枕着我的胳膊问我说。有,我亲了一下她的鼻子说。我们就是,我们会永远相爱,直到有一天离开人世。
小镇上没有焚化炉,死去的人都还像是过去一样,被放在棺材里,埋在墓地里。墓地挨着一座小山,离平房有几分钟的车程。我和几个人把她的棺材抬到一辆皮卡上,雪不断地落下来,落到了每个抬棺人的肩膀上。皮卡缓慢地开动了,后面跟着一溜车。我开车跟在皮卡后面,经过小镇上的咖啡馆时,似乎透过玻璃窗看见了她在咖啡馆里忙碌的身影,看见她在招呼客人,把一杯杯香浓的冒着热气的咖啡递到客人手中。
我站在飘着大雪的墓地棺木的旁边,木然地伫立着,心里很空落。送葬的人们散在四周,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悲痛的神情,空气里飘动着阴郁忧伤的气氛,连雪花也悄悄地停住下坠,悬在半空中。看着自己所爱的人被钉在棺木里,棺木缓缓下沉,放到了坑底,那样一种心情,好象是眼前的一切都不是真实发生的一样。当最后一锹土盖住了棺木的时候,我觉得风呼啸着卷着雪花穿过了心口,好像那里一下子都空了一样。
她走了。带着微笑走了。
但是我知道她给我留下了什么:记忆。无法失去的清晰的记忆。每当我拿起画笔来,我就能感觉到身后有一双温暖的眼睛在看着我,能看到她脸上的舒心的微笑。她知道我喜欢画画,当我画画的时候,心里是快乐的。只要你快乐,我就很快乐;只要你幸福,我就很幸福,她曾经对我说。在我落下画笔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过去,回到了跟她在一起的温馨的时光。我无法留住她的身体,但是我可以把她留在画里。她走后的三年以来,我每天都在画,每天让她都在我的画里出现,陪着我。我在画里倾听她的话语,带她去她想去的地方,做她想做的事情,说她想说的话,让她在画里总是那样的年轻,美丽,轻盈,像是一只翩翩飞起的蝴蝶。
画布在我的眼前动了起来,我看到风儿和他的心爱的女孩从画面上走下来,手里牵着一个可爱的小男孩,走出门口,沿着鹅卵石铺成的小径,走向了海边的沙滩。在一棵紫色的树下,他们停驻脚步,对视了一眼。风儿亲吻了一下女孩,女孩伸手抚摸了一下风儿的头发,小孩仰着头看着他们。花瓣从树上纷纷飘落,落了他们一身。他们领着小孩继续前行,背影渐渐从我的眼中消失了。
把画笔停顿下来,我疲惫地审视了一下画板上的画,在画的右下角签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
这是最后的一幅画。我终于完成了这一套《风儿》连续漫画。这套漫画并没有像我一开始画的时候想得那样好,中间还发生了许多转折,甚至无法继续画下去。它情节散漫,结构也有些凌乱,前后甚至还有些脱节,想来也不会有很多人喜欢。
但是我把它画完了,就像漫长的生命旅途中,你疲惫不堪地到达了终点,终于可以停下脚步来说,是结束的时候了。
- 注册
- 2010-04-24
- 消息
- 33,189
- 荣誉分数
- 17,601
- 声望点数
- 1,373
七十
圣诞节的时候,小镇上突然热闹了起来。不断有旅游团的大巴带着各地的游客途径这里前往各个风景旅游点,在这个虽然说不上多么美,但是有灯塔有礁石有海滩有餐馆有洗手间的地方停下来休息。从车上下来各种肤色,穿着各种衣服,讲着各种语言的人。他们在灯塔边摆好姿势拍照,在岩石上茫然地眺望大海,在餐馆里长着嘴闭着嘴咀嚼当地的海鲜。也经常有人迈进咖啡馆里来,点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坐在小圆桌前品尝一下咖啡馆里自制的甜点。
一个说不上是晴天也说不上是阴天的下午,少年站在咖啡馆的柜台后面,低头用搌布擦着柜台上的玻璃。玻璃橱窗下面摆放着大大小小的碟子,里面摆放着当天做出来的样式精致的甜点。少年的眼睛不时地瞥一眼门口,在等着他喜欢的那个女孩出现。那个女孩每天总是放学后到咖啡馆来,趴在柜台边上跟他聊一会儿天,然后坐在靠窗的一个小桌子上,读书或者做作业。有她在的时候,即使外面很冷,即使天空布满了阴霾,少年总是感觉到屋里很温暖,很阳光,心里也快乐起来。
门口的铃铛叮咚响了一声,少年抬起头,看见从挂着彩灯贴着圣诞老人的图像的门口,走进来一个女人。女人穿着一件长到膝盖的乳白色掐腰羽绒服,左手牵着一个像是八岁左右的小女孩,右手臂上挎着一个精致的路易维登白色手包,腿上是一件厚实的蓝色牛仔裤,裤腿的下端塞在一双半高腰的黑色长筒靴里。女人的身后是一个穿着一件厚厚的黑色羽绒服,肩膀宽阔,脸上显得有些沧桑,但给人一种安全感,看上去很成熟的男人。男人的粗壮有力的手推着门,让女人和小孩走进屋里。阳光和冷风一起从门口钻进来,有些昏暗的咖啡屋顿时变得明亮一些起来。
少年知道,他们一定是从刚才在门口开过去的那辆蓝灰色的涂着灰狗标记的旅游大巴上下来的游客。那辆轮子上沾满雪泥的灰狗大巴疲累地停在咖啡馆前面不远的地方,像是一个历经风霜的老人,靠在路边休息。从敞开的屋门里,依然可以听见导游在喊着什么,看见背着背包的游客们在上下大巴。有的游客站在路边甩动着胳膊和腿脚,有的在眺望着海面,有的走进前面的一个餐馆去上洗手间。
咖啡馆的门关上了,男人,女人和小孩一起走进屋来。他们在门口跺跺脚,让脚上沾染的雪落在门口的垫子之上。女人走到柜台前面,仰头看着柜台上方的价格表。小女孩拉着女人的手,两只好奇的眼睛盯着玻璃柜台里的样式诱人的甜点。男人沉默着站在女人的后面,漠然地看着屋内的摆设。少年看着他们,没有说话。他知道要给他们一点时间来挑自己喜欢的。
你要喝点儿什么?女人回头问男人。
什么都行,只要不是咖啡,男人说。这么多年了,一直喝不惯咖啡,一喝咖啡就睡不着觉。
这里有绿茶,给你来一杯热茶怎么样?女人依旧看着价目表,征询着男人的意见。
绿茶好,男人面无表情地说。不要冰块。
妈妈,我要这个。小女孩拽着女人的乳白色的羽绒服,胖胖的小手指隔着玻璃窗点着柜台里陈放着的一块巧克力慕斯奶油蛋糕说。
劳驾给我们来一杯摩卡,一杯绿茶,要热的,一碟巧克力慕斯蛋糕,和一杯纯果汁,女人对少年说。
摩卡里要cream吗?少年问女人。
Yes,please,女人点头说。
一共$18.5,少年的手灵巧地敲击着键盘。
男人从兜里掏出钱包,取出一张卡,递给少年。少年接过来,低头在机器上刷卡。女人的眼睛环视四周,看见了窗前的那个画架。
你画画吗?女人的眼睛瞥了一眼画架问少年。
不,少年抬头说。那是我爸的。你们随便坐吧,一会儿我把饮料和蛋糕给你们端过去。
谢谢,女人微笑着说。
女人领着小女孩走到窗边,脱下外面的羽绒服,在画架旁边的桌子坐下。男人从少年手里接过信用卡,跟着走过去,坐在女人对面。
外面天干冷干冷的,男人搓着手说。好在屋子里还暖和一些。
小镇不错,女人看着窗外的灯塔说。安静,也美。
是不错,男人顺着女人的目光看着窗外说。
男人和女人看着窗外,一时失去了话语。他们沉默地坐着,像是相处太久,久得都无话可说了一样。即使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双方也懒得交谈什么。小女孩依偎着女人的膝盖,玩着女人的羽绒服上的一个扣子。
可是你更喜欢大城市,对吗?过了几分钟,男人最终打破了沉默,没话找话地问女人说。
原来在W城的时候,就觉得不习惯,女人带着感慨说。现在就更觉得不习惯了。从小在大城市里长大,到了W城就像是到了乡村似的感觉。
我爸爸原来也是在W城。少年把盛放着热咖啡,茶,蛋糕和果汁的托盘放到女人面前的小圆桌上说。你们是从中国来的吗?他也是从中国来的。
Oh, ya? 女人说。他是哪里人?
北京人。
可你身上一点也看不出。。。有亚洲人的血缘,女人用眼睛上下打量着少年说。
我是领养的,少年把切蛋糕的刀叉摆放在桌上说。十年以前,H城曾经来过一次飓风,发过一次大水,我亲生父母在飓风里丧生,是我爸妈领养了我,带着我来到这里。
十年前。。。飓风。。。女人眯着眼睛思索着。
突然像是想起来了什么似的,女人扬起眉毛来,问少年说:是卡洛斯飓风吗?
就是,少年说。我当时还小,不知道飓风的名字,后来我爸告诉了我,我还去查过一些资料。那次飓风比预报的要大,H城死了有一千多人,失踪了几十人,我亲生父母就在失踪的名单里面。
太可怜了,女人带着同情的眼光看着少年说。
也没什么,我爸妈对我很好的,比我亲生父母还好。少年对着他们微笑了一下,转身走回了柜台。
你怎么对一个飓风记得这么清楚呢?男人喝了一口热茶,问女人说。
那时我正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女人想了一下说。上飞机的时候听说飓风要登陆H城,到了北京,电视新闻里已经到处是H城的新闻,镜头上到处是飓风吹倒大树,掀开房顶,摧毁防洪堤,海水淹没H城的新闻,印象特别深刻。
妈妈我要吃蛋糕,小女孩打断了女人的话说。
女人左手用叉子扎住蛋糕,右手用餐具刀把蛋糕切成小块,让小女孩扎着吃。小女孩一边吃一边缠着女人问这问那,女人耐心地回答着小女孩的问题,看着小女孩把蛋糕都吃完,把果汁给喝了。
我们该走了。男人看了一下手表说。大巴快该出发了。
男人喝光了杯子里的最后的茶,把茶杯咖啡杯蛋糕盘收拾好,端着托盘,向着柜台走去,把托盘放在柜台边的一个台子上。女人站起身来,穿上乳白色的羽绒服,领着小女孩的手向着门口走去。在经过画架的时候,女人不经意地看了一眼画架上的画,突然怔住了。她停下脚步,仔细地看着画上的画,又看了一眼画面右下角的签名,身子微微的颤抖起来。
这是你父亲的画吗?女人扭过头来问柜台边低头忙碌的少年说。
他最后的一幅画,少年抬起头来说。
最后一幅画?他现在在哪里?女人问少年。
男人已经走到了门边。他不解地瞥了女人一眼,立在门边,把手放在门的把手上,眼睛看着表,有些不耐烦地等着女人。
一个月前他去世了,少年看着画架说。他画完这幅画后,晚上到前面的一个酒吧喝了一瓶酒,出门的时候,晕倒在雪地里。当时没有人看见他,他就冻死了。医生说,他以前也曾经喝多了酒晕倒过,但是过去都有人看见,就没出危险。
女人惊呆了。她楞楞地站在画架前面,像是内心在掀起一阵风暴的狂澜一样,脸色由红润一下变得苍白,像是全身的血液都挥发到空气里一样。她身体颤栗了一下,随后手扶着画架,让身子伫立在画架前,仔细地端详着画上的人物。她的眼里湿润了起来。小女孩挣脱了她的手,向着门口的男人跑去。
你还在磨蹭什么呢?男人催促着女人说。一个小镇上的业余画家的画有什么可看的,你要喜欢看画,夏天我带你去法国,去卢浮宫看去,那才过瘾------
我能买这幅画吗?女人不理男人的唠叨,从画面上抬起头问少年说。
你真疯了,男人不满地嘟囔说。赶紧走吧,别在这里耽误时间了,这破画也值得买。
你有完没完?女人对着男人吼了一声。
男人不出声了,把手从门把手上缩回来,拉着小女孩的手在门边站着。少年不知所措地看着男人和女人,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突然一下吵起来。他不太懂,有的夫妻看着很好很相配,对别人也都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但是他们自己说起话来却连陌生人都不如。
对不起,我想买这幅画。女人压下声音来,和颜悦色地对少年说。告诉我一个价钱,多少都行。
这画不能卖,少年带着一些抱歉说。这是我爸留下的唯一一幅亲笔画,以前他的画都给出版社了。这一幅还没来得及寄出去。我没告诉出版社,想留着它给自己做个纪念。
你刚才是说他一个月前才去世的吗?
还不到一个月,少年说。给他订的墓碑刚给运来,昨天才放在墓地上。
真是命啊,女人小声地嘟囔了一声。我怎么没有早点儿来?
什么?少年不解地问了一句。
哦,没什么,我是说要不是有件事耽搁了一下,一个月前我就该到这里了,女人带着一种悲伤的神情说。他的墓地在哪里?我能去看看吗?
可以,不是很远,在前面的小山边,少年伸手指着窗外隐约可见的一片青色的小山说。开车要几分钟,走着要二十分钟吧。你要是想去,我可以开车带你去,反正现在店里也没人,有个一刻钟就够来回的了。
大巴该开走了。男人明显的不耐烦地推开门,眼睛看着墙上的电子钟说。你走不走?不走我走了,一车上的人都等着我们呢。出门就磨蹭,到这里又磨蹭,早知这样我不跟着出来了。
少年看了男人一眼,不解男人哪里来的这么大的火气。难道她不是你的太太吗?难道你对她不能耐心一点儿,好好的说话吗?少年想。
妈妈,快走吧,去晚了车上的叔叔阿姨们又该说我们了。小女孩跑过来摇晃着女人的手说。
门外的阳光和冷风一起吹进来,不远处传来灰狗大巴导游在招呼游客们上车的声音。墙上的电子表的秒针在滴答地响着,像是在催促着依旧站在画架之前的女人离去。女人突然像是控制不住自己了一样,在画前闭上了眼睛,再睁开的时候,眼睛里掉出一滴晶莹的泪水来。她没有再跟少年讲话,也没有搭理男人,只是最后看了一眼画架,被小女孩拉着,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咖啡馆的大门。
咖啡馆的贴着圣诞图像的大门重新关上,乳白色的长羽绒服和白色的路易维登包随着脚步声一起消失了,屋内重新回到了一片静穆之中。少年走到画架之前,看着画上被泪水浸湿的一个逐渐扩大的圆点,思索着。他想不清楚那个女人为何掉下眼泪来,但是显然,这幅画勾起了女人的一些回忆。秒针在一秒一秒地走着,少年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觉得读懂了女人沉默的外表下心里所起的狂澜,以及女人最后留在画架上的悲伤。少年把画从画架上拿下来,卷起,推开了咖啡馆的屋门,向着不远处的灰狗大巴快步走去。
大巴在一声沉重的哀鸣之中,关上了门,轮子开始在雪地上移动,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在地上碾出一道道硬硬的轮胎痕迹。少年看见灰狗大巴昏暗的车厢里,一个乳白色的羽绒服站了起来,从车厢后部走向前部。阳光流泻在少年身上,他沿着铺满白雪的街道快速地跑着,不知道大巴是否会停下来等他一下。大巴驶进了一片树从的阴影之中,他甚至看不见车厢里面的乳白色的羽绒服了。但是他知道,乳白色的羽绒服一定看见了他,也知道他在为什么追着大巴。树丛从他的身边向后倒去,阳光晃着他的眼睛,让他看不清前面的路。他眯着眼一边跑,一边不断地向大巴挥舞着手里卷起来的画,像是挥舞着一把闪闪发光的宝剑。
【全文完】
圣诞节的时候,小镇上突然热闹了起来。不断有旅游团的大巴带着各地的游客途径这里前往各个风景旅游点,在这个虽然说不上多么美,但是有灯塔有礁石有海滩有餐馆有洗手间的地方停下来休息。从车上下来各种肤色,穿着各种衣服,讲着各种语言的人。他们在灯塔边摆好姿势拍照,在岩石上茫然地眺望大海,在餐馆里长着嘴闭着嘴咀嚼当地的海鲜。也经常有人迈进咖啡馆里来,点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坐在小圆桌前品尝一下咖啡馆里自制的甜点。
一个说不上是晴天也说不上是阴天的下午,少年站在咖啡馆的柜台后面,低头用搌布擦着柜台上的玻璃。玻璃橱窗下面摆放着大大小小的碟子,里面摆放着当天做出来的样式精致的甜点。少年的眼睛不时地瞥一眼门口,在等着他喜欢的那个女孩出现。那个女孩每天总是放学后到咖啡馆来,趴在柜台边上跟他聊一会儿天,然后坐在靠窗的一个小桌子上,读书或者做作业。有她在的时候,即使外面很冷,即使天空布满了阴霾,少年总是感觉到屋里很温暖,很阳光,心里也快乐起来。
门口的铃铛叮咚响了一声,少年抬起头,看见从挂着彩灯贴着圣诞老人的图像的门口,走进来一个女人。女人穿着一件长到膝盖的乳白色掐腰羽绒服,左手牵着一个像是八岁左右的小女孩,右手臂上挎着一个精致的路易维登白色手包,腿上是一件厚实的蓝色牛仔裤,裤腿的下端塞在一双半高腰的黑色长筒靴里。女人的身后是一个穿着一件厚厚的黑色羽绒服,肩膀宽阔,脸上显得有些沧桑,但给人一种安全感,看上去很成熟的男人。男人的粗壮有力的手推着门,让女人和小孩走进屋里。阳光和冷风一起从门口钻进来,有些昏暗的咖啡屋顿时变得明亮一些起来。
少年知道,他们一定是从刚才在门口开过去的那辆蓝灰色的涂着灰狗标记的旅游大巴上下来的游客。那辆轮子上沾满雪泥的灰狗大巴疲累地停在咖啡馆前面不远的地方,像是一个历经风霜的老人,靠在路边休息。从敞开的屋门里,依然可以听见导游在喊着什么,看见背着背包的游客们在上下大巴。有的游客站在路边甩动着胳膊和腿脚,有的在眺望着海面,有的走进前面的一个餐馆去上洗手间。
咖啡馆的门关上了,男人,女人和小孩一起走进屋来。他们在门口跺跺脚,让脚上沾染的雪落在门口的垫子之上。女人走到柜台前面,仰头看着柜台上方的价格表。小女孩拉着女人的手,两只好奇的眼睛盯着玻璃柜台里的样式诱人的甜点。男人沉默着站在女人的后面,漠然地看着屋内的摆设。少年看着他们,没有说话。他知道要给他们一点时间来挑自己喜欢的。
你要喝点儿什么?女人回头问男人。
什么都行,只要不是咖啡,男人说。这么多年了,一直喝不惯咖啡,一喝咖啡就睡不着觉。
这里有绿茶,给你来一杯热茶怎么样?女人依旧看着价目表,征询着男人的意见。
绿茶好,男人面无表情地说。不要冰块。
妈妈,我要这个。小女孩拽着女人的乳白色的羽绒服,胖胖的小手指隔着玻璃窗点着柜台里陈放着的一块巧克力慕斯奶油蛋糕说。
劳驾给我们来一杯摩卡,一杯绿茶,要热的,一碟巧克力慕斯蛋糕,和一杯纯果汁,女人对少年说。
摩卡里要cream吗?少年问女人。
Yes,please,女人点头说。
一共$18.5,少年的手灵巧地敲击着键盘。
男人从兜里掏出钱包,取出一张卡,递给少年。少年接过来,低头在机器上刷卡。女人的眼睛环视四周,看见了窗前的那个画架。
你画画吗?女人的眼睛瞥了一眼画架问少年。
不,少年抬头说。那是我爸的。你们随便坐吧,一会儿我把饮料和蛋糕给你们端过去。
谢谢,女人微笑着说。
女人领着小女孩走到窗边,脱下外面的羽绒服,在画架旁边的桌子坐下。男人从少年手里接过信用卡,跟着走过去,坐在女人对面。
外面天干冷干冷的,男人搓着手说。好在屋子里还暖和一些。
小镇不错,女人看着窗外的灯塔说。安静,也美。
是不错,男人顺着女人的目光看着窗外说。
男人和女人看着窗外,一时失去了话语。他们沉默地坐着,像是相处太久,久得都无话可说了一样。即使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双方也懒得交谈什么。小女孩依偎着女人的膝盖,玩着女人的羽绒服上的一个扣子。
可是你更喜欢大城市,对吗?过了几分钟,男人最终打破了沉默,没话找话地问女人说。
原来在W城的时候,就觉得不习惯,女人带着感慨说。现在就更觉得不习惯了。从小在大城市里长大,到了W城就像是到了乡村似的感觉。
我爸爸原来也是在W城。少年把盛放着热咖啡,茶,蛋糕和果汁的托盘放到女人面前的小圆桌上说。你们是从中国来的吗?他也是从中国来的。
Oh, ya? 女人说。他是哪里人?
北京人。
可你身上一点也看不出。。。有亚洲人的血缘,女人用眼睛上下打量着少年说。
我是领养的,少年把切蛋糕的刀叉摆放在桌上说。十年以前,H城曾经来过一次飓风,发过一次大水,我亲生父母在飓风里丧生,是我爸妈领养了我,带着我来到这里。
十年前。。。飓风。。。女人眯着眼睛思索着。
突然像是想起来了什么似的,女人扬起眉毛来,问少年说:是卡洛斯飓风吗?
就是,少年说。我当时还小,不知道飓风的名字,后来我爸告诉了我,我还去查过一些资料。那次飓风比预报的要大,H城死了有一千多人,失踪了几十人,我亲生父母就在失踪的名单里面。
太可怜了,女人带着同情的眼光看着少年说。
也没什么,我爸妈对我很好的,比我亲生父母还好。少年对着他们微笑了一下,转身走回了柜台。
你怎么对一个飓风记得这么清楚呢?男人喝了一口热茶,问女人说。
那时我正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女人想了一下说。上飞机的时候听说飓风要登陆H城,到了北京,电视新闻里已经到处是H城的新闻,镜头上到处是飓风吹倒大树,掀开房顶,摧毁防洪堤,海水淹没H城的新闻,印象特别深刻。
妈妈我要吃蛋糕,小女孩打断了女人的话说。
女人左手用叉子扎住蛋糕,右手用餐具刀把蛋糕切成小块,让小女孩扎着吃。小女孩一边吃一边缠着女人问这问那,女人耐心地回答着小女孩的问题,看着小女孩把蛋糕都吃完,把果汁给喝了。
我们该走了。男人看了一下手表说。大巴快该出发了。
男人喝光了杯子里的最后的茶,把茶杯咖啡杯蛋糕盘收拾好,端着托盘,向着柜台走去,把托盘放在柜台边的一个台子上。女人站起身来,穿上乳白色的羽绒服,领着小女孩的手向着门口走去。在经过画架的时候,女人不经意地看了一眼画架上的画,突然怔住了。她停下脚步,仔细地看着画上的画,又看了一眼画面右下角的签名,身子微微的颤抖起来。
这是你父亲的画吗?女人扭过头来问柜台边低头忙碌的少年说。
他最后的一幅画,少年抬起头来说。
最后一幅画?他现在在哪里?女人问少年。
男人已经走到了门边。他不解地瞥了女人一眼,立在门边,把手放在门的把手上,眼睛看着表,有些不耐烦地等着女人。
一个月前他去世了,少年看着画架说。他画完这幅画后,晚上到前面的一个酒吧喝了一瓶酒,出门的时候,晕倒在雪地里。当时没有人看见他,他就冻死了。医生说,他以前也曾经喝多了酒晕倒过,但是过去都有人看见,就没出危险。
女人惊呆了。她楞楞地站在画架前面,像是内心在掀起一阵风暴的狂澜一样,脸色由红润一下变得苍白,像是全身的血液都挥发到空气里一样。她身体颤栗了一下,随后手扶着画架,让身子伫立在画架前,仔细地端详着画上的人物。她的眼里湿润了起来。小女孩挣脱了她的手,向着门口的男人跑去。
你还在磨蹭什么呢?男人催促着女人说。一个小镇上的业余画家的画有什么可看的,你要喜欢看画,夏天我带你去法国,去卢浮宫看去,那才过瘾------
我能买这幅画吗?女人不理男人的唠叨,从画面上抬起头问少年说。
你真疯了,男人不满地嘟囔说。赶紧走吧,别在这里耽误时间了,这破画也值得买。
你有完没完?女人对着男人吼了一声。
男人不出声了,把手从门把手上缩回来,拉着小女孩的手在门边站着。少年不知所措地看着男人和女人,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突然一下吵起来。他不太懂,有的夫妻看着很好很相配,对别人也都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但是他们自己说起话来却连陌生人都不如。
对不起,我想买这幅画。女人压下声音来,和颜悦色地对少年说。告诉我一个价钱,多少都行。
这画不能卖,少年带着一些抱歉说。这是我爸留下的唯一一幅亲笔画,以前他的画都给出版社了。这一幅还没来得及寄出去。我没告诉出版社,想留着它给自己做个纪念。
你刚才是说他一个月前才去世的吗?
还不到一个月,少年说。给他订的墓碑刚给运来,昨天才放在墓地上。
真是命啊,女人小声地嘟囔了一声。我怎么没有早点儿来?
什么?少年不解地问了一句。
哦,没什么,我是说要不是有件事耽搁了一下,一个月前我就该到这里了,女人带着一种悲伤的神情说。他的墓地在哪里?我能去看看吗?
可以,不是很远,在前面的小山边,少年伸手指着窗外隐约可见的一片青色的小山说。开车要几分钟,走着要二十分钟吧。你要是想去,我可以开车带你去,反正现在店里也没人,有个一刻钟就够来回的了。
大巴该开走了。男人明显的不耐烦地推开门,眼睛看着墙上的电子钟说。你走不走?不走我走了,一车上的人都等着我们呢。出门就磨蹭,到这里又磨蹭,早知这样我不跟着出来了。
少年看了男人一眼,不解男人哪里来的这么大的火气。难道她不是你的太太吗?难道你对她不能耐心一点儿,好好的说话吗?少年想。
妈妈,快走吧,去晚了车上的叔叔阿姨们又该说我们了。小女孩跑过来摇晃着女人的手说。
门外的阳光和冷风一起吹进来,不远处传来灰狗大巴导游在招呼游客们上车的声音。墙上的电子表的秒针在滴答地响着,像是在催促着依旧站在画架之前的女人离去。女人突然像是控制不住自己了一样,在画前闭上了眼睛,再睁开的时候,眼睛里掉出一滴晶莹的泪水来。她没有再跟少年讲话,也没有搭理男人,只是最后看了一眼画架,被小女孩拉着,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咖啡馆的大门。
咖啡馆的贴着圣诞图像的大门重新关上,乳白色的长羽绒服和白色的路易维登包随着脚步声一起消失了,屋内重新回到了一片静穆之中。少年走到画架之前,看着画上被泪水浸湿的一个逐渐扩大的圆点,思索着。他想不清楚那个女人为何掉下眼泪来,但是显然,这幅画勾起了女人的一些回忆。秒针在一秒一秒地走着,少年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觉得读懂了女人沉默的外表下心里所起的狂澜,以及女人最后留在画架上的悲伤。少年把画从画架上拿下来,卷起,推开了咖啡馆的屋门,向着不远处的灰狗大巴快步走去。
大巴在一声沉重的哀鸣之中,关上了门,轮子开始在雪地上移动,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在地上碾出一道道硬硬的轮胎痕迹。少年看见灰狗大巴昏暗的车厢里,一个乳白色的羽绒服站了起来,从车厢后部走向前部。阳光流泻在少年身上,他沿着铺满白雪的街道快速地跑着,不知道大巴是否会停下来等他一下。大巴驶进了一片树从的阴影之中,他甚至看不见车厢里面的乳白色的羽绒服了。但是他知道,乳白色的羽绒服一定看见了他,也知道他在为什么追着大巴。树丛从他的身边向后倒去,阳光晃着他的眼睛,让他看不清前面的路。他眯着眼一边跑,一边不断地向大巴挥舞着手里卷起来的画,像是挥舞着一把闪闪发光的宝剑。
【全文完】
- 注册
- 2010-04-24
- 消息
- 33,189
- 荣誉分数
- 17,601
- 声望点数
- 1,373
后记:
这一篇终于敲完了,哩哩啦啦的,一共敲了三十五万字。本来想七月底写完,一直拖到了九月底。一开始是想写《邻居家的女孩》,写着写着转成了《蓝色的浮冰》。
下一步,是想把《蓝色的浮冰》重新整理一下,动个大手术,结构上重新调整一下各个章节,增删一些内容,人物性格也要更一致一些,再补一补里面的漏洞。然后给贴到文学城上去。
再下一步,是想把《小小饼屋》给扩展一下,把那个短篇给扩展成中长篇。
写《蓝色的浮冰》的一个附带的收获,是看到了自己的不少的弱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相信《蓝色浮冰》的修改稿一定会比这个初稿好一些。写到中间差点儿坚持不下去了,最后总算把坑给填满了,心里也松了一口气。虽然没有能够达到最开始的预想,但是完成了一部总是心里很高兴的。
这一篇终于敲完了,哩哩啦啦的,一共敲了三十五万字。本来想七月底写完,一直拖到了九月底。一开始是想写《邻居家的女孩》,写着写着转成了《蓝色的浮冰》。
下一步,是想把《蓝色的浮冰》重新整理一下,动个大手术,结构上重新调整一下各个章节,增删一些内容,人物性格也要更一致一些,再补一补里面的漏洞。然后给贴到文学城上去。
再下一步,是想把《小小饼屋》给扩展一下,把那个短篇给扩展成中长篇。
写《蓝色的浮冰》的一个附带的收获,是看到了自己的不少的弱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相信《蓝色浮冰》的修改稿一定会比这个初稿好一些。写到中间差点儿坚持不下去了,最后总算把坑给填满了,心里也松了一口气。虽然没有能够达到最开始的预想,但是完成了一部总是心里很高兴的。
最后编辑:
- 注册
- 2010-04-24
- 消息
- 33,189
- 荣誉分数
- 17,601
- 声望点数
- 1,373
呵呵,毫无疑问,你的小说你做主。格格真的对你很nice,连话也讲得含蓄有理。我是没药可救了,打算恶人做到底。因着这次你有框架了,不是随意写,那就先砸你一下。诚实地讲,只有这篇我细细读过,所以也就认真滴说些看法
按你的描述,这小说整个儿就是重写。但只要你不嫌麻烦,为什么不呢。只是别忘了,要重写(大框架改变)就该认真滴重敲每一个字,哪怕是与一版蓝冰的段落一模一样,也要一字一句地敲键盘,因为这种抄写也会有tone 的不同,会有只字的变化,也才会有精华。以前,粗粗看过你的11世,那时只顾溜须拍马。其实想说,那个改写和没改区别不大,反倒失了真性情
用飓风做背景听上去很吸引人,等着看。 说起意识流,对你也算合适。看你独自幂想的片段也挺疯,写这个应该很过瘾。你疯魔地扮演每一个人,每个人物自己展现他们的感受和挖掘他们自己的内心深处, 自由联想,意识飘移,再玩儿点您特有的意识流语言。 妙
对了,你是打民国来的? 为什么现代女孩小萍要有东方的含蓄,小镇的她要有西方的热烈。再说您刚写完的那篇可一点儿也没看出来,而且是反着的。 其实,一版的蓝冰在处理小萍和小镇女的性格上是很成功的,应该借鉴。要塑造新的性格怕是工作量太艰巨了吧。一直不知道,小镇女是哪国人?
在信息发达的现今社会,文化这词已经显得越来越淡薄了,东西方文化也国际化了。 特别是现在的中国,有文化吗。所谓的东方文化只能体现在拘谨的举止,狭隘的思维,和偏执不自信地扭捏作态。而真正东方的优雅端庄,剔透玲珑,兰质蕙心,知书达理, 仪态万方 又有几个人见过。 西方也只有在六七十年代,受第二波的冲击,才有疯狂的一段,但也被淘汰了。真正的西方文化是个宗教的文化,从几个洋人身上了解,即使生活过几年也不全,太片面。 除非是很主流的那种,还要隔绝一段东方文化,才能领悟一点
因此,人物内心的变化,走文化路子难呀,倒是着眼于人性方面的挣扎,会来得更真切些,也容易。当然,也许楼主早胸有成竹。反正,有感受写时才能打动自己,影响别人。 写男主,干嘛老写的象神一样的完美无瑕疵。先大逆不道, 再挣扎,最后从良,不信就没有看点。 当然,男主一定要有个性,是个才俊, 讨人喜欢的那种
总之,既然大框架变了,细节也不会一模一样。那么就该先放二版在这儿,让这儿的人给你重新洗礼一下,然后不变框架滴改细节。最后,放到文学城。 您觉得484这样好呀。 还是那句话,你的小说你做主,对你这种donkey style person,还应该有兼听则明
没有想重写,重码这么多字。。。。想起来就晕。
我也没有完全想好,我想很多细节和故事可以用原来的,不过是在一个不同的故事结构下。原来是跨度几年的一个故事,现在想给它浓缩到几天几夜。
小镇女孩没有写是哪国人,也没有名字,这样你把她想成哪里的人都可以。
人们一般都觉得东方女孩会含蓄一点儿吧,我觉得也是这样。
一直不太喜欢写人性的挣扎,因为现在人们的生活都平平淡淡,没有那么多坏人和悲惨故事,《悲惨世界》那个时代是一百多年以前了。我想海明威要是今天重新写《老人与海》,他可能会写老人在海上坐了一天,没看见大鱼,自己感伤了一段就回来了,而不会再写老人与大鱼的搏斗。
我觉得没必要在这里再贴二版了,等我改得差不多了直接贴文学城就是了。
- 注册
- 2010-04-24
- 消息
- 33,189
- 荣誉分数
- 17,601
- 声望点数
- 1,373
- 注册
- 2010-04-24
- 消息
- 33,189
- 荣誉分数
- 17,601
- 声望点数
- 1,373
梵高的画你不能用现在的眼光看,他那个时代就是没看点,没人喜欢他的画。他亲哥是卖画的agent,哪怕他的画在当时有一丁点儿看点,他哥早把他给推销出去了,而不至于只卖出一幅画去。嗯,我可以闭着眼鼓励你不管不顾,不用借鉴,不看脚下,闷头儿开辟你自己的路。可你不觉得太假,太无知。我只能说,任何的写作当然都需要看读者层面,写个检查不也要看是给谁写。 至于看点,更别说了,,,什么叫纯文学艺术? 梵高不是也摆脱不了黄金分割,他的画,那里没看点? 他的风格是建立在他专业的熟练的画技基础上的。而这基础早融入于他的血液,人们看不见这层,就只
见他执迷于自己的风格。如果只为了追求风格而忽略其他所有的东西,是不是有点急功近利。自己的风格是一种油然而生,很明确要怎么做的。你很清楚吗? 还是正在寻找的过程中?
我觉得写东西的时候,你不能想这个情节是不是看点,是不是会有人喜欢,会不会读的人多。你应该想,这样写是不是你觉得最好。如果你觉得这样写最好,就这样写。
我知道你在好心的建议,想让我写出来的东西变得更吸引人一些。但我觉得能否更吸引人不是关键的。有些情节可能会增加看点,但并不是我想要的或者在乎的。
最后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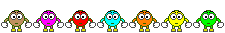 i miss you
i miss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