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册
- 2010-07-16
- 消息
- 6,980
- 荣誉分数
- 648
- 声望点数
- 223
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
我庆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告诉你为什么。
9月,欧洲和东南亚的二十二个外交部长在德国开会。新加坡外长教训欧洲人:
“我们亚洲人拥有足够的科技与资金去长期发展经济……冷战结束之后,欧洲人试
图外销他们的文化价值;我们可以接受其中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双方必须学习去
尊重对方的不同。”
说得理直气壮,好像亚洲人整个的尊严都在里面了。地主国德国的报纸也以显
著的排版突出新闻。主题是“亚洲和欧洲的文化冲突”。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说法当
然又被引用:讲究自由和个人尊严的西方文化对峙强调权威和集体利益的亚洲文化。”
新加坡外长的话有什么不对吗?表面上没有不对。欧洲的文化输出当然不仅只
是冷战后的几年;对中国而言,应该说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如果我们从鸦片战
争算起。风水轮流转,欧洲人向别国学习,也是时候了。令我不舒服的是,最近新
加坡政府频频与西方对话,口气中俨然以亚洲的代言人自居。开口就是“我们亚洲
人的价值怎么样怎么样……”西方的媒体竟然也跟着说“他们亚洲人的价值怎么样
怎么……”两造一唱一和,好像新加坡代表了亚洲,新加坡的文化价值就是整个亚
洲的文化价值。
什么时候,李光耀变成了我的代言人?
鞭打美国人的案件刚过去, 新加坡在9月吊死了一个贩毒的荷兰人。已经废除
死刑的欧洲人议论纷纷。我并不特别同情这个荷兰人——他知法犯法,而且,新加
坡没有理由因为他是欧洲人而对他法外开恩。但是,新加坡政府没有傲慢的权利—
—至少,它没有资格代表我这个台湾人,而我可是个道地的亚洲人。
我不赞成死刑。我不赞成将死刑犯五花大绑拍照。我不喜欢看到丢纸屑的人被
警察当众羞辱作为合法的惩罚。我不喜欢人家来规定我能不能吃口香糖。我不愿意
买不到想读的外国杂志。我不愿意任何人告诉我我能看什么书不能看什么书。我不
能忍受一小撮人指定我怎么想,怎么说,怎么活,怎么做爱生几个小孩。我不能忍
受一小撮自以为比我聪明的人告诉我我的文化价值是什么。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
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个人自由与
尊严。
而且,有这种想法的人绝对不只我一个亚洲人。日本,韩国,台湾……多的是。
新加坡理想国内也很多,只不过我们外面的人听不见他们的声音罢了。
新加坡人当然有充分权利依照他们的价值准则去过日子——什么样的人民有什
么样的政府。但是拜托,下次再有什么西方人被打被吊的,说“我们新加坡人如何
如何?’吧!不要把我这一类不可救药的讲究个人尊严与自由的“亚洲人”包括进
去。
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的话,写了这篇文章可不好玩了。
<script>mpanel(1);</script>
(原载1994年10月10日台北《中国时报》)
</pre>
我庆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告诉你为什么。
9月,欧洲和东南亚的二十二个外交部长在德国开会。新加坡外长教训欧洲人:
“我们亚洲人拥有足够的科技与资金去长期发展经济……冷战结束之后,欧洲人试
图外销他们的文化价值;我们可以接受其中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双方必须学习去
尊重对方的不同。”
说得理直气壮,好像亚洲人整个的尊严都在里面了。地主国德国的报纸也以显
著的排版突出新闻。主题是“亚洲和欧洲的文化冲突”。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说法当
然又被引用:讲究自由和个人尊严的西方文化对峙强调权威和集体利益的亚洲文化。”
新加坡外长的话有什么不对吗?表面上没有不对。欧洲的文化输出当然不仅只
是冷战后的几年;对中国而言,应该说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如果我们从鸦片战
争算起。风水轮流转,欧洲人向别国学习,也是时候了。令我不舒服的是,最近新
加坡政府频频与西方对话,口气中俨然以亚洲的代言人自居。开口就是“我们亚洲
人的价值怎么样怎么样……”西方的媒体竟然也跟着说“他们亚洲人的价值怎么样
怎么……”两造一唱一和,好像新加坡代表了亚洲,新加坡的文化价值就是整个亚
洲的文化价值。
什么时候,李光耀变成了我的代言人?
鞭打美国人的案件刚过去, 新加坡在9月吊死了一个贩毒的荷兰人。已经废除
死刑的欧洲人议论纷纷。我并不特别同情这个荷兰人——他知法犯法,而且,新加
坡没有理由因为他是欧洲人而对他法外开恩。但是,新加坡政府没有傲慢的权利—
—至少,它没有资格代表我这个台湾人,而我可是个道地的亚洲人。
我不赞成死刑。我不赞成将死刑犯五花大绑拍照。我不喜欢看到丢纸屑的人被
警察当众羞辱作为合法的惩罚。我不喜欢人家来规定我能不能吃口香糖。我不愿意
买不到想读的外国杂志。我不愿意任何人告诉我我能看什么书不能看什么书。我不
能忍受一小撮人指定我怎么想,怎么说,怎么活,怎么做爱生几个小孩。我不能忍
受一小撮自以为比我聪明的人告诉我我的文化价值是什么。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
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个人自由与
尊严。
而且,有这种想法的人绝对不只我一个亚洲人。日本,韩国,台湾……多的是。
新加坡理想国内也很多,只不过我们外面的人听不见他们的声音罢了。
新加坡人当然有充分权利依照他们的价值准则去过日子——什么样的人民有什
么样的政府。但是拜托,下次再有什么西方人被打被吊的,说“我们新加坡人如何
如何?’吧!不要把我这一类不可救药的讲究个人尊严与自由的“亚洲人”包括进
去。
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的话,写了这篇文章可不好玩了。
<script>mpanel(1);</script>
(原载1994年10月10日台北《中国时报》)
</p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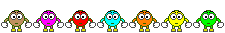 加油!
加油!